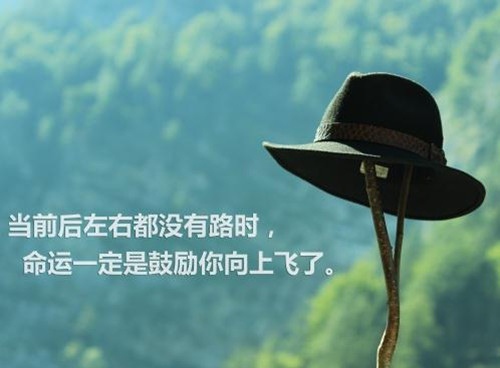女朋友都说分手了,还戴着我送她的定情信物是什么意思?
把酒;持鳌。
筚篥;喇叭。
筑堤;修坝。
兴亡;成败。
鹭序;鹓班。
更深;夜半。
复国;兴邦。
自理;承包。
花萼;芽苞。
美誉;嘉褒。
长幼;尊卑。
喜悦;伤悲。
对虾;贻贝。
慢走;狂奔。
周末;日本。
总结;评比。
红安;赤壁。
护岛;侵边。
抑扬;褒贬。
骤雨;狂飙。
区分;辨别。
济济;彬彬。
三火;九冰。
猛将;雄兵。
荷泽;荔波。
秋割;春播。
云浓;雾薄。
棉绸;纱布。
信赖;疑猜。
七曜;三才。
定情;纳采。
政协;军参。
月落;花残。
车站;船舱。
授职;分曹。
水塔;烟囱。
暖灶;寒窗。
椽檩;门窗。
净几;明窗。
绣户;纱窗。
深屋;疏窗。
东阁;西窗。
帆影;舷窗。
兰室;芸窗。
户扇;灶窗。
西席;东床。
电扇;机床。
雨打;风吹。
耸立;低垂。
雨洒;虹垂。
内陆;边陲。
半夏;长春。
白日;青春。
露夏;望春。
腊月;新春。
消夏;游春。
陆橘;庄椿。
老练;单纯。
眉目;齿唇。
蜜意;芳唇。
杏靥;樱唇。
白脸;朱唇。
粉颈;朱唇。
皓齿;朱唇。
鄙陋;深淳。
鹦鹉;鹌鹑。
隽永;芳醇。
淡泊;和醇。
聪明;愚蠢。
测字;弹词。
妙曲;好词。
古庙;荒祠。
土舍;茅茨。
镀锡;搪瓷。
暴戾;仁慈。
孝友;仁慈。
传记;歌辞。
礼义;文辞。
牝牡;雄雌。
鹦鹉;鸬鹚。
因而;故此。
对刀;议刺。
遵守;服从。
罢赛;盲从。
保卫;随从。
便宜;随从。
信赖;依从。
草草;匆匆。
海藻;沙葱。
艾虎;花骢。
碧野;芳丛。
手拙;心粗。
韭郁;介脆。
珍珠;翡翠。
寻芳;拾翠。
老舍;陈村。
药圃;花村。
顾城;回村。
工厂;农村。
海岛;山村。
城市;乡村。
抚按;揉搓。
调控;切磋。
犁耙;鋾锉。
风吹;浪打。
伶俐;痴呆。
颖悟;痴呆。
是非;好歹。
峨冠;博带。
一帮;二带。
地衣;海带。
披襟;弄带。
指环;腰带。
金簪;玉带。
锦袍;玉带。
萍逢;株待。
储蓄;借贷。
皮衣;布袋。
酒囊;饭袋。
眼波;眉黛。
丸散;膏丹。
妙药;灵丹。
积翠;流丹。
水白;山丹。
血赤;心丹。
素白;朱丹。
求偶;保单。
台独;床单。
热闹;孤单。
被薄;衣单。
手举;肩担。
千钧;万担。
手熟;心耽。
郏鄏;邯郸。
桐柏;邯郸。
计拙;心殚。
丹心;赤胆。
粗心;大胆。
寸心;斗胆。
忠肝;义胆。
星期;谷旦。
真诚;妄诞。
杜撰;包弹。
飞船;导弹。
鱼雷;导弹。
论点;评弹。
雅吹;清弹。
菜蔬;茶淡。
明暗;浓淡。
浅深;浓淡。
亥既;丁当。
茶芽;瓜当。
鱼复;马当。
象简;珠珰。
薜荔;筼筜。
浮洲;莽荡。
舞剑;操刀。
乱箭;单刀。
舞剑;挥刀。
湖笔;井刀。
把剑;磨刀。
嘱咐;唠叨。
宣传;辅导。
手舞;足蹈。
爱情;交道。
里闾;街道。
主阶;邻道。
马路;人道。
曲艺;歌德。
赞美;歌德。
炉火;壁灯。
渔火;禅灯。
月桂;宫灯。
只履;孤灯。
彩烛;花灯。
石箭;金灯。
刻苦;攀登。
祖逖;孙登。
独步;同登。
武进;文登。
远近;高低。
左右;高低。
露重;云低。
大坝;长堤。
曲岸;长堤。
远岸;危堤。
筹边;御敌。
黄茅;白荻。
鸾箫;凤笛。
钢琴;竹笛。
毫尖;笔底。
胸中;肚底。
高天;大地。
边区;腹地。
桑田;麦地。
画墙;漆地。
竹田;石地。
陈皮;熟地。
城隍;土地。
高原;洼地。
冰天;雪地。
名言;妙谛。
救溺;扶颠。
水底;山颠。
海港;山巅。
面条;糕点。
心音;脑电。
花坞;芳甸。
粉黛;钗钿。
川沙;海淀。
琼楼;宝殿。
兰台;桂殿。
芦帘;竹簟。
叶茂;花凋。
刺虎;斩貂。
快马;大雕。
深刻;浮雕。
细刻;精雕。
鸡谈;鹤吊。
晓耕;寒钓。
雨顺;风调。
修合;烹调。
山歌;水调。
耳顺;心调。
燕引;莺调。
舅舅;爹爹。
锤子;干爹。
母舅;姑爹。
水母;沙爹。
孤单;重迭。
逶迤;重迭。
北樵;西谍。
谯楼;雉堞。
期颐;耄耋。
飞蛾;舞蝶。
菜甲;瓜丁。
盗甲;哄丁。
黑丑;红丁。
马甲;鸡丁。
孤独;零丁。
三甲;六丁。
知己;识丁。
玉甲;银丁。
局促;伶仃。
胧朦;酩酊。
蜂腰;鹤顶。
竹肤;木顶。
拔山;扛鼎。
商彝;周鼎。
动摇;坚定。
长乐;永定。
同安;永定。
惊慌;镇定。
取得;抛丢。
岭北;江东。
冀北;辽东。
河北;山东。
湖北;山东。
岭北;山东。
陕北;山东。
南北;西东。
春夏;秋冬。
九夏;三冬。
酷夏;严冬。
云霞;螮蝀。
风吹;草动。
神驰;心动。
生泉;破冻。
岱岳;崆峒。
雕梁;画栋。
珠帘;画栋。
竹林;石洞。
佛堂;仙洞。
烟楼;雪洞。
天阙;皇都。
首府;京都。
南宫;北斗。
追求;奋斗。
烧瓶;漏斗。
红薯;绿豆。
权衡;尺度。
小小;端端。
彻底;开端。
取长;补短。
重轻;长短。
偏长;超短。
鹤长;凫短。
川莲;续断。
丝绒;绸缎。
马邑;龙堆。
湖墅;山墩。
竹榻;石墩。
先锋;后盾。
兵少;官多。
富寡;贫多。
谋广;智多。
琢雕;堆垛。
扶犁;掌舵。
勤劳;怠惰
《骆驼祥子》关于描写祥子的十个片段和虎妞的五个片段 每个片段50字
【精彩片段】 他的身量肉都发展到年岁前边去;二十来的岁已经很大很高,虽然肢体还没被年月铸成一定的格局,可是已经像个成人了——一个脸上身上都带出天真淘气的样子的大人。
看着那高等的车夫,他计划着怎样杀进他的腰①(注释:①〔杀进腰〕把腰部勒得细一些。
)去,好更显出他的铁扇面似的胸,与直硬的背;扭头看看自己的肩,多么宽,多么威严!杀好了腰,再穿上肥腿的白裤,裤脚用鸡肠子带儿系住,露出那对“出号”的大脚!是的,他无疑的可以成为最出色的车夫;傻子似的他自己笑了。
他没有什么模样,使他可爱的是脸上的精神。
头不很大,圆眼,肉鼻子,两条眉很短很粗,头上永远剃得发亮。
腮上没有多余的肉,脖子可是几乎与头一边儿②(注释:②〔一边儿〕即同样的。
)粗;脸上永远红扑扑的,特别亮的是颧骨与右耳之间一块不小的疤——小时候在树下睡觉,被驴啃了一口。
他不甚注意他的模样,他爱自己的脸正如同他爱自己的身体,都那么结实硬棒;他把脸仿佛算在四肢之内,只要硬棒就好。
是的,到城里以后,他还能头朝下,倒着立半天。
这样立着,他觉得,他就很像一棵树,上下没有一个地方不挺脱的。
他确乎有点像一棵树,坚壮,沉默,而又有生气。
他有自己的打算,有些心眼,但不好向别人讲论。
在洋车夫里,个人的委屈与困难是公众的话料,“车口儿”上,小茶馆中,大杂院里,每人报告着形容着或吵嚷着自己的事,而后这些事成为大家的财产,像民歌似的由一处传到一处。
祥子是乡下人,口齿没有城里人那么灵便;设若口齿灵利是出于天才,他天生来的不愿多说话,所以也不愿学着城里人的贫嘴恶舌。
他的事他知道,不喜欢和别人讨论。
因为嘴常闲着,所以他有工夫去思想,他的眼仿佛是老看着自己的心。
只要他的主意打定,他便随着心中所开开的那条路儿走;假若走不通的话,他能一两天不出一声,咬着牙,好似咬着自己的心! 他决定去拉车,就拉车去了。
赁了辆破车,他先练练腿。
第一天没拉着什么钱。
第二天的生意不错,可是躺了两天,他的脚脖子肿得像两条瓠子似的,再也抬不起来。
他忍受着,不管是怎样的疼痛。
他知道这是不可避免的事,这是拉车必须经过的一关。
非过了这一关,他不能放胆的去跑。
脚好了之后,他敢跑了。
这使他非常的痛快,因为别的没有什么可怕的了:地名他很熟习,即使有时候绕点远也没大关系,好在自己有的是力气。
拉车的方法,以他干过的那些推,拉,扛,挑的经验来领会,也不算十分难。
况且他有他的主意:多留神,少争胜,大概总不会出了毛病。
至于讲价争座,他的嘴慢气盛,弄不过那些老油子们。
知道这个短处,他干脆不大到“车口儿”上去;哪里没车,他放在哪里。
在这僻静的地点,他可以从容的讲价,而且有时候不肯要价,只说声:“坐上吧,瞧着给!”他的样子是那么诚实,脸上是那么简单可爱,人们好像只好信任他,不敢想这个傻大个子是会敲人的。
即使人们疑心,也只能怀疑他是新到城里来的乡下老儿,大概不认识路,所以讲不出价钱来。
以至人们问到:“认识呀?”他就又像装傻,又像耍俏的那么一笑,使人们不知怎样才好。
两三个星期的工夫,他把腿溜出来了。
他晓得自己的跑法很好看。
跑法是车夫的能力与资格的证据。
那撇着脚,像一对蒲扇在地上扇乎的,无疑的是刚由乡间上来的新手。
那头低得很深,双脚蹭地,跑和走的速度差不多,而颇有跑的表示的,是那些五十岁以上的老者们。
那经验十足而没什么力气的却另有一种方法;胸向内含,度数很深;腿抬得很高;一走一探头;这样,他们就带出跑得很用力的样子,而在事实上一点也不比别人快;他们仗着“作派”去维持自己的尊严。
祥子当然决不采取这几种姿态。
他的腿长步大,腰里非常的稳,跑起来没有多少响声,步步都有些伸缩,车把不动,使座儿觉到安全,舒服。
说站住,不论在跑得多么快的时候,大脚在地上轻蹭两蹭,就站住了;他的力气似乎能达到车的各部分。
脊背微俯,双手松松拢住车把,他活动,利落,准确;看不出急促而跑得很快,快而没有危险。
就是在拉包车的里面,这也得算很名贵的。
精彩片段 1 他的身量与筋肉都发展到年岁前边去;二十来岁,他已经很大很虽然肢体还没被年月铸成一定的格局,可是已经像个成人了——一个脸上身上都带出天真淘气的样子的大人。
看着那高等的车夫,他计划着怎样杀进他的腰①(注释:①〔杀进腰〕把腰部勒得细一些。
)去,好更显出他的铁扇面似的胸,与直硬的背;扭头看看自己的肩,多么宽,多么威严!杀好了腰,再穿上肥腿的白裤,裤脚用鸡肠子带儿系住,露出那对“出号”的大脚!是的,他无疑的可以成为最出色的车夫;傻子似的他自己笑了。
他没有什么模样,使他可爱的是脸上的精神。
头不很大,圆眼,肉鼻子,两条眉很短很粗,头上永远剃得发亮。
腮上没有多余的肉,脖子可是几乎与头一边儿②(注释:②〔一边儿〕即同样的。
)粗;脸上永远红扑扑的,特别亮的是颧骨与右耳之间一块不小的疤——小时候在树下睡觉,被驴啃了一口。
他不甚注意他的模样,他爱自己的脸正如同他爱自己的身体,都那么结实硬棒;他把脸仿佛算在四肢之内,只要硬棒就好。
是的,到城里以后,他还能头朝下,倒着立半天。
这样立着,他觉得,他就很像一棵树,上下没有一个地方不挺脱的。
他确乎有点像一棵树,坚壮,沉默,而又有生气。
他有自己的打算,有些心眼,但不好向别人讲论。
在洋车夫里,个人的委屈与困难是公众的话料,“车口儿”上,小茶馆中,大杂院里,每人报告着形容着或吵嚷着自己的事,而后这些事成为大家的财产,像民歌似的由一处传到一处。
祥子是乡下人,口齿没有城里人那么灵便;设若口齿灵利是出于天才,他天生来的不愿多说话,所以也不愿学着城里人的贫嘴恶舌。
他的事他知道,不喜欢和别人讨论。
因为嘴常闲着,所以他有工夫去思想,他的眼仿佛是老看着自己的心。
只要他的主意打定,他便随着心中所开开的那条路儿走;假若走不通的话,他能一两天不出一声,咬着牙,好似咬着自己的心! 他决定去拉车,就拉车去了。
赁了辆破车,他先练练腿。
第一天没拉着什么钱。
第二天的生意不错,可是躺了两天,他的脚脖子肿得像两条瓠子似的,再也抬不起来。
他忍受着,不管是怎样的疼痛。
他知道这是不可避免的事,这是拉车必须经过的一关。
非过了这一关,他不能放胆的去跑。
脚好了之后,他敢跑了。
这使他非常的痛快,因为别的没有什么可怕的了:地名他很熟习,即使有时候绕点远也没大关系,好在自己有的是力气。
拉车的方法,以他干过的那些推,拉,扛,挑的经验来领会,也不算十分难。
况且他有他的主意:多留神,少争胜,大概总不会出了毛病。
至于讲价争座,他的嘴慢气盛,弄不过那些老油子们。
知道这个短处,他干脆不大到“车口儿”上去;哪里没车,他放在哪里。
在这僻静的地点,他可以从容的讲价,而且有时候不肯要价,只说声:“坐上吧,瞧着给!”他的样子是那么诚实,脸上是那么简单可爱,人们好像只好信任他,不敢想这个傻大个子是会敲人的。
即使人们疑心,也只能怀疑他是新到城里来的乡下老儿,大概不认识路,所以讲不出价钱来。
以至人们问到:“认识呀?”他就又像装傻,又像耍俏的那么一笑,使人们不知怎样才好。
两三个星期的工夫,他把腿溜出来了。
他晓得自己的跑法很好看。
跑法是车夫的能力与资格的证据。
那撇着脚,像一对蒲扇在地上扇乎的,无疑的是刚由乡间上来的新手。
那头低得很深,双脚蹭地,跑和走的速度差不多,而颇有跑的表示的,是那些五十岁以上的老者们。
那经验十足而没什么力气的却另有一种方法;胸向内含,度数很深;腿抬得很高;一走一探头;这样,他们就带出跑得很用力的样子,而在事实上一点也不比别人快;他们仗着“作派”去维持自己的尊严。
祥子当然决不采取这几种姿态。
他的腿长步大,腰里非常的稳,跑起来没有多少响声,步步都有些伸缩,车把不动,使座儿觉到安全,舒服。
说站住,不论在跑得多么快的时候,大脚在地上轻蹭两蹭,就站住了;他的力气似乎能达到车的各部分。
脊背微俯,双手松松拢住车把,他活动,利落,准确;看不出急促而跑得很快,快而没有危险。
就是在拉包车的里面,这也得算很名贵的。
【点评】这一段人物描写,从装束、体态、身段,到靠力气吃饭的人所引以自豪的体能、体力以及品性人格都写得很精彩,把一个活生生的祥子呈现在我们面前。
作者大声地赞美他——他的健壮、朴实、充满生气,让我们与作者一同欣赏这个旧中国的北京人力车夫吧! 精彩片段 2 外面的黑暗渐渐习惯了,心中似乎停止了活动,他的眼不由的闭上了。
不知道是往前走呢,还是已经站住了,心中只觉得一浪一浪的波动,似一片波动的黑海,黑暗与心接成一气,都渺茫,都起落,都恍惚。
忽然心中一动,象想起一些什么,又似乎是听见了一些声响,说不清;可是又睁开了眼。
他确是还往前走呢,忘了刚才是想起什么来,四外也并没有什么动静。
心跳了一阵,渐渐又平静下来。
他嘱咐自己不要再闭上眼,也不要再乱想;快快的到城里是第一件要紧的事。
可是心中不想事,眼睛就很容易再闭上,他必须想念着点儿什么,必须醒着。
他知道一旦倒下,他可以一气睡三天。
想什么呢
他的头有些发晕,身上潮渌渌的难过,头发里发痒,两脚发酸,口中又干又涩。
他想不起别的,只想可怜自己。
可是,连自己的事也不大能详细的想了,他的头是那么虚空昏胀,仿佛刚想起自己,就又把自己忘记了,象将要灭的蜡烛,连自己也不能照明白了似的。
再加上四围的黑暗,使他觉得象在一团黑气里浮荡,虽然知道自己还存在着,还往前迈步,可是没有别的东西来证明他准是在哪里走,就很象独自在荒海里浮着那样不敢相信自己。
他永远没尝受过这种惊疑不定的难过,与绝对的寂闷。
平日,他虽不大喜欢交朋友,可是一个人在日光下,有太阳照着他的四肢,有各样东西呈现在目前,他不至于害怕。
现在,他还不害怕,只是不能确定一切,使他受不了。
设若骆驼们要是象骡马那样不老实,也许倒能教他打起精神去注意它们,而骆驼偏偏是这么驯顺,驯顺得使他不耐烦;在心神最恍惚的时候,他忽然怀疑骆驼是否还在他的背后,教他吓一跳;他似乎很相信这几个大牲口会轻轻的钻入黑暗的岔路中去,而他一点也不晓得,象拉着块冰那样能渐渐的化尽。
精彩片段 3(18)五那天,天热得发了狂。
太阳刚一出来,地上已象下了火。
一些似云非云,似雾非雾的灰气低低的浮在空中,使人觉得憋气。
一点风也没有。
祥子在院中看了看那灰红的天,打算去拉晚儿——过下午四点再出去;假若挣不上钱的话,他可以一直拉到天亮:夜间无论怎样也比白天好受一些。
虎妞催着他出去,怕他在家里碍事,万一小福子拉来个客人呢。
“你当在家里就好受哪
屋子里一到晌午连墙都是烫的
” 他一声没出,喝了瓢凉水,走了出去。
街上的柳树,象病了似的,叶子挂着层灰土在枝上打着卷;枝条一动也懒得动的,无精打采的低垂着。
马路上一个水点也没有,干巴巴的发着些白光。
便道上尘土飞起多高,与天上的灰气联接起来,结成一片毒恶的灰沙阵,烫着行人的脸。
处处干燥,处处烫手,处处憋闷,整个的老城象烧透的砖窑,使人喘不出气。
狗爬在地上吐出红舌头,骡马的鼻孔张得特别的大,小贩们不敢吆喝,柏油路化开;甚至于铺户门前的铜牌也好象要被晒化。
街上异常的清静,只有铜铁铺里发出使人焦躁的一些单调的叮叮当当。
拉车的人们,明知不活动便没有饭吃,也懒得去张罗买卖:有的把车放在有些阴凉的地方,支起车棚,坐在车上打盹;有的钻进小茶馆去喝茶;有的根本没拉出车来,而来到街上看看,看看有没有出车的可能。
那些拉着买卖的,即使是最漂亮的小伙子,也居然甘于丢脸,不敢再跑,只低着头慢慢的走。
每一个井台都成了他们的救星,不管刚拉了几步,见井就奔过去;赶不上新汲的水,便和驴马们同在水槽里灌一大气。
还有的,因为中了暑,或是发痧,走着走着,一头栽在地上,永不起来。
连祥子都有些胆怯了
拉着空车走了几步,他觉出由脸到脚都被热气围着,连手背上都流了汗。
可是,见了座儿,他还想拉,以为跑起来也许倒能有点风。
他拉上了个买卖,把车拉起来,他才晓得天气的厉害已经到了不允许任何人工作的程度。
一跑,便喘不过气来,而且嘴唇发焦,明知心里不渴,也见水就想喝。
不跑呢,那毒花花的太阳把手和脊背都要晒裂。
好歹的拉到了地方,他的裤褂全裹在了身上。
拿起芭蕉扇搧,没用,风是热的。
他已经不知喝了几气凉水,可是又跑到茶馆去。
两壶热茶喝下去,他心里安静了些。
茶由口中进去,汗马上由身上出来,好象身上已是空膛的,不会再藏储一点水分。
他不敢再动了。
坐了好久,他心中腻烦了。
既不敢出去,又没事可作,他觉得天气仿佛成心跟他过不去。
不,他不能服软。
他拉车不止一天了,夏天这也不是头一遭,他不能就这么白白的“泡”一天。
想出去,可是腿真懒得动,身上非常的软,好象洗澡没洗痛快那样,汗虽出了不少,而心里还不畅快。
又坐了会儿,他再也坐不住了,反正坐着也是出汗,不如爽性出去试试。
一出来,才晓得自己的错误。
天上那层灰气已散,不甚憋闷了,可是阳光也更厉害了许多:没人敢抬头看太阳在哪里,只觉得到处都闪眼,空中,屋顶上,墙壁上,地上,都白亮亮的,白里透着点红;由上至下整个的象一面极大的火镜,每一条光都象火镜的焦点,晒得东西要发火。
在这个白光里,每一个颜色都刺目,每一个声响都难听,每一种气味都混含着由地上蒸发出来的腥臭。
街上仿佛已没了人,道路好象忽然加宽了许多,空旷而没有一点凉气,白花花的令人害怕。
祥子不知怎么是好了,低着头,拉着车,极慢的往前走,没有主意,没有目的,昏昏沉沉的,身上挂着一层粘汗,发着馊臭的味儿。
走了会儿,脚心和鞋袜粘在一块,好象踩着块湿泥,非常的难过。
本来不想再喝水,可是见了井不由的又过去灌了一气,不为解渴,似乎专为享受井水那点凉气,由口腔到胃中,忽然凉了一下,身上的毛孔猛的一收缩,打个冷战,非常舒服。
喝完,他连连的打嗝,水要往上漾
走一会儿,坐一会儿,他始终懒得张罗买卖。
一直到了正午,他还觉不出饿来。
想去照例的吃点什么,看见食物就要恶心。
胃里差不多装满了各样的水,有时候里面会轻轻的响,象骡马似的喝完水肚子里光光光的响动。
拿冬与夏相比,祥子总以为冬天更可怕。
他没想到过夏天这么难受。
在城里过了不止一夏了,他不记得这么热过。
是天气比往年热呢,还是自己的身体虚呢
这么一想,他忽然的不那么昏昏沉沉的了,心中仿佛凉了一下。
自己的身体,是的,自己的身体不行了
他害了怕,可是没办法。
他没法赶走虎妞,他将要变成二强子,变成那回遇见的那个高个子,变成小马儿的祖父。
祥子完了
正在午后一点的时候,他又拉上个买卖。
这是一天里最热的时候,又赶上这一夏里最热的一天,可是他决定去跑一趟。
他不管太阳下是怎样的热了:假若拉完一趟而并不怎样呢,那就证明自己的身子并没坏;设若拉不下来这个买卖呢,那还有什么可说的,一个跟头栽死在那发着火的地上也好
刚走了几步,他觉到一点凉风,就象在极热的屋里由门缝进来一点凉气似的。
他不敢相信自己;看看路旁的柳枝,的确是微微的动了两下。
街上突然加多了人,铺户中的人争着往外跑,都攥着把蒲扇遮着头,四下里找:“有了凉风
有了凉风
凉风下来了
”大家几乎要跳起来嚷着。
路旁的柳树忽然变成了天使似的,传达着上天的消息:“柳条儿动了
老天爷,多赏点凉风吧
” 还是热,心里可镇定多了。
凉风,即使是一点点,给了人们许多希望。
几阵凉风过去,阳光不那么强了,一阵亮,一阵稍暗,仿佛有片飞沙在上面浮动似的。
风忽然大起来,那半天没有动作的柳条象猛的得到什么可喜的事,飘洒的摇摆,枝条都象长出一截儿来。
一阵风过去,天暗起来,灰尘全飞到半空。
尘土落下一些,北面的天边见了墨似的乌云。
祥子身上没了汗,向北边看了一眼,把车停住,上了雨布,他晓得夏天的雨是说来就来,不容工夫的。
刚上好了雨布,又是一阵风,黑云滚似的已遮黑半边天。
地上的热气与凉风搀合起来,夹杂着腥臊的干土,似凉又热;南边的半个天响晴白日,北边的半个天乌云如墨,仿佛有什么大难来临,一切都惊慌失措。
车夫急着上雨布,铺户忙着收幌子,小贩们慌手忙脚的收拾摊子,行路的加紧往前奔。
又一阵风。
风过去,街上的幌子,小摊,与行人,仿佛都被风卷了走,全不见了,只剩下柳枝随着风狂舞。
云还没铺满了天,地上已经很黑,极亮极热的晴午忽然变成黑夜了似的。
风带着雨星,象在地上寻找什么似的,东一头西一头的乱撞。
北边远处一个红闪,象把黑云掀开一块,露出一大片血似的。
风小了,可是利飕有劲,使人颤抖。
一阵这样的风过去,一切都不知怎好似的,连柳树都惊疑不定的等着点什么。
又一个闪,正在头上,白亮亮的雨点紧跟着落下来,极硬的砸起许多尘土,土里微带着雨气。
大雨点砸在祥子的背上几个,他哆嗦了两下。
雨点停了,黑云铺匀了满天。
又一阵风,比以前的更厉害,柳枝横着飞,尘土往四下里走,雨道往下落;风,土,雨,混在一处,联成一片,横着竖着都灰茫茫冷飕飕,一切的东西都被裹在里面,辨不清哪是树,哪是地,哪是云,四面八方全乱,全响,全迷糊。
风过去了,只剩下直的雨道,扯天扯地的垂落,看不清一条条的,只是那么一片,一阵,地上射起了无数的箭头,房屋上落下万千条瀑布。
几分钟,天地已分不开,空中的河往下落,地上的河横流,成了一个灰暗昏黄,有时又白亮亮的,一个水世界。
祥子的衣服早已湿透,全身没有一点干松地方;隔着草帽,他的头发已经全湿。
地上的水过了脚面,已经很难迈步;上面的雨直砸着他的头与背,横扫着他的脸,裹着他的裆。
他不能抬头,不能睁眼,不能呼吸,不能迈步。
他象要立定在水中,不知道哪是路,不晓得前后左右都有什么,只觉得透骨凉的水往身上各处浇。
他什么也不知道了,只心中茫茫的有点热气,耳旁有一片雨声。
他要把车放下,但是不知放在哪里好。
想跑,水裹住他的腿。
他就那么半死半活的,低着头一步一步的往前曳。
坐车的仿佛死在了车上,一声不出的任着车夫在水里挣命。
雨小了些,祥子微微直了直脊背,吐出一口气:“先生,避避再走吧
” “快走
你把我扔在这儿算怎回事
”坐车的跺着脚喊。
祥子真想硬把车放下,去找个地方避一避。
可是,看看身上,已经全往下流水,他知道一站住就会哆嗦成一团。
他咬上了牙,郯着水不管高低深浅的跑起来。
刚跑出不远,天黑了一阵,紧跟着一亮,雨又迷住他的眼。
拉到了,坐车的连一个铜板也没多给。
祥子没说什么,他已顾不过命来。
雨住一会儿,又下一阵儿,比以前小了许多。
祥子一气跑回了家。
抱着火,烤了一阵,他哆嗦得象风雨中的树叶。
虎妞给他冲了碗姜糖水,他傻子似的抱着碗一气喝完。
喝完,他钻了被窝,什么也不知道了,似睡非睡的,耳中刷刷的一片雨声。
到四点多钟,黑云开始显出疲乏来,绵软无力的打着不甚红的闪。
一会儿,西边的云裂开,黑的云峰镶上金黄的边,一些白气在云下奔走;闪都到南边去,曳着几声不甚响亮的雷。
又待了一会儿,西边的云缝露出来阳光,把带着雨水的树叶照成一片金绿。
东边天上挂着一双七色的虹,两头插在黑云里,桥背顶着一块青天。
虹不久消散了,天上已没有一块黑云,洗过了的蓝空与洗过了的一切,象由黑暗里刚生出一个新的,清凉的,美丽的世界。
连大杂院里的水坑上也来了几个各色的蜻蜓。
描写虎妞片段: “不喝就滚出去;好心好意,不领情是怎着
你个傻骆驼
辣不死你
连我还能喝四两 呢。
不信,你看看
”她把酒盅端起来,灌了多半盅,一闭眼,哈了一声。
举着盅儿:“你喝
要不我揪耳朵灌你
” 她的脸是离他那么近,她的衣裳是那么干净光滑,她的唇是那么红,都使他觉到一种新 的刺激。
她还是那么老丑,可是比往常添加了一些活力,好似她忽然变成另一个人,还是她,但多了一些什么。
她今天也异样,不知是电灯照的,还是擦了粉,脸上比平日白了许多;脸上白了些,就掩去好多她的凶相。
嘴唇上的确是抹着点胭脂,使虎妞带出些媚气;祥子看到这里,觉得非常的奇怪,心中更加慌乱,因为平日没拿她当过女人看待,骤然看到这红唇,心中忽然感到点不好意思。
她上身穿着件浅绿的绸子小夹袄,下面一条青洋绉肥腿的单裤。
绿袄在电灯下闪出些柔软而微带凄惨的丝光,因为短小,还露出一点点白裤腰来,使绿色更加明显素净。
下面的肥黑裤被小风吹得微动,象一些什么阴森的气儿,想要摆脱开那贼亮的灯光,而与黑夜联成一气。
祥子不敢再看了,茫然的低下头去,心中还存着个小小的带光的绿袄。
虎姑娘一向,他晓得,不这样打扮。
以刘家的财力说,她满可以天天穿着绸缎,可是终日与车夫们打交待,她总是布衣布裤,即使有些花色,在布上也就不惹眼。
祥子好似看见一个非常新异的东西,既熟识,又新异,所以心中有点发乱。
虎妞脸上的神情很复杂:眼中带出些渴望看到他的光儿;嘴可是张着点,露出点儿冷笑;鼻子纵起些纹缕,折叠着些不屑与急切;眉棱棱着,在一脸的怪粉上显出妖媚而霸道。
看见祥子出来,她的嘴唇撇了几撇,脸上的各种神情一时找不到个适当的归束。
她咽了口吐沫,把复杂的神气与情感似乎镇压下去,拿出点由刘四爷得来的外场劲儿,半恼半笑,假装不甚在乎的样子打了句哈哈:“你可倒好
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头啊
”她的嗓门很高,和平日在车厂与车夫们吵嘴时一样。
说出这两句来,她脸上的笑意一点也没有了,忽然的仿佛感到一种羞愧与下贱,她咬上了嘴唇。
虎妞有了孕,这回是真的。
祥子清早就出去,她总得到八九点钟才起来;怀孕不宜多运动是传统的错谬信仰,虎妞既相信这个,而且要借此表示出一些身分:大家都得早早的起来操作,唯有她可以安闲自在的爱躺到什么时候就躺到什么时候。
到了晚上,她拿着个小板凳到街门外有风的地方去坐着,直到院中的人差不多都睡了才进来,她不屑于和大家闲谈。
虎妞的“月子”①是转过年二月初的。
自从一入冬,她的怀已显了形,而且爱故意的往外腆着,好显出自己的重要。
看着自己的肚子,她简直连炕也懒得下。
作菜作饭全托付给了小福子,自然那些剩汤腊水的就得教小福子拿去给弟弟们吃。
这个,就费了许多。
饭菜而外,她还得吃零食,肚子越显形,她就觉得越须多吃好东西;不能亏着嘴。
她不但随时的买零七八碎的,而且嘱咐祥子每天给她带回点儿来。
恶作剧之吻1(31集)里 江直树吻袁湘琴5次分别是哪几集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 不是生与死的距离 而是我站在你的面前 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 不是我站在你的面前 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而是爱到痴迷 却不能说我爱你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 不是我不能说我爱你 而是想你痛彻心脾 却只能深埋心底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 不是我不能说我想你 而是彼此相爱 却不能够在一起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 不是彼此相爱 却不能在一起 而是明明无法抵挡这一股气息 却还得装作毫不在意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 不是明明无法抵挡这一股气息 却还得装作毫不在意 而是用一颗冷漠的心 在你和爱你的人之间 掘了一条无法跨越的沟渠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 不是树与树的距离 而是同根生长的树枝 却无法在风中相依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 不是树枝无法相依 而是相互了望的星星 却没有交汇的轨迹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 不是星星之间的轨迹 而是纵然轨迹交汇 却在转瞬间无处寻觅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 不是瞬间便无处寻觅 而是尚未相遇 便注定无法相聚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 是鱼与飞鸟的距离 一个在天 一个却深潜海底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 不是生与死的距离 而是我站在你的面前 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 不是我站在你的面前 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而是爱到痴迷 却不能说我爱你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 不是我不能说我爱你 而是想你痛彻心脾 却只能深埋心底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 不是我不能说我想你 而是彼此相爱 却不能够在一起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 不是彼此相爱 却不能在一起 而是明明无法抵挡这一股气息 却还得装作毫不在意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 不是明明无法抵挡这一股气息 却还得装作毫不在意 而是用一颗冷漠的心 在你和爱你的人之间 掘了一条无法跨越的沟渠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 不是树与树的距离 而是同根生长的树枝 却无法在风中相依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 不是树枝无法相依 而是相互了望的星星 却没有交汇的轨迹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 不是星星之间的轨迹 而是纵然轨迹交汇 却在转瞬间无处寻觅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 不是瞬间便无处寻觅 而是尚未相遇 便注定无法相聚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 是鱼与飞鸟的距离 一个在天 一个却深潜海底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生和死 而是我就站在你面前 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飞鸟集》 泰戈尔
我住酒店,突然流鼻血把床单弄脏了,会不会要赔钱啊
赔钱多少,要是狮子大开口怎么办
如果不是很大的面积可以自己处理,看不出来就可以了,在床单下垫上卫生纸上面用沾湿的毛巾擦拭就可以了去除了
酒店不会为难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