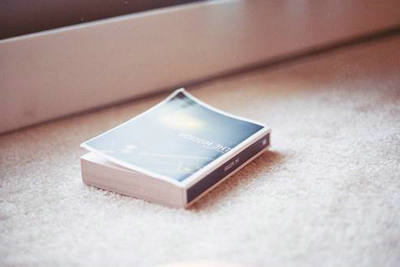求有关爱情的戏曲
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红楼梦》、《白蛇传》、《孔雀东南飞》、《陆游与唐琬》京剧:《白蛇传》《生死恨》《李慧娘》(越剧的也有)川剧:《柳荫记》《红梅记》黄梅戏:《天仙配》、《牛郎织女》、《槐荫记》评剧:《相寺树》(这个最早是越剧剧目)
越剧《十八相送》是描写了哪段古代爱情故事中的情节
梁山伯与祝英台
急急急,谁知道越剧里有没有特别凄美的爱情故事
求详细的故事内容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
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唐代诗人孟郊的一首《游子吟》,形象生动,情真意切,吟唱出多少远行游子的心声,更道出了天下母亲的无限牵挂。
在那个群星璀璨的唐朝,孟郊未必算得上是最优秀的,但此中所蕴藉的游子情怀,却别有一种身影茕然的惆怅和依恋,就像他一生的坎坷,最堪垂悯而承载母爱的伟大。
钱钟书在《谈艺录》中说:“史必征实,诗可凿空。
”其解诗之道,不求以诗证史,而以艺论诗,讲究诗的语言修辞、情感意境。
颜全毅编剧、杨小青导演的越剧《游子吟》,取意“游子”这一意象,正是“凿空”为孟郊立传的壁障,非常真诚真挚地讲述了母子之间的情感。
编剧和导演都十分熟悉越剧,取意而写意,本是他们所擅长的。
在孟郊乏善可陈的人生经历和十分有限的史料记载中,越剧《游子吟》选择了进入诗歌意境的合适角度和方式。
全剧通过母亲两次送孟郊、孟郊最后送母亲的“三送”,建立了全剧的情感关系。
它并不泛泛地描述赶考和送别,而是把孟郊的爱情、婚姻和功名诉求的冲突,捏揉进母子关系之中,让全剧的戏剧冲突、情感表达丰盈起来。
对于一个孤儿寡母的家庭,科考功名几乎是所有的期盼。
母亲明明看到孟郊与乔心盈青梅竹马、两情相悦,但面对家境的差距、乔家要告官剥夺孟郊功名身份的威胁,她只好狠心拆散两人。
这对孟郊的打击是巨大的。
他的沉沦落魄成了推进戏剧冲突的关键。
孟郊冷待妻子、酗酒撒疯,他不能理解母亲的苦心,质问母亲。
母亲是过来人,可母亲又何曾是过来人呢
孟郊和母亲,都在摸着石头过河。
“儿啊儿,你怎知世上做娘无人教,全凭初心一世修”,母亲教导孟郊如何做人,凭的就是那一片初心和苦心。
这一大段唱词唱腔,情感饱满酣畅、直钻人心,是极其感人的。
“游子”所对应的不单是对母亲、家庭的牵挂,这牵挂还包括对故乡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和无数的人与事。
母亲是那个最显性的形象,而乔心盈所代表的年少时的恋情,则是投射内心的隐性形象。
在越剧《游子吟》中,这两个形象是交叠的,全剧的戏剧关系、情感关系都由此产生和蕴藉。
她们都是游子牵挂的心念,从而在诗歌意境、戏剧情境确保了情感和逻辑的整一性。
更进一步,也超出了一般抽象的游子咏叹,不仅让人物关系变得具体、生动和感人,同时也获得了人生的普遍意义。
这是《游子吟》诗情酝酿的针线所在。
越剧《游子吟》很诗意,画面简洁,清新淡雅,舞美、灯光等外部形式的处理尤其娴熟得当。
比如,开场时的调度。
母亲送行未已,灯光乍变,乔心盈出现,告知家里逼嫁的情况。
导演不用幕次而用灯光来实现场景的切换,节奏紧凑,简洁明快,短短时间内就完成了戏剧性的生成、人物关系的确立。
其中对母子送别的处理,孟郊不让母亲送,裴月娘偷偷跟随,转台缓缓转动,山水草木,人行且行。
导演很注意匀称,也明白行走带来的视角转移,让对手的两组演员前与后、左与右适时调动位置,画面充满了流动的美感。
最具诗意的是导演用了多处对比效果的调度和场面。
比如,无幕次的灯光切换,让情节紧凑、悬念陡生;乔心盈出嫁,悲剧以欢乐的场面呈现,加上音乐的喜、唱腔的悲形成对比,让人别有幽愁暗恨生。
静谧之处,满月悬窗,偌大的舞台砌末廖廖,一人一灯一轮月,写尽了临行密密缝的慈母意。
月色的亮,灯盏的红,与母亲渐渐衰老的形象相互映衬;光阴如月,青春曾红,却再难回到她身上。
此外,江南水乡,画眉桥头,渡口送别,这些环境和情境,不仅提供规定情境,也还别有诗意。
比如,舞台背幕的水乡,恰是笔毫蘸墨的造型;明月窗前的窗格,又是竹简垂挂的风韵,等等,似同时提醒观众,孟郊是一个诗人。
在以《西厢记》《陆游与唐琬》《藏书之家》等为代表的一批“文人越剧”确立强烈的文人主体意识之后,近些年来越剧界似乎都在探寻新的方向。
《甄嬛传》涉足宫廷题材,青睐其中的宏富复杂;《江南好人》偏于都市化,掺入爵士舞,这些都是例子。
作为“文人越剧”的开创性导演,杨小青似乎也希望找到一个突破和跨越的契机。
她是很有诗人气质的导演,很擅长以意象赋诗心,“宫廷”和“都市”都不在她的心境之内。
相对于强化主体意识的精英思维,颜全毅没有仰望孟郊,视角和情感更加民间。
或许,这种平视恰好打动了导演。
在孜孜不倦的诗意探索中,诗意的本质是什么
民间显然提供了考察维度。
剧中的裴月娘由王滨梅饰演,表演甚为工稳,把一个教子有方的母亲在不同年龄段的形象刻画得极为感人。
最感人的两段唱:一是孟郊获知真相质问时,母亲的那段“你问娘,娘能问谁去”,若记忆无误,应是用的清板慢唱,真是委婉深挚,一唱三叹,把母亲鳏寡受苦的身世、望子成龙的期盼、希望宽宥的无措自责和无奈“世上做娘无人教,全凭初心一世修”的命运感全带出来了。
二是母亲打了孟郊后唱的“一记巴掌打在你脸上真响亮”,唱得急切、痛切,偏越剧唱腔自有回转润饰之意,虽似追云赶月,却能沉坠留韵,把唱词最后“寒风飞雪、苦苦站立、悲伤苍凉、白发落泪的老亲娘”的意境和形象都唱了出来。
孟郊由尹派青年演员汪舟格扮演。
他嗓音甚佳,唱腔醇厚隽永,尤其到中后场,情绪情感与唱腔表演的磨合渐趋天然,尹派塑造人物性格的优势越发凸显了出来。
值得商榷的地方,一是开始演孟郊青葱年少时显过稚;二是表演动作过多,不像越剧的范儿,而且与孟郊孤僻内向的性格有距离。
至于最后步入中老年的孟郊(包括相应渐老的裴月娘)在装束、扮相上是否需要做老,或另可探讨;但那种历经宦海沉浮、沧桑坎坷的内心支撑,或可作远近处理,起欲悠远,转要沉坠,余味平和,方可得冷清、苍茫之意。
可以商榷的地方还有三处:一是在全剧把重心放到母亲身上后,孟郊的诗人身份虽然不那么重要了,但这是他写出诗篇的前提,似乎不应忽略。
二是“回送”有刻意之嫌。
儿子为官,母亲何必回老家去呢
同时,这样也显得重心在“报得三春晖”,是喜剧团圆,但诗歌《游子吟》里最重要的心境,恰恰是“报得三春晖”成为一个难以实现的心愿,方显意境更阔大、更隽永。
三是结尾处孟郊已步入中老年,不应如年少时喜怒形于色。
青山隐隐,流水迢迢,唯此情化作乌云坠,作诗即可,天地可鉴,喊出献诗母亲,大可不必。
尽管如此,越剧《游子吟》无疑是感人至深的。
颜全毅的创作总能别具生趣、给人启示。
同时,在诗化越剧、文人越剧、都市越剧之外,杨小青导演对民间情感的关注让人期待,甚至可能打开一个崭新的视野——以现代立场重返乡土民间,拾掇、缝补乃至编织新的乡土,反映可能被忽视的人们的精神世界。
重点不仅是伦理情感,更在于贯穿其中的情感逻辑和人性幽微所反映出的人的现代意识。
越剧《十八相送》是描写了哪段古代爱情故事中的情节
梁山伯与祝英台\ 十八相送是梁山伯与祝英台故事中的一段,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经典爱情早已深深的进入我们每个人的心里,他们用生命来歌颂爱情。
如今,我们只能用那悠悠的歌声纪念纪念他们,纪念他们那永远不朽的爱情。
悠悠清唱十八相送。
《十八相送》节选自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该部分是该剧中的经典唱段。
越剧《红楼梦》宝黛爱情的描写与以往的爱情描写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小说的第三回,黛玉因为母亲去世,被外祖母史老太君(宝玉的奶奶,书中一般称作贾母)接到贾府。
后来就听二舅母(王夫人)说:她有个儿子是个“混世魔王”,“你以后不要睬他”。
黛玉知道二舅母说的便是衔玉而生的那个表哥贾宝玉。
正不知道该怎么对待他,宝玉就来了。
于是二人相见认识。
按照书中的写法,他们是前世就认识的,贾宝玉是神英侍者,黛玉是绛株仙子,神英侍者为快要枯萎的绛株草浇水使之活下来,绛珠草决心用一生的眼泪报答他,这就是木石前盟,这是一种带有神话色彩的浪漫写法。
所以回到现实中,他们就一见钟情,并慢慢深厚了感情。
宝黛爱情的发展还体现在第二十三回《 西厢记妙词通戏语 牡丹亭艳曲警芳心 》之中。
先看:“(宝玉)谁想静中生烦恼,忽一日不自在起来,这也不好,那也不好,出来进去只是闷闷的.园中那些人多半是女孩儿,正在混沌世界,天真烂漫之时,坐卧不避,嘻笑无心,那里知宝玉此时的心事. 那宝玉心内不自在,”标准的青春期烦躁。
于是有了共读西厢,这时二人的关系进入初恋。
越剧《十八相送》是描写了哪段古代爱情故事中的情节
梁山伯与祝英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