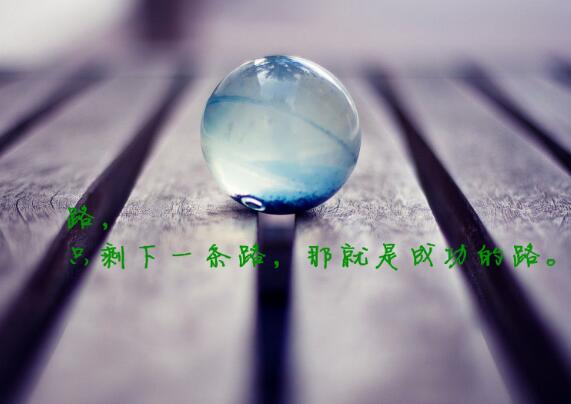泰山日出徐志摩中写太阳的句子
我们在泰山顶上看出太阳。
在航过海的人,看太阳从地平线下爬上来
比徐志摩的泰山日出里太阳升起的描写还美的古诗是哪首
泰山日出 铎来信要我在《月报》的泰戈尔号上说几句话也曾答应了,但时 游济南游泰山游孔陵,太乐了,一时竟拉不拢心思来做整篇的文字,一直埃到现在期限 快到,只得勉强坐下来,把我想得到的话不整齐的写出。
我们在泰山顶上看出太阳。
在航过海的人,看太阳从地平线下爬上来,本不是奇事; 而且我个人是曾饱饫过江海与印度洋无比的日彩的。
但在高山顶上看日出,尤其在泰山 顶上,我们无餍的好奇心,当然盼望一种特异的境界,与平原或海上不同的。
果然,我 们初起时,天还暗沉沉的,西方是一片的铁青,东方些微有些白意,宇宙只是——如用 旧词形容——一体莽莽苍苍的。
但这是我一面感觉劲烈的晓寒,一面睡眼不曾十分醒豁 时约略的印象。
等到留心回览时,我不由得大声的狂叫——因为眼前只是一个见所未见 的境界。
原来昨夜整夜暴风的工程,却砌成一座普遍的云海。
除了日观峰与我们所在的 玉皇顶以外,东西南北只是平铺着弥漫的云气,在朝旭未露前,宛似无量数厚毳长绒的 绵羊,交颈接背的眠着,卷耳与弯角都依稀辨认得出。
那时候在这茫茫的云海中,我独 自站在雾霭溟蒙的小岛上,发生了奇异的幻想—— 我躯体无限的长大,脚下的山峦比例我的身量,只是一块拳石;这巨人披着散发, 长发在风里像一面墨色的大旗,飒飒的在飘荡。
这巨人竖立在大地的顶尖上,仰面向着 东方,平拓着一双长臂,在盼望,在迎接,在催促,在默默的叫唤;在崇拜,在祈祷, 在流泪——在流久慕未见而将见悲喜交互的热泪…… 这泪不是空流的,这默祷不是不生显应的。
巨人的手,指向着东方—— 东方有的,在展露的,是什么
东方有的是瑰丽荣华的色彩,东方有的是伟大普照的光明出现了,到了,在这里了…… 玫瑰汁、葡萄浆、紫荆液、玛瑙精、霜枫叶——大量的染工,在层累的云底工作; 无数蜿蜒的鱼龙,爬进了苍白色的云堆。
一方的异彩,揭去了满天的睡意,唤醒了四隅的明霞—— 光明的神驹,在热奋地驰骋…… 云海也活了;眠熟了兽形的涛澜,又回复了伟大的呼啸,昂头摇尾的向着我们朝露 染青馒形的小岛冲洗,激起了四岸的水沫浪花,震荡着这生命的浮礁,似在报告光明与 欢欣之临莅…… 再看东方——海句力士已经扫荡了他的阻碍,雀屏似的金霞,从无垠的肩上产生, 展开在大地的边沿。
起……起……用力,用力。
纯焰的圆颅,一探再探的跃出了地平, 翻登了云背,临照在天空…… 歌唱呀,赞美呀,这是东方之复活,这是光明的胜利…… 散发祷祝的巨人,他的身彩横亘在无边的云海上,已经渐渐的消翳在普遍的欢欣里; 现在他雄浑的颂美的歌声,也已在霞采变幻中,普彻了四方八隅…… 听呀,这普彻的欢声;看呀,这普照的光明
这是我此时回忆泰山日出时的幻想,亦是我想望泰戈尔来华的颂词。
(原刊1923年9月《小说月报》第十四卷第九号) 注① 振铎,即郑振铎(1898—1958),作家、编辑、文学活动家。
他是文学研究会 发起人之一,当时正主编《小说月报》。
《泰山日出》是篇应命之作自不待言,这在文章的小序中已有说明(第一段即小序)。
更重要的是,泰戈尔作为东方文学的泰斗,不仅有“天竺圣人”之誉,还是获诺贝尔文 学奖的第一位世界性诗人。
在他一九二四年来华访问前夕,“泰戈尔热”已来势汹涌。
为“泰戈尔专号”写颂词,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
徐志摩以“泰山日出”来隐喻泰戈尔 的文学创作和来华访问,表达中国诗人对泰戈尔的敬仰的感情,真是一个卓越的比喻。
这是何等倾心的盼望、何等热烈的迎候,何等辉煌的莅临
诗人以他才华横溢的想象和 语言,描绘了一幅令人难忘的迎日图:
泰山日出是否只是对日出的描写?还表达了作者怎样的感情?快
急!
有4层意思 ①对的景象的喜爱和赞美之情②对东方文明的赞美③对光明的渴望和对理想的追求④对即将来到中国的景仰和欢迎之情
日出(刘白羽),泰山日出(徐志摩)的 相同点和不同点
在刘白羽的《日出》中,日出景象无疑是文章的主体,但是作者直接写日出感受的篇幅只有五分之二,将近五分之二的篇幅是引用别人的文章,还有五分之一写的是在黄山没有看成日出。
把这么多的文字花在别的方面是不是喧宾夺主呢
好像也不是。
如果一上来就写如何在飞机上看到日出,看完了,文章也就完成了,当然也是可以的,但可能给人以单调之感。
而有了前面这一切,文章就显得比较丰富,不但是语言上丰富,而且想象、情感、色彩上也丰富。
俗语说,红花还要绿叶扶。
这五分之三的篇幅是一种陪衬,或者说是一种烘托。
这有点近似国画上所说的“烘云托月”。
当然,这并不是说写日出非这样写不可。
有时不用烘托,直接描写也是可以的。
小学五年级的课本上有巴金的《海上日出》,该文就没有烘托,几乎全是直接描写。
刘白羽和巴金的风格完全不同,他的这篇《日出》风格多样化。
当然,单纯也有单纯的美。
笼统地评说单纯或多样化是没有意义的,要有比较的对象,也就是要有参照系。
这参照系首先就是指文体,其次是风格。
同样的文体,就要看风格。
显然,和刘白羽的风格比较起来,巴金的就显得单纯多了。
巴金的感觉是蓝色的天空,红色的霞,黑色的、紫色的云,光亮夺目的阳光,等等,而且这种光亮的效果有两种:一是射得眼睛发痛,二是把云、海和作者照得透明。
文章不长,应该说视角和层次并不单调,但是,如果刘白羽满足于巴金这样的感觉,那他的文章就不用写了。
刘白羽之所以要用同样的题目再写一下,肯定是因为他觉得自己有超过前辈的地方。
刘白羽引用了海涅、屠格涅夫的文章,却没有引用巴金的,可能并不是偶然。
而引用海涅和屠格涅夫的文章,不是为了显示这样的描写无以复加,也不是为了作陪衬,而是另有一番用心——在这些经典的基础上,把日出的抒写推向一个新的水准。
他的突破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心理背景上的反差。
感受日出的辉煌,在“没有一点准备、一丝预料的时刻”,为了强调突遇“无与伦比的光华、丰采”的惊异,前面特意写了两次失望,一次是在印度——看日出的胜地,一次是在黄山,遭遇了和著名旅行家徐霞客一样的失望。
第二,在光和色的对比上。
当然,巴金、屠格涅夫写日出,光和色也是有对比的,但是刘白羽在色彩层次上更显丰富。
先是色调和色温的对比。
“黑沉沉的浓夜”“一线微明”“暗红色长带”“清冷的淡蓝色晨曦”“变为磁蓝色的光芒”“红海上簇拥出一堆堆墨蓝色云霞”“墨蓝色云霞里矗起一道细细的抛物线”“红得透亮,闪着金光”。
这里,不但有色彩的对比,而且有色调、色温的对比,蓝色(其间还有磁蓝和淡蓝的层次)是“清冷”的,而红色、亮色(其间还有暗红,红得透亮的层次)是温暖的,是“沸腾的”。
其次是静态和动态的对比。
飞机在不断上升,抛开地面,“不知穿过多少云层”,把夜空“愈抬愈远”,这种动的幅度是很宏大的。
而另一方面,则是宁静的:地面是“黑沉沉的”,“飞机好像唯恐惊醒人们的安眠,马达声特别轻柔”。
不但有动静对比,而且有转化,由冷变暖,由静变动——“一转眼,清冷的晨曦变为磁蓝色的光芒”“原来的红海上簇拥出一堆堆墨蓝色云霞”“突然间从墨蓝色云霞里矗起一道细细的抛物线,这线红得透亮,闪着金光,如同沸腾的溶液一下抛溅上去,然后像一支火箭一直向上冲”。
这一句特别值得称道,这是刘白羽式的创造,是固态和液态的转化,太阳本来是有固定形状的,这里却以液态(“沸腾”)来形容,显得特别新奇。
再次是情景的对比。
刘白羽在飞机上惊奇地领略日出的壮观景象,用了一系列辉煌的语汇,诸如:晶光耀眼、火一般鲜红、火一般强烈。
瞬息之间,平静的心态转化为激情状态。
一切景象都染上了激情的色彩:“一眨眼工夫,我看见飞机的翅膀红了,窗玻璃红了,机舱座里每一个酣睡者的面孔红了。
”红是火热的色彩,而在汉语里“热”与“闹”是自然地联系在一起的,正如“冷”与“静”联系在一起一样。
接下来,刘白羽激情的状态又转化为宁静的状态:这时一切一切都宁静极了,宁静极了。
整个宇宙就像刚诞生过婴儿的母亲一样温柔、宁静,充满着清新、幸福之感……我靠在软椅上睡熟了。
醒来时我们的飞机正平平稳稳,自由自在,向我的亲爱的祖国、向太阳升起的地方航行。
本来,这里是文章的高潮,是感情的高潮,是强烈的激情,是刚性的,但是刘白羽却把它和柔性结合在一起,把激情与平静自然地统一起来,以显示出一种“宁静”的“幸福感”,其特点是以一种内心的、无声的体验,进入一种庄严的、思索的境界。
最后,顺理成章地把这种幸福的体验和庄严的思索升华为政治的抒情。
这种升华,就是在半个世纪后的今天读起来,也并不太生硬,因为其间从个人的体悟到集体话语的过渡相当自然,这得力于一个关键词的运用,那就是说,飞机向“亲爱的祖国、向太阳升起的地方航行”。
有了这样的过渡,下面写道:这时,我深切感到这个光彩夺目的黎明,正是新中国瑰丽的景象……我在体会着“我们是早上六点钟的太阳”这一句诗那最优美、最深刻的含意。
从大自然的感受上升为政治的激情抒发,是刘白羽的惯用手法。
也许,今天的青少年读者,对他这种强烈的政治抒情并不一定能够全部体验,但是,仍然可以从中感受到上个世纪中期,中国知识分子浪漫主义的、崇高的追求。
(二)从表面上看,徐志摩笔下的日出和刘白羽笔下的日出,最明显的不同就是一个从泰山上看,一个从飞机上看。
但是,光看到这样的区别是肤浅的。
文章的精神不在于写了些什么,从什么角度看,而在于用什么样的情绪去感受。
读者已经习惯了一般的写法:首先集中笔力描绘出日出的壮丽景观,然后慢慢激动起来。
但是,徐志摩却不是这样。
首先,他不太着重写景,因为在他看来,最初的印象是很平淡的,西方一片铁青,东方有点发白,只能用“旧词”——“莽莽苍苍”来形容。
此时的心情,也不是很兴奋的,有点懒洋洋的观感,等到仔细留心再看时,却一下子兴奋、激动起来,不由得大声狂叫。
要注意,这样的写法和刘白羽是很不相同的。
刘白羽是把景象写透了,才激动起来,慢慢诱导读者激动,避免读者跟不上趟而无动于衷。
而徐志摩这种写法的好处在于调动读者情绪,和作者同步发展,循序渐进,层次井然。
但是,这并不是唯一的途径,徐志摩和刘白羽不同,他是个浪漫主义诗人,他的情绪来得快,使用的方法也与刘白羽恰恰相反,先不讲任何理由,突然就激动起来,引起读者的惊异,然后以戏剧性的悬念调动读者的阅读兴趣,维持读者的内在注意力。
这也是一种方法,是浪漫诗人比较常用的手法。
和一般抒情散文不同,不是情与景的平衡发展,而是以情感为纲,以情感为主导。
描绘的效果,得力于组合性的比喻。
作者把云海比喻为绵羊,由绵羊联想,引申出羊绒、羊角、羊颈的交接,应该说,是挺形象的。
可是这时诗人却激动莫名,由于站在山峰顶端,“发生了奇异的幻想”——自己化为一个巨人,脚下的山峦变得像拳头一样小,自己站在大地的顶尖上,长发变成墨色的旗帜,平举着一双长臂,向着东方,默默地呼唤、祈祷,而且流下了热泪。
为什么会激动到这种程度呢
这里有几个关键词:崇拜、久慕未见、悲喜交互。
一个也不要放过,要弄明白。
崇拜、久慕未见,比较好解释,因为在浪漫诗人看来,大自然的景象太动人了,太值得崇拜了。
长期地向往,却未能得见;一旦见到,就激动得不能自制。
但是,理解悲喜交互就有点难度。
喜是很好理解的,因为美好的景色而喜。
悲呢
这个问题,我们先留着到后面去试着解释。
下面有一个词更为关键:东方。
(巨人的手指向东方。
)这里显然不是地理学意义上的东方,而有着更多的文化的、历史的含义。
请看:东方有的,在展露的,是什么
东方有的是瑰丽荣华的色彩,东方有的是伟大普照的光明出现了……这里的“瑰丽荣华的色彩”“伟大普照的光明”,显然不仅仅是大自然的现象,而是一种文化的象征。
东方的曙光,东方的觉醒,是重点,对于这一点,徐志摩以更为华彩的语言来美化:玫瑰汁、葡萄浆、紫荆液、玛瑙精、霜枫叶……这样的色彩,比最初使诗人激动的云层要强烈得多了,他甚至不惜用堆砌的方法,集中了这么多富丽堂皇的词语,充分表现了诗人的浪漫情感和文采。
但是,色彩还是表层的,内涵在其深层,如果仅仅限于表层,文章的深度就可能受到局限。
幸而,诗人把自己的思想逐步透露:一方的异彩,揭去了满天的睡意,唤醒了四隅的明霞——光明的神驹,在热奋地驰骋……这里的“异彩”之所以值得赞美,是因为驱除了“满天的睡意”。
天是没有什么睡意的,这不是写实,而是象征,把这里的“睡意”和“东方”联系起来,就不难理解了,这象征着东方巨人的觉醒。
要注意,本文写于1923年,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期,文中的“光明的神驹”,提示了时代背景。
类似的提示还有:再看东方——海句力士已经扫荡了他的阻碍……歌唱呀,赞美呀,这是东方之复活,这是光明的胜利……这里的“海句力士(大力士)”“复活”“光明”,都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欢呼和礼赞。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礼赞,不仅是对时代的,而且是对自我的。
文章到了最后,诗人特别强调了这一点:散发祷祝的巨人,他的身彩横亘在无边的云海上,已经渐渐的消翳在普遍的欢欣里……听呀,这普彻的欢声;看呀,这普照的光明
在文章最后,是光明的普照,这是“四方八隅”的欢歌,也是巨人心灵的光华,这是情绪的高潮,也是欢乐的高潮。
欢乐充斥着身体内外,可以说是一首精神解放的欢乐颂。
现在,再回答我们曾在本文前面留下的一个疑问:为什么诗人在初见泰山日出的时候,流下是“悲喜交互”的热泪
喜,已经得到充分的解释,可是悲从何来呢
如果光是自然景观的欣赏,是不可能有悲的成分的。
这里暗示的是东方巨人的觉醒,“驱除睡意”,这种睡意是历史的,是经历了漫长的痛苦和屈辱的,是充满着重重障碍的,而一旦觉醒,“扫荡阻碍”,并不是轻而易举的,这才令人悲喜交集。
这种悲喜交集,是历史的转折点决定的。
徐志摩是一个浪漫主义的热情诗人,在表现情绪上,具有足够的气魄,但是在表现历史感方面,是比较薄弱的。
这一点只要把本文和郭沫若的《凤凰涅槃》相比,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
在郭沫若笔下,凤凰是英勇地烧毁了旧世界,同时又自觉地烧毁了旧自我,在旧我毁灭之后,才获得了火中涅槃的永恒生命。
徐志摩的散文,在理解新文化运动的深度方面,显然是有局限的,因而在谈到“悲喜交互”时,难免给读者留下一些困惑。
最后总结一下,关于日出的美,我们已经读了两篇文章,两篇文章有共同之处,就是日出的美都与光华和温暖联系在一起,然后由光华和温暖激起了作者情感的特殊激动。
二者都美,哪一方面更重要呢
两篇都是抒情散文,文章的动人,是以情为主,还是以物象为主呢
看来应该是以情动人,但是,一般的情感,类似的情感,是不是都能动人呢
比如说,两个人的情感差不多,没有各自的特点,是不是一样能动人呢
绝对不能。
分析文章的重点就在于找到情感的特殊性、情感的区别,抓住了特点,才能抓住刘白羽和徐志摩的个性,体悟到他们发现、创造美的境界是不同的。
求徐志摩《泰山日出》的深层理解
《泰山日出》是篇应命之作自不待言,这在文章的小序中已有说明(第一段即小序)。
更重要的是,泰戈尔作为东方文学的泰斗,不仅有“天竺圣人”之誉,还是获诺贝尔文 学奖的第一位世界性诗人。
在他一九二四年来华访问前夕,“泰戈尔热”已来势汹涌。
为“泰戈尔专号”写颂词,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
徐志摩以“泰山日出”来隐喻泰戈尔 的文学创作和来华访问,表达中国诗人对泰戈尔的敬仰的感情,真是一个卓越的比喻。
这是何等倾心的盼望、何等热烈的迎候,何等辉煌的莅临
诗人以他才华横溢的想象和 语言,描绘了一幅令人难忘的迎日图: 我的躯体无限的长大,脚下的山峦比例我的身量,只是一块拳石;这巨人披着散发, 长发在风里像一面墨色的大旗,飒飒的在飘荡。
这巨人竖立在大地的顶尖上,仰面向着 东方,平拓着一双长臂,在盼望,在迎接,在催促,在默默的叫唤;在崇拜,在祈祷, 在流泪——在流久慕未见而将见悲喜交互的热泪…… 这泪不是空流的,这默祷不是不生显应的。
巨人的手,指向着东方—— 东方有的,在展露的,是什么
东方有的是瑰丽荣华的色彩,东方有的是伟大普照的光明——出现了,到了,在这 里了…… 这里的想象和构图都是不同凡响的。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文章通篇描写的只是泰山 看日出的情景和幻想,欢迎泰戈尔来华只在结尾提到。
诗人的潇洒,诗人的才华都体现 在这里:徐志摩并不把为泰戈尔来华写颂词的大事,当作一项精神负担,照样游山玩水, 乐而忘返。
他不想为文苦吟,而是兴之所至,全凭灵感。
但他能把切身的经验感受调动 起来,融入一种更有意味和张力的艺术创造,即使偷懒取巧,也表现出偷懒取巧的才气, 不失基本的艺术魅力和奇思妙笔。
正因为此,这篇《泰山日出》仍比一般平庸的颂词要 高明十倍。
这不仅体现在作者笔笔紧扣泰山日出的奇伟景观,却又每笔都蕴含着欢迎泰 戈尔的情思与赞美方面;而且反映在独特的个人经验与普遍情感的融合方面。
特别是前 面长风散发的祷祝巨人的描写,以及临结尾时写这巨人消翳在普遍的欢欣里,叫人产生 许多想象和联想,最能体现徐志摩的才情和创。
然而,这究竟是匆促成篇之作,诗人的才气也未能遮掩艺术上的粗糙。
首先是这篇 文章的文体感不强,前面一大段是散文的文笔,是细致的经验与感受的实写,而后面的 文字语气则明显是散文诗的,是抒情的、幻想的、暗示的。
这两种文笔虽然各自都很美, 但放在一起则很不和谐。
本来,传统的、经验的文体感不强也不要紧,伟大的作家往往 是新文体的创造家,只要自成一体,具有自身气脉、神韵的贯通和完整性。
艺术创格是 好事。
但问题在于这篇《泰山日出》恰恰气韵上前后不够贯通,没有浑融境界,不能自 成一格。
艺术创造毕竟不是一种可以矜才使气的工作,它需要的不仅是才华,还有全神 贯注的精神投入和艰苦的艺术经营。
完美的作品,总是才华与自觉艺术经营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