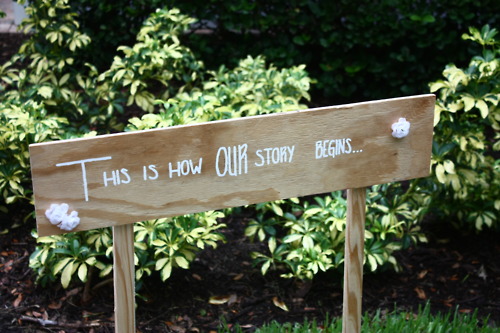想找一些像史铁生、海子等文人所写的文章和美的诗句
史铁生超越了自己的痛苦,升华了自己的生命,这个生命在最后不是走向世俗的轮回,而是走向了光明的无尽的解脱之境。
史铁生《我与地坛》中所描写景物的总体特点是什么
其作用是什么
文中的描写动静结合,生动、新奇、。
作者或捕捉静景物写“古殿檐头剥蚀璃”“门壁上淡褪的朱红”,用以表现地坛沧桑的历史;或描摹动态的景物,写“蚂蚁摇头晃脑捋着触须,猛然间想透了什么,转身疾行而去”,来表现渺小生命生存、思索、奋斗的快乐;写“露水在草叶上滚动、聚集,压弯了草叶轰然坠地摔开万道金光”表明即使短暂平凡的小生命也能创造出生命…… 作者残疾之后,地坛公园是他较长时间活动的场所,是这一独特“沉静”的环境,使他活过来,使他感悟到人生的艰难,从而产生了质的飞跃和超越。
这种环境“弥漫”着沉静的“光芒”,是培养他飞跃超越的土壤。
他感受到了“时间”无声无息的流逝,更看到了自己残疾的“身影”。
可见,这句话将环境、时间和个人的遭遇紧紧联在一起,揭示了时间的无情和现实的残酷,同时,也表现了作者不逃避、不懦弱、勇敢面对现实的坚强意志。
关于史铁生的作文
四十七年前,当轰隆隆的火车碾过他的身躯,他手中的诗集被抛在了铁轨上,还有他的灵魂。
海子自不被世人理解,他活在一个封闭的、充满了压抑的空间,于是,他用诗歌发泄,他不分昼夜的写诗去发表,出诗集。
然而旁人不理解他所处的世界,对他冷漠甚至冷嘲热讽,以至于在世时他没有一首让人赞不绝口的诗歌。
直至他死后,人们才幡然觉悟,纷纷在他的纪念日上赠花圈、慰问,开诗歌朗诵会。
海子是消极的,但也是环境所逼,那是他的无奈,他没有适应社会,于是,他便去了另一个国度。
“我想人不如死了好,不如不出生的好,不如压根儿没有这个世界的好。
可你并没有去死。
我又想到那是一件不必着急的事。
可是不必着急的事并不证明是一件必要拖延的事呀
你总是决定活下来,这说明什么
是的,我还是想活。
人为什么活着
因为人想活着。
”史铁生遇见了海子,他便会对他这么说。
他知道他的灵魂还在,一直都在,每一首海子的诗便可以跳出一个灵魂。
2010年12月31日,史铁生逝世,享年49岁。
我想,他死时必定怀着一种安然和恬淡,他珍惜且好好度过了自己的年华。
《我与地坛》中的那个青年史铁生指责《春天,十个海子》中的海子:“既然你向往‘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生活,为何还未等到,便匆匆辞于人世
”十个海子低下头沉思,不知道沉思的什么。
他自杀的那晚大脑不听使唤一般,迷气功的他以为道教巫徒操纵了他的大脑,所以才意识混乱的捧了几本自己的诗集,匆匆赶赴铁轨。
也许,有什么在召唤他。
青年史铁生又不客气地说道:“我当初腿瘸了,忍受下来了,成天无所事事地闲逛地坛,从未动过自杀的念头,因为我还有母亲,还有我未完成的梦。
”他顿了顿,语气缓了下来:“如果你还在的话,定能见证自己的成功。
”也是海子的承受能力不够,如果他能捱过当初,说不定现在他也还尚在人世。
他没有领会到生命的存在时神圣而不易的,他辜负了每一个爱他的人。
如果,我是说如果。
在很久以前,海子就遇见过《我与地坛》,并且像我一样,被它深深地感动,那么他的内心会不会柔软一点
史铁生适应了这个社会,并在逆境中顽强的存活下来,于是他便成了神话,撇开《我与地坛》,单是他的精神、经历,便是让人感动。
而海子,人们对他的感觉只有“悲痛”,他没有融入社会,人们也便会觉得他分外遥远,他也有一颗善良的心,一份美好的愿望,但他用错了方式。
唯一不变的,是他对诗歌的热情。
史铁生的死引起了轰动,全国上下几万人为之悲怆。
互联网、电视,报纸纷纷报道这一噩耗。
是的,只有人死了,人们才万般重视。
一番轰动之后,才会渐渐缓下来,相比于史铁生,海子的死在过去了47年之后,人们提起,便只有淡淡的哀愁。
人的肉体存活于世有限,但精神及留下的作品却可以超脱尘世,深深的镌刻在,亿万人的心中。
史铁生的骨灰被洒在了地坛之中,那个时候,想必他是微笑的。
当人们的悲痛褪去,便可怀着一种恬然与温馨的感觉,读他们的作品。
史铁生遇见海子,是两种精神的契合——两种迥然的生活态度,两个不同的灵魂,对生命和诗歌有着不同的坚守,带给人不一样的感动。
一个人活在不被理解的尘世中25年很不容易,而好好活着,更加伟大。
史铁生在《史铁生散文集》中写过哪些著名的话
太多了,觉得他的书让人心醉人所不能者,即是限制,即是残疾·我们生来孤单,无数的历史和无限的时间因而破碎成片断。
·左右苍茫时,总也得有条路走,这路又不能再用腿去趟,便用笔去找。
·在奥运口号“更快、更高、更强”之后,应该再加上“更美”。
·死是一件无须乎着急去做的事,是一件无论怎样耽搁也不会错过了的事,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
如果能够原谅我的残忍,他的不幸也是一种“幸运”。
二十一岁,他便被命运之手弃于轮椅中。
那可是个到处疯跑的年纪呀,他却只能在思绪中奔跑了,奔跑的,是他的痛苦。
他蜷缩在屋内的黑暗里,隐藏在地坛的角落里,他躲避着别人的目光,放弃了熊熊的激情。
他痛苦甚而愤恨,他质问着生与死,他探寻着意义。
而多少个明明灭灭的时光,他终于拾回了自己,终于找到了生命的意义。
生命的意义就在于生命的过程。
卓别林说,死亡迟早会来的,着什么急
好吧,那么做什么呢
他说,为了不致于死,写作吧。
于是他的文章,尽力去精彩;他的文章,也总有着淡淡的忧伤。
史铁生 说: 其实每时每刻我们都是幸运的,因为任何灾难的面前都可能再加上一个“更”字。
史铁生 说: 世界上的人很多,每个人的世界其实又很小,一个个小世界大约只在务实之际有所相关,一旦务虚,便很可能老死难相理解。
史铁生 说: 我看不见那个吹唢呐的人,唯唢呐声在星光寥寥的夜空里低吟高唱,时而悲怆时而欢快,时面缠绵时而苍凉,或许这几个词都不足以形容它,我清清醒醒地听出它响在过去,响在现在...史铁生 说: 时间限制了我们,习惯限制了我们,谣言般的舆论让我们陷于实际,让我们在白昼的魔法中闭目塞听不敢妄为。
史铁生 说: 大脑做不到心灵所能做到的一切。
心灵比大脑广阔得多,深远得多,复杂得多。
史铁生 说: 一个情人来说,不管多么漫长的时光也是稍纵即逝,那时他便明白,每一步每一步,其实一步步都是走在回去的路上。
当牵牛花初开的时节,葬礼的号角就已吹响。
史铁生 说: 命运而言,休论公道。
那么,一切不幸命运的救赎之路在哪里呢? 设若智慧的悟性可以引领我们去找到救赎之路,难道所有的人都能够获得这样的智慧和悟...史铁生说: 这下好了,您不再恐谎了不再是个人质了,您自由了。
算了吧你,我怎么可能自由呢
别忘了人真正的名字是:欲望。
所以您得知道,消灭恐慌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消灭欲望。
可是我...史铁生 说: 每一个有激情的演员都难免是一个人质。
每一个懂得欣赏的观众都巧妙地粉碎了一场阴谋。
每一个乏味的演员都是因为他老以为这戏剧与自己无关。
每一个倒霉的观众都是因为他总是...史铁生 说: 宇宙以其不息的欲望将一个歌舞炼为永恒。
这欲望有怎样一个人间的姓名,大可忽略不计。
史铁生 说: 果上帝并不允许一个人把他的梦统统忘掉得干净,那么最好让梦停留在最美丽的位置,在那儿画一个句号,或是一行删节号。
所谓最美丽的位置,f医生以为,并不一定是指...史铁生 说: 无论是以“好汉”的光荣或惶惑,还是以“混蛋” 的勇敢或恐惧,都在振臂高呼,随波逐流。
^_^望采纳^_^
描写晚上的散文 史铁生
秋天的怀念 双腿瘫,我的脾气暴怒无常。
望着望着天上的雁阵,突然把面前的玻璃砸碎;听着听着李谷一甜美的歌声,我会猛地把手边的东西摔向四周的墙壁。
母亲就悄悄地躲出去,在我看不见的地方偷偷地听着我的动静。
当一切恢复沉寂,她又悄悄地进来,眼边红红的,看着我。
“听说北海的花儿都开了,我推着你去走走。
”她总是这么说。
母亲喜欢花,可自从我的腿瘫痪后,她侍弄的那些花都死了。
“不,我不去
”我狠命地捶打这两条可恨的腿,喊着:“我活着有什么劲
”母亲扑过来抓住我的手,忍住哭声说:“咱娘儿俩在一块儿,好好儿活,好好儿活……”可我却一直都不知道,她的病已经到了那步田地。
后来妹妹告诉我,她常常肝疼得整宿整宿翻来覆去地睡不了觉。
那天我又独自坐在屋里,看着窗外的树叶“唰唰啦啦”地飘落。
母亲进来了,挡在窗前:“北海的菊花开了,我推着你去看看吧。
”她憔悴的脸上现出央求般的神色。
“什么时候
”“你要是愿意,就明天?”她说。
我的回答已经让她喜出望外了。
“好吧,就明天。
”我说。
她高兴得一会坐下,一会站起:“那就赶紧准备准备。
”“唉呀,烦不烦
几步路,有什么好准备的
”她也笑了,坐在我身边,絮絮叨叨地说着:“看完菊花,咱们就去‘仿膳’,你小时候最爱吃那儿的豌豆黄儿。
还记得那回我带你去北海吗
你偏说那杨树花是毛毛虫,跑着,一脚踩扁一个……”她忽然不说了。
对于“跑”和“踩”一类的字眼儿。
她比我还敏感。
她又悄悄地出去了。
她出去了。
就再也没回来。
邻居们把她抬上车时,她还在大口大口地吐着鲜血。
我没想到她已经病成那样。
看着三轮车远去,也绝没有想到那竟是永远的诀别。
邻居的小伙子背着我去看她的时候,她正艰难地呼吸着,像她那一生艰难的生活。
别人告诉我,她昏迷前的最后一句话是:“我那个有病的儿子和我那个还未成年的女儿……” 又是秋天,妹妹推我去北海看了菊花。
黄色的花淡雅、白色的花高洁、紫红色的花热烈而深沉,泼泼洒洒,秋风中正开得烂漫。
我懂得母亲没有说完的话。
妹妹也懂。
我俩在一块儿,要好好儿活……合欢树 世界上有一种最美丽的声音,那便是母亲的呼唤。
--但丁 10岁那年,我在一次作文比赛中得了第一。
母亲那时候还年轻,急着跟我说她自己,说她小时候的作文作得还要好,老师甚至不相信那么好的文章会是她写的。
“老师找到家来问,是不是家里的大人帮了忙。
我那时可能还不到10岁呢。
”我听得扫兴,故意笑:“可能
什么叫‘可能还不到’
”她就解释。
我装做根本不在意她的话,对着墙打乒乓球,把她气得够呛。
不过我承认她聪明,承认她是世界上长得最好看的女的。
她正给自己做一条蓝底白花的裙子。
我20岁时,我的两条腿残废了。
除去给人家画彩蛋,我想我还应该再干点别的事,先后改变了几次主意,最后想学写作。
母亲那时已不年轻,为了我的腿,她头上开始有了白发。
医院已明确表示,我的病目前没法治。
母亲的全副心思却还放在给我治病上,到处找大夫,打听偏方,花了很多钱。
她倒总能找来些稀奇古怪的药,让我吃,让我喝,或是洗、敷、熏、灸。
“别浪费时间啦,根本没用
”我说。
我一心只想着写小说,仿佛那东西能把残疾人救出困境。
“再试一回,不试你怎么知道会没用
”她每说一回都虔诚地抱着希望。
然而对我的腿,有多少回希望就有多少回失望。
最后一回,我的胯上被熏成烫伤。
医院的大夫说,这实在太悬了,对于瘫痪病人,这差不多是要命的事。
我倒没太害怕,心想死了也好,死了倒痛快。
母亲惊惶了几个月,昼夜守着我,一换药就说:“怎么会烫了呢
我还总是在留神呀
”幸亏伤口好起来,不然她非疯了不可。
后来她发现我在写小说。
她跟我说:“那就好好写吧。
”我听出来,她对治好我的腿也终于绝望。
“我年轻的时候也喜欢文学,跟你现在差不多大的时候,我也想过搞写作。
你小时候的作文不是得过第一吗
那就写着试试看。
”她提醒我说。
我们俩都尽力把我的腿忘掉。
她到处去给我借书,顶着雨或冒着雪推我去看电影,像过去给我找大夫、打听偏方那样,抱了希望。
30岁时,我的第一篇小说发表了,母亲却已不在人世。
过了几年,我的另一篇小说也获了奖,母亲已离开我整整7年了。
获奖之后,登门采访的记者就多。
大家都好心好意,认为我不容易。
但是我只准备了一套话,说来说去就觉得心烦。
我摇着车躲了出去。
坐在小公园安静的树林里,想:上帝为什么早早地召母亲回去呢
迷迷糊糊的,我听见回答:“她心里太苦了。
上帝看她受不住了,就召她回去。
”我的心得到一点安慰,睁开眼睛,看见风正在树林里吹过。
我摇车离开那儿,在街上瞎逛,不想回家。
母亲去世后,我们搬了家。
我很少再到母亲住过的那个小院子去。
小院在一个大院的尽里头,我偶尔摇车到大院儿去坐坐,但不愿意去那个小院子,推说手摇车进去不方便。
院子里的老太太们还都把我当儿孙看,尤其想到我又没了母亲,但都不说,光扯些闲话,怪我不常去。
我坐在院子当中,喝东家的茶,吃西家的瓜。
有一年,人们终于又提到母亲:“到小院子去看看吧,你妈种的那棵合欢树今年开花了
”我心里一阵抖,还是推说手摇车进出太不易。
大伙就不再说,忙扯到别的,说起我们原来住的房子里现在住了小两口,女的刚生了个儿子,孩子不哭不闹,光是瞪着眼睛看窗户上的树影儿。
我没料到那棵树还活着。
那年,母亲到劳动局去给我找工作,回来时在路边挖了一棵刚出土的绿苗,以为是含羞草,种在花盆里,竟是一棵合欢树。
母亲从来喜欢那些东西,但当时心思全在别处,第二年合欢树没有发芽,母亲叹息了一回,还不舍得扔掉,依然让它留在瓦盆里。
第三年,合欢树不但长出了叶子,而且还比较茂盛。
母亲高兴了好多天,以为那是个好兆头,常去侍弄它,不敢太大意。
又过了一年,她把合欢树移出盆,栽在窗前的地上,有时念叨,不知道这种树几年才开花。
再过一年,我们搬了家,悲哀弄得我们都把那棵小树忘记了。
与其在街上瞎逛,我想,不如去看看那棵树吧。
我也想再看看母亲住过的那间房。
我老记着,那儿还有个刚来世上的孩子,不哭不闹,瞪着眼睛看树影儿。
是那棵合欢树的影子吗
院子里的老太太们还是那么喜欢我,东屋倒茶,西屋点烟,送到我跟前。
大伙都知道我获奖的事,也许知道,但不觉得那很重要;还是都问我的腿,问我是否有了正式工作。
这回,想摇车进小院儿真是不能了。
家家门前的小厨房都扩大了,过道窄得一个人推自行车进去也要侧身。
我问起那棵合欢树,大伙说,年年都开花,长得跟房子一样高了。
这么说,我再看不见它了。
我要是求人背我去看,倒也不是不行。
我挺后悔前两年没有自己摇车进去看看。
我摇车在街上慢慢走,不想急着回家。
人有时候只想独自静静地呆一会。
悲伤也成享受。
有那么一天,那个孩子长大了。
会想起童年的事,会想起那些晃动的树影儿,会想起他自己的妈妈。
他会跑去看看那棵树。
但他不会知道那棵树是谁种的,是怎么种的。
史铁生作品中描写母亲的段落
《我与地坛》 现才想到,当年我独自跑到地,曾经给母亲出了一样的难题。
她不是那种光会疼爱儿子而不懂得理解儿子的母亲。
她知道我心里的苦闷,知道不该阻止我出去走走,知道我要是老呆在家里结果会更糟,但她又担心我一个人在那荒僻的园子里整天都想些什么。
我那时脾气坏到极点,经常是发了疯一样地离开家,从那园子里回来又中了魔似的什么话都不说。
母亲知道有些事不宜问,便犹犹豫豫地想问而终于不敢问,因为她自己心里也没有答案。
她料想我不会愿意她跟我一同去,所以她从未这样要求过,她知道得给我一点独处的时间,得有这样一段过程。
她只是不知道这过程得要多久,和这过程的尽头究竟是什么。
每次我要动身时,她便无言地帮我准备,帮助我上了轮椅车,看着我摇车拐出小院;这以后她会怎样,当年我不曾想过。
有一回我摇车出了小院;想起一件什么事又返身回来,看见母亲仍站在原地,还是送我走时的姿势,望着我拐出小院去的那处墙角,对我的回来竟一时没有反应。
待她再次送我出门的时候,她说:“出去活动活动,去地坛看看书,我说这挺好。
”许多年以后我才渐渐听出,母亲这话实际上是自我安慰,是暗自的祷告,是给我的提示,是恳求与嘱咐。
只是在她猝然去世之后,我才有余暇设想。
当我不在家里的那些漫长的时间,她是怎样心神不定坐卧难宁,兼着痛苦与惊恐与一个母亲最低限度的祈求。
现在我可以断定,以她的聪慧和坚忍,在那些空落的白天后的黑夜,在那不眠的黑夜后的白天,她思来想去最后准是对自己说:“反正我不能不让他出去,未来的日子是他自己的,如果他真的要在那园子里出了什么事,这苦难也只好我来承担。
”在那段日子里——那是好几年长的一段日子,我想我一定使母亲作过了最坏的准备了,但她从来没有对我说过:“你为我想想”。
事实上我也真的没为她想过。
那时她的儿子,还太年轻,还来不及为母亲想,他被命运击昏了头,一心以为自己是世上最不幸的一个,不知道儿子的不幸在母亲那儿总是要加倍的。
她有一个长到二十岁上忽然截瘫了的儿子,这是她唯一的儿子;她情愿截瘫的是自己而不是儿子,可这事无法代替;她想,只要儿子能活下去哪怕自己去死呢也行,可她又确信一个人不能仅仅是活着,儿子得有一条路走向自己的幸福;而这条路呢,没有谁能保证她的儿子终于能找到。
——这样一个母亲,注定是活得最苦的母亲。
有一次与一个作家朋友聊天,我问他学写作的最初动机是什么?他想了一会说:“为我母亲。
为了让她骄傲。
”我心里一惊,良久无言。
回想自己最初写小说的动机,虽不似这位朋友的那般单纯,但如他一样的愿望我也有,且一经细想,发现这愿望也在全部动机中占了很大比重。
这位朋友说:“我的动机太低俗了吧?”我光是摇头,心想低俗并不见得低俗,只怕是这愿望过于天真了。
他又说:“我那时真就是想出名,出了名让别人羡慕我母亲。
”我想,他比我坦率。
我想,他又比我幸福,因为他的母亲还活着。
而且我想,他的母亲也比我的母亲运气好,他的母亲没有一个双腿残废的儿子,否则事情就不这么简单。
在我的头一篇小说发表的时候,在我的小说第一次获奖的那些日子里,我真是多么希望我的母亲还活着。
我便又不能在家里呆了,又整天整天独自跑到地坛去,心里是没头没尾的沉郁和哀怨,走遍整个园子却怎么也想不通:母亲为什么就不能再多活两年?为什么在她儿子就快要碰撞开一条路的时候,她却忽然熬不住了?莫非她来此世上只是为了替儿子担忧,却不该分享我的一点点快乐?她匆匆离我去时才只有四十九岁呀!有那么一会,我甚至对世界对上帝充满了仇恨和厌恶。
后来我在一篇题为“合欢树”的文章中写道:“我坐在小公园安静的树林里,闭上眼睛,想,上帝为什么早早地召母亲回去呢?很久很久,迷迷糊溯的我听见了回答:‘她心里太苦了,上帝看她受不住了,就召她回去。
’我似乎得了一点安慰,睁开眼睛,看见风正从树林里穿过。
”小公园,指的也是地坛。
只是到了这时候,纷纭的往事才在我眼前幻现得清晰,母亲的苦难与伟大才在我心中渗透得深彻。
上帝的考虑,也许是对的。
摇着轮椅在园中慢慢走,又是雾罩的清晨,又是骄阳高悬的白昼,我只想着一件事:母亲已经不在了。
在老柏树旁停下,在草地上在颓墙边停下,又是处处虫鸣的午后,又是鸟儿归巢的傍晚,我心里只默念着一句话:可是母亲已经不在了。
把椅背放倒,躺下,似睡非睡挨到日没,坐起来,心神恍惚,呆呆地直坐到古祭坛上落满黑暗然后再渐渐浮起月光,心里才有点明白,母亲不能再来这园中找我了。
曾有过好多回,我在这园子里呆得太久了,母亲就来找我。
她来找我又不想让我发觉,只要见我还好好地在这园子里,她就悄悄转身回去,我看见过几次她的背影。
我也看见过几回她四处张望的情景,她视力不好,端着眼镜像在寻找海上的一条船,她没看见我时我已经看见她了,待我看见她也看见我了我就不去看她,过一会我再抬头看她就又看见她缓缓离去的背影。
我单是无法知道有多少回她没有找到我。
有一回我坐在矮树丛中,树丛很密,我看见她没有找到我;她一个人在园子里走,走过我的身旁,走过我经常呆的一些地方,步履茫然又急迫。
我不知道她已经找了多久还要找多久,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决意不喊她——但这绝不是小时候的捉迷藏,这也许是出于长大了的男孩子的倔强或羞涩?但这倔只留给我痛侮,丝毫也没有骄傲。
我真想告诫所有长大了的男孩子,千万不要跟母亲来这套倔强,羞涩就更不必,我已经懂了可我已经来不及了。
儿子想使母亲骄傲,这心情毕竟是太真实了,以致使“想出名”这一声名狼藉的念头也多少改变了一点形象。
这是个复杂的问题,且不去管它了罢。
随着小说获奖的激动逐日暗淡,我开始相信,至少有一点我是想错了:我用纸笔在报刊上碰撞开的一条路,并不就是母亲盼望我找到的那条路。
年年月月我都到这园子里来,年年月月我都要想,母亲盼望我找到的那条路到底是什么。
母亲生前没给我留下过什么隽永的哲言,或要我恪守的教诲,只是在她去世之后,她艰难的命运,坚忍的意志和毫不张扬的爱,随光阴流转,在我的印象中愈加鲜明深刻。
有一年,十月的风又翻动起安详的落叶,我在园中读书,听见两个散步的老人说:“没想到这园子有这么大。
”我放下书,想,这么大一座园子,要在其中找到她的儿子,母亲走过了多少焦灼的路。
多年来我头一次意识到,这园中不单是处处都有过我的车辙,有过我的车辙的地方也都有过母亲的脚印。
《合欢树》 10岁那年,我在一次作文比赛中得了第一。
母亲那时候还年轻,急着跟我说她自己,说她小时候的作文作得还要好,老师甚至不相信那么好的文章会是她写的。
“老师找到家来问,是不是家里的大人帮了忙。
我那时可能还不到10岁呢。
”我听得扫兴,故意笑:“可能
什么叫‘可能还不到’
”她就解释。
我装做根本不在意她的话,对着墙打乒乓球,把她气得够呛。
不过我承认她聪明,承认她是世界上长得最好看的女的。
她正给自己做一条蓝底白花的裙子。
我20岁时,我的两条腿残废了。
除去给人家画彩蛋,我想我还应该再干点别的事,先后改变了几次主意,最后想学写作。
母亲那时已不年轻,为了我的腿,她头上开始有了白发。
医院已明确表示,我的病目前没法治。
母亲的全副心思却还放在给我治病上,到处找大夫,打听偏方,花了很多钱。
她倒总能找来些稀奇古怪的药,让我吃,让我喝,或是洗、敷、熏、灸。
“别浪费时间啦,根本没用
”我说。
我一心只想着写小说,仿佛那东西能把残疾人救出困境。
“再试一回,不试你怎么知道会没用
”她每说一回都虔诚地抱着希望。
然而对我的腿,有多少回希望就有多少回失望。
最后一回,我的胯上被熏成烫伤。
医院的大夫说,这实在太悬了,对于瘫痪病人,这差不多是要命的事。
我倒没太害怕,心想死了也好,死了倒痛快。
母亲惊惶了几个月,昼夜守着我,一换药就说:“怎么会烫了呢
我还总是在留神呀
”幸亏伤口好起来,不然她非疯了不可。
后来她发现我在写小说。
她跟我说:“那就好好写吧。
”我听出来,她对治好我的腿也终于绝望。
“我年轻的时候也喜欢文学,跟你现在差不多大的时候,我也想过搞写作。
你小时候的作文不是得过第一吗
那就写着试试看。
”她提醒我说。
我们俩都尽力把我的腿忘掉。
她到处去给我借书,顶着雨或冒着雪推我去看电影,像过去给我找大夫、打听偏方那样,抱了希望。
30岁时,我的第一篇小说发表了,母亲却已不在人世。
过了几年,我的另一篇小说也获了奖,母亲已离开我整整7年了。
获奖之后,登门采访的记者就多。
大家都好心好意,认为我不容易。
但是我只准备了一套话,说来说去就觉得心烦。
我摇着车躲了出去。
坐在小公园安静的树林里,想:上帝为什么早早地召母亲回去呢
迷迷糊糊的,我听见回答:“她心里太苦了。
上帝看她受不住了,就召她回去。
”我的心得到一点安慰,睁开眼睛,看见风正在树林里吹过。
我摇车离开那儿,在街上瞎逛,不想回家。
母亲去世后,我们搬了家。
我很少再到母亲住过的那个小院子去。
小院在一个大院的尽里头,我偶尔摇车到大院儿去坐坐,但不愿意去那个小院子,推说手摇车进去不方便。
院子里的老太太们还都把我当儿孙看,尤其想到我又没了母亲,但都不说,光扯些闲话,怪我不常去。
我坐在院子当中,喝东家的茶,吃西家的瓜。
有一年,人们终于又提到母亲:“到小院子去看看吧,你妈种的那棵合欢树今年开花了
”我心里一阵抖,还是推说手摇车进出太不易。
大伙就不再说,忙扯到别的,说起我们原来住的房子里现在住了小两口,女的刚生了个儿子,孩子不哭不闹,光是瞪着眼睛看窗户上的树影儿。
我没料到那棵树还活着。
那年,母亲到劳动局去给我找工作,回来时在路边挖了一棵刚出土的绿苗,以为是含羞草,种在花盆里,竟是一棵合欢树。
母亲从来喜欢那些东西,但当时心思全在别处,第二年合欢树没有发芽,母亲叹息了一回,还不舍得扔掉,依然让它留在瓦盆里。
第三年,合欢树不但长出了叶子,而且还比较茂盛。
母亲高兴了好多天,以为那是个好兆头,常去侍弄它,不敢太大意。
又过了一年,她把合欢树移出盆,栽在窗前的地上,有时念叨,不知道这种树几年才开花。
再过一年,我们搬了家,悲哀弄得我们都把那棵小树忘记了。
与其在街上瞎逛,我想,不如去看看那棵树吧。
我也想再看看母亲住过的那间房。
我老记着,那儿还有个刚来世上的孩子,不哭不闹,瞪着眼睛看树影儿。
是那棵合欢树的影子吗
院子里的老太太们还是那么喜欢我,东屋倒茶,西屋点烟,送到我跟前。
大伙都知道我获奖的事,也许知道,但不觉得那很重要;还是都问我的腿,问我是否有了正式工作。
这回,想摇车进小院儿真是不能了。
家家门前的小厨房都扩大了,过道窄得一个人推自行车进去也要侧身。
我问起那棵合欢树,大伙说,年年都开花,长得跟房子一样高了。
这么说,我再看不见它了。
我要是求人背我去看,倒也不是不行。
我挺后悔前两年没有自己摇车进去看看。
我摇车在街上慢慢走,不想急着回家。
人有时候只想独自静静地呆一会。
悲伤也成享受。
有那么一天,那个孩子长大了。
会想起童年的事,会想起那些晃动的树影儿,会想起他自己的妈妈。
他会跑去看看那棵树。
但他不会知道那棵树是谁种的,是怎么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