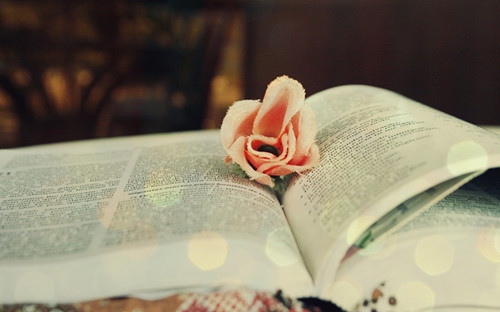读杨绛与钱钟书的爱情才知何为最美的爱情
相识:人生若只如初见杨绛出生在无锡一个书香门第,清逸温婉,知书达理。
1928年,杨绛高中毕业,她心心念念想报考清华大学外文系,孰料那年清华大学开始招收女生,但是南方没有名额。
无奈之下,杨绛选择了东吴大学。
1932年初,杨绛本该读大四下,东吴大学却因学潮而停课。
为了顺利完成学业,杨绛毅然北上京华,借读清华大学。
当时,为了去清华,杨绛放弃了美国韦尔斯利女子大学的奖学金,至此,她终于圆了清华梦。
仿佛冥冥中,清华园的钱钟书正在召唤着姗姗来迟的她。
3月的一天,风和日丽,幽香袭人。
杨绛在清华大学古月堂的门口,幸运地结识了大名鼎鼎的清华才子钱钟书。
当时钱钟书穿着青布大褂,脚穿一双毛布底鞋,戴一副老式眼镜,目光炯炯有神,谈吐机智幽默,满身浸润着儒雅气质。
两人一见如故,侃侃而谈。
钱钟书急切地澄清:“外界传说我已经订婚,这不是事实,请你不要相信。
”杨绛也趁机说明:“坊间传闻追求我的男孩子有孔门弟子‘七十二人’之多,也有人说费孝通是我的男朋友,这也不是事实。
”恰巧两人在文学上有共同的爱好和追求,这一切使他们怦然心动,一见钟情。
两人恋爱时,除了约会,就是通信。
钱钟书文采斐然,写的信当然是撩人心弦的情书,杨绛的那颗芳心被迅速融化。
有一次,杨绛的回信落在了钱钟书父亲钱基博老先生的手里。
钱父好奇心突发,悄悄拆开信件,看完喜不自禁。
原来,杨绛在信中说:“现在吾两人快乐无用,须两家父母兄弟皆大欢喜,吾两人之快乐乃彻始彻终不受障碍”,钱父大赞:“此诚聪明人语
”在钱父看来,杨绛思维缜密,办事周到,这对于不谙世事的儿子,是可遇不可求的贤内助。
1935年,两人完婚,牵手走入围城。
其实,这段缘分早就命中注定了。
早在1919年,8岁的杨绛曾随父母去过钱钟书家做客,只是当时年纪小,印象寥寥。
但这段经历恰恰开启了两人之间的“前缘”。
而且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与杨绛的父亲杨荫杭都是无锡本地的名士,两人的结合可谓是“门当户对,珠联璧合”,两家人是真正地“皆大欢喜”。
相爱:赌书消得泼茶香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杨绛与钱钟书是天造地设的绝配。
胡河清曾赞叹:“钱锺书、杨绛伉俪,可说是当代文学中的一双名剑。
钱锺书如英气流动之雄剑,常常出匣自鸣,语惊天下;杨绛则如青光含藏之雌剑,大智若愚,不显刀刃。
”在这样一个单纯温馨的学者家庭,两人过着“琴瑟和弦,鸾凤和鸣”的围城生活。
1935年,杨绛陪夫君去英国牛津就读。
初到牛津,杨绛很不习惯异国的生活,又乡愁迭起。
一天早上,杨绛还在睡梦中,钱钟书早已在厨房忙活开了,平日里“拙手笨脚”的他煮了鸡蛋,烤了面包,热了牛奶,还做了醇香的红茶。
睡眼惺忪的杨绛被钱钟书叫醒,他把一张用餐小桌支在床上,把美味的早餐放在小桌上,这样杨绛就可以坐在床上随意享用了。
吃着夫君亲自做的饭,杨绛幸福地说:“这是我吃过的最香的早饭”,听到爱妻满意的回答,钱钟书欣慰地笑了。
学习之余,杨绛和钱钟书还展开读书竞赛,比谁读的书多。
通常情况下,两人所读的册数不相上下。
有一次,钱钟书和杨绛交流阅读心得:“一本书,第二遍再读,总会发现读第一遍时会有许多疏忽。
最精彩的句子,要读几遍之后才会发现。
”杨绛不以为然,说:“这是你的读法。
我倒是更随性,好书多看几遍,不感兴趣的书则浏览一番即可。
”读读写写,嘻嘻闹闹,两人的婚姻生活倒充满了悠悠情趣,羡煞旁人。
1942年底,杨绛创作了话剧《称心如意》。
在金都大戏院上演后,一鸣惊人,迅速走红。
杨绛的蹿红,使大才子钱钟书坐不住了。
一天,他对杨绛说:“我想写一部长篇小说,你支持吗
”杨绛大为高兴,催他赶紧写。
杨绛让他减少授课时间,为了节省开支,她还把家里的女佣辞退了,自己包揽了所有的家务活,劈材生火做饭样样都来,经常被烟火熏得满眼是泪,也会不小心切破手指。
可是杨绛并未抱怨过,她心甘情愿地做灶下婢,只盼着钟书的大作早日问世。
看着昔日娇生惯养的富家小姐,如今修炼成任劳任怨的贤内助,钱钟书心里虽有惭愧,但更多的是对爱妻的感激与珍爱。
两年后,《围城》成功问世。
钱钟书在《围城》序中说:“这本书整整写了两年。
两年里忧世伤生,屡想中止。
由于杨绛女士不断的督促,替我挡了许多事,省出时间来,得以锱铢积累地写完。
照例这本书该献给她。
”其实,《围城》是在沦陷上海的时期写的,艰难岁月里,夫妻两人相濡以沫,相敬如宾,这是多么难得的人间真情啊
相守:此情可待成追忆爱女阿圆出生时,钱钟书致“欢迎辞”:“这是我的女儿,我喜欢的。
”杨绛说女儿是自己“平生唯一的杰作”。
回国后,这个三口之家一直居无定所。
1962年8月,一家人迁居干面胡同新建的宿舍,有四个房间,还有一个阳台,他们又添置了家具,终于有了个舒适的家。
那时,钱钟书经常带着妻女去饭馆吃饭,有一次,在等待上菜的空挡,钱钟书和阿圆一直在观察其他饭桌上吃客的言谈举止,并且像看戏一样很是着迷。
杨绛奇怪地问:“你们这是干嘛啊
”阿圆说:“观察生活是件很有趣的事,你看那一桌两个人是夫妻,在吵架,那一桌是在宴请亲戚……”杨绛明白了,这父女俩是在看戏呢。
待到吃完饭的时候,有的戏已经下场,有的戏正在上演。
这三人在一起,总有无穷的趣味,平淡的生活充满了温情。
这个三口之家,很朴素,很单纯,温馨如饴,只求相守在一起,各自做力所能及的事……时光静静流逝着,再美好的故事总有谢幕的一天,杨绛在《我们仨》里写道:“1997年早春,阿媛去世。
1998年岁末,钟书去世。
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
现在,只剩下我一个。
”阿圆去世时,钱钟书已重病卧床,他黯然地看着杨绛,眼睛是干枯的,心里却在流泪。
杨绛急忙告诉他:“阿圆是在沉睡中去的。
”钱钟书点头,痛苦地闭上眼睛。
怀着丧女之痛,杨绛还要每天去医院探望钱钟书,百般劝慰他,并亲自做饭带给他吃。
那时,杨绛已经八十多岁高龄,老病相催,生活日趋艰难。
尽管如此,她依旧坚强地支撑起这个失去爱女的破碎之家。
女儿走了,丈夫走了,昔日其乐融融的家庭不复存在,只剩下杨绛孤零零一个人。
从此,杨绛深居简出,很少接待来客,开始悉心整理钱钟书的手稿。
有一日,社会学家费孝通来拜访杨绛。
他对当年的心上人还是情有独钟,便带着自己的著作来请杨绛“斧正”。
旧友重逢,喜上眉梢,两人嘘寒问暖,交谈甚欢,忽然杨绛意识到自己有些失态了,便态度冷淡起来。
待送别费老时,他颤巍巍走下楼梯,还依依不舍地频频回头,杨绛淡淡地说:“楼梯不好走,你以后再不要知难而上了。
”费老瞬间领悟了她的意思,从此彻底死了心。
2011年7月17日,是杨绛先生的百岁大寿,但是她很低调,没有举行任何隆重的庆祝仪式。
她只嘱咐亲戚们在家为她吃上一碗寿面即可。
钱钟书曾用一句话,概括他与杨绛的爱情:“绝无仅有的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
”这对文坛伉俪的爱情,不仅有碧桃花下、新月如钩的浪漫,更融合了两人心有灵犀的默契与坚守。
纵然斯人已逝,而杨绛先生的深情依旧在岁月的轮回中静水流深,生生不息。
钱钟书和杨绛对爱情看透了 还有多少真实
钱钟书和林徽因邻居,他的猫经常和林的猫打架,他就准备了一根长竹竿,不管天气多冷,只要听到他的猫在打架,他就拿起竹竿去帮他的猫打架。
。
。
1966年,杨绛、钱钟书先后被打成“牛鬼蛇神”双双接受“改造”。
就是在那些苦难的日子里也保持着一份少有的幽默。
比如被迫剃了“阴阳头”,她会说:“小时候老羡慕弟弟剃光头……果不其然,羡慕的事早晚会实现。
”相守:此情可待成追忆爱女阿圆出生时,钱钟书致“欢迎辞”:“这是我的女儿,我喜欢的。
”杨绛说女儿是自己“平生唯一的杰作”。
回国后,这个三口之家一直居无定所。
1962年8月,一家人迁居干面胡同新建的宿舍,有四个房间,还有一个阳台,他们又添置了家具,终于有了个舒适的家。
那时,钱钟书经常带着妻女去饭馆吃饭,有一次,在等待上菜的空挡,钱钟书和阿圆一直在观察其他饭桌上吃客的言谈举止,并且像看戏一样很是着迷。
杨绛奇怪地问:“你们这是干嘛啊
”阿圆说:“观察生活是件很有趣的事,你看那一桌两个人是夫妻,在吵架,那一桌是在宴请亲戚……”杨绛明白了,这父女俩是在看戏呢。
待到吃完饭的时候,有的戏已经下场,有的戏正在上演。
这三人在一起,总有无穷的趣味,平淡的生活充满了温情。
这个三口之家,很朴素,很单纯,温馨如饴,只求相守在一起,各自做力所能及的事……时光静静流逝着,再美好的故事总有谢幕的一天,杨绛在《我们仨》里写道:“1997年早春,阿媛去世。
1998年岁末,钟书去世。
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
现在,只剩下我一个。
”阿圆去世时,钱钟书已重病卧床,他黯然地看着杨绛,眼睛是干枯的,心里却在流泪。
杨绛急忙告诉他:“阿圆是在沉睡中去的。
”钱钟书点头,痛苦地闭上眼睛。
怀着丧女之痛,杨绛还要每天去医院探望钱钟书,百般劝慰他,并亲自做饭带给他吃。
那时,杨绛已经八十多岁高龄,老病相催,生活日趋艰难。
尽管如此,她依旧坚强地支撑起这个失去爱女的破碎之家。
女儿走了,丈夫走了,昔日其乐融融的家庭不复存在,只剩下杨绛孤零零一个人。
从此,杨绛深居简出,很少接待来客,开始悉心整理钱钟书的手稿。
有一日,社会学家费孝通来拜访杨绛。
他对当年的心上人还是情有独钟,便带着自己的著作来请杨绛“斧正”。
旧友重逢,喜上眉梢,两人嘘寒问暖,交谈甚欢,忽然杨绛意识到自己有些失态了,便态度冷淡起来。
待送别费老时,他颤巍巍走下楼梯,还依依不舍地频频回头,杨绛淡淡地说:“楼梯不好走,你以后再不要知难而上了。
”费老瞬间领悟了她的意思,从此彻底死了心。
2010年7月17日,是杨绛先生的百岁大寿,但是她很低调,没有举行任何隆重的庆祝仪式。
她只嘱咐亲戚们在家为她吃上一碗寿面即可。
钱钟书曾用一句话,概括他与杨绛的爱情:“绝无仅有的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
”这对文坛伉俪的爱情,不仅有碧桃花下、新月如钩的浪漫,更融合了两人心有灵犀的默契与坚守。
纵然斯人已逝,而杨绛先生的深情依旧在岁月的轮回中静水流深,生生不息。
杨绛给钱钟书写信只有一个字:怂,钱钟书的回信有多浪漫
相识:人生若只如初见杨绛出生在无锡一个书香门第,清逸温婉,知书达理。
1928年,杨绛高中毕业,她心心念念想报考清华大学外文系,孰料那年清华大学开始招收女生,但是南方没有名额。
无奈之下,杨绛选择了东吴大学。
1932年初,杨绛本该读大四下,东吴大学却因学潮而停课。
为了顺利完成学业,杨绛毅然北上京华,借读清华大学。
当时,为了去清华,杨绛放弃了美国韦尔斯利女子大学的奖学金,至此,她终于圆了清华梦。
仿佛冥冥中,清华园的钱钟书正在召唤着姗姗来迟的她。
3月的一天,风和日丽,幽香袭人。
杨绛在清华大学古月堂的门口,幸运地结识了大名鼎鼎的清华才子钱钟书。
当时钱钟书穿着青布大褂,脚穿一双毛布底鞋,戴一副老式眼镜,目光炯炯有神,谈吐机智幽默,满身浸润着儒雅气质。
两人一见如故,侃侃而谈。
钱钟书急切地澄清:“外界传说我已经订婚,这不是事实,请你不要相信。
”杨绛也趁机说明:“坊间传闻追求我的男孩子有孔门弟子‘七十二人’之多,也有人说费孝通是我的男朋友,这也不是事实。
”恰巧两人在文学上有共同的爱好和追求,这一切使他们怦然心动,一见钟情。
两人恋爱时,除了约会,就是通信。
钱钟书文采斐然,写的信当然是撩人心弦的情书,杨绛的那颗芳心被迅速融化。
有一次,杨绛的回信落在了钱钟书父亲钱基博老先生的手里。
钱父好奇心突发,悄悄拆开信件,看完喜不自禁。
原来,杨绛在信中说:“现在吾两人快乐无用,须两家父母兄弟皆大欢喜,吾两人之快乐乃彻始彻终不受障碍”,钱父大赞:“此诚聪明人语
”在钱父看来,杨绛思维缜密,办事周到,这对于不谙世事的儿子,是可遇不可求的贤内助。
1935年,两人完婚,牵手走入围城。
其实,这段缘分早就命中注定了。
早在1919年,8岁的杨绛曾随父母去过钱钟书家做客,只是当时年纪小,印象寥寥。
但这段经历恰恰开启了两人之间的“前缘”。
而且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与杨绛的父亲杨荫杭都是无锡本地的名士,两人的结合可谓是“门当户对,珠联璧合”,两家人是真正地“皆大欢喜”。
相爱:赌书消得泼茶香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杨绛与钱钟书是天造地设的绝配。
胡河清曾赞叹:“钱锺书、杨绛伉俪,可说是当代文学中的一双名剑。
钱锺书如英气流动之雄剑,常常出匣自鸣,语惊天下;杨绛则如青光含藏之雌剑,大智若愚,不显刀刃。
”在这样一个单纯温馨的学者家庭,两人过着“琴瑟和弦,鸾凤和鸣”的围城生活。
1935年,杨绛陪夫君去英国牛津就读。
初到牛津,杨绛很不习惯异国的生活,又乡愁迭起。
一天早上,杨绛还在睡梦中,钱钟书早已在厨房忙活开了,平日里“拙手笨脚”的他煮了鸡蛋,烤了面包,热了牛奶,还做了醇香的红茶。
睡眼惺忪的杨绛被钱钟书叫醒,他把一张用餐小桌支在床上,把美味的早餐放在小桌上,这样杨绛就可以坐在床上随意享用了。
吃着夫君亲自做的饭,杨绛幸福地说:“这是我吃过的最香的早饭”,听到爱妻满意的回答,钱钟书欣慰地笑了。
学习之余,杨绛和钱钟书还展开读书竞赛,比谁读的书多。
通常情况下,两人所读的册数不相上下。
有一次,钱钟书和杨绛交流阅读心得:“一本书,第二遍再读,总会发现读第一遍时会有许多疏忽。
最精彩的句子,要读几遍之后才会发现。
”杨绛不以为然,说:“这是你的读法。
我倒是更随性,好书多看几遍,不感兴趣的书则浏览一番即可。
”读读写写,嘻嘻闹闹,两人的婚姻生活倒充满了悠悠情趣,羡煞旁人。
1942年底,杨绛创作了话剧《称心如意》。
在金都大戏院上演后,一鸣惊人,迅速走红。
杨绛的蹿红,使大才子钱钟书坐不住了。
一天,他对杨绛说:“我想写一部长篇小说,你支持吗
”杨绛大为高兴,催他赶紧写。
杨绛让他减少授课时间,为了节省开支,她还把家里的女佣辞退了,自己包揽了所有的家务活,劈材生火做饭样样都来,经常被烟火熏得满眼是泪,也会不小心切破手指。
可是杨绛并未抱怨过,她心甘情愿地做灶下婢,只盼着钟书的大作早日问世。
看着昔日娇生惯养的富家小姐,如今修炼成任劳任怨的贤内助,钱钟书心里虽有惭愧,但更多的是对爱妻的感激与珍爱。
两年后,《围城》成功问世。
钱钟书在《围城》序中说:“这本书整整写了两年。
两年里忧世伤生,屡想中止。
由于杨绛女士不断的督促,替我挡了许多事,省出时间来,得以锱铢积累地写完。
照例这本书该献给她。
”其实,《围城》是在沦陷上海的时期写的,艰难岁月里,夫妻两人相濡以沫,相敬如宾,这是多么难得的人间真情啊
相守:此情可待成追忆爱女阿圆出生时,钱钟书致“欢迎辞”:“这是我的女儿,我喜欢的。
”杨绛说女儿是自己“平生唯一的杰作”。
回国后,这个三口之家一直居无定所。
1962年8月,一家人迁居干面胡同新建的宿舍,有四个房间,还有一个阳台,他们又添置了家具,终于有了个舒适的家。
那时,钱钟书经常带着妻女去饭馆吃饭,有一次,在等待上菜的空挡,钱钟书和阿圆一直在观察其他饭桌上吃客的言谈举止,并且像看戏一样很是着迷。
杨绛奇怪地问:“你们这是干嘛啊
”阿圆说:“观察生活是件很有趣的事,你看那一桌两个人是夫妻,在吵架,那一桌是在宴请亲戚……”杨绛明白了,这父女俩是在看戏呢。
待到吃完饭的时候,有的戏已经下场,有的戏正在上演。
这三人在一起,总有无穷的趣味,平淡的生活充满了温情。
这个三口之家,很朴素,很单纯,温馨如饴,只求相守在一起,各自做力所能及的事……时光静静流逝着,再美好的故事总有谢幕的一天,杨绛在《我们仨》里写道:“1997年早春,阿媛去世。
1998年岁末,钟书去世。
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
现在,只剩下我一个。
”阿圆去世时,钱钟书已重病卧床,他黯然地看着杨绛,眼睛是干枯的,心里却在流泪。
杨绛急忙告诉他:“阿圆是在沉睡中去的。
”钱钟书点头,痛苦地闭上眼睛。
怀着丧女之痛,杨绛还要每天去医院探望钱钟书,百般劝慰他,并亲自做饭带给他吃。
那时,杨绛已经八十多岁高龄,老病相催,生活日趋艰难。
尽管如此,她依旧坚强地支撑起这个失去爱女的破碎之家。
女儿走了,丈夫走了,昔日其乐融融的家庭不复存在,只剩下杨绛孤零零一个人。
从此,杨绛深居简出,很少接待来客,开始悉心整理钱钟书的手稿。
有一日,社会学家费孝通来拜访杨绛。
他对当年的心上人还是情有独钟,便带着自己的著作来请杨绛“斧正”。
旧友重逢,喜上眉梢,两人嘘寒问暖,交谈甚欢,忽然杨绛意识到自己有些失态了,便态度冷淡起来。
待送别费老时,他颤巍巍走下楼梯,还依依不舍地频频回头,杨绛淡淡地说:“楼梯不好走,你以后再不要知难而上了。
”费老瞬间领悟了她的意思,从此彻底死了心。
2011年7月17日,是杨绛先生的百岁大寿,但是她很低调,没有举行任何隆重的庆祝仪式。
她只嘱咐亲戚们在家为她吃上一碗寿面即可。
钱钟书曾用一句话,概括他与杨绛的爱情:“绝无仅有的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
”这对文坛伉俪的爱情,不仅有碧桃花下、新月如钩的浪漫,更融合了两人心有灵犀的默契与坚守。
纵然斯人已逝,而杨绛先生的深情依旧在岁月的轮回中静水流深,生生不息。
钱钟书与杨绛感情那么好,为什么还写围城,很矛盾
其实钱钟书和鲁迅一样,因为某些非正常的因素被捧到了一个非正常的位置,虽然都是大家,但并没有到称圣的程度,作家的书多少都有真实个人经历、思想混杂在里面,大众所了解的钱钟书夫妇都是杨绛描写的,是她愿意让我们了解的,真实其实我们无从得知,但从围城看,钱并不相信爱情,对女人的描写入木三分,婚姻都是一种现实的选择,这样的人不可能有无私的爱,但是维持一段外人看上去美好的感情是不难的,至少他的智商超人,从一些同时代的人评价来看,他是一个非常喜欢说段子的人,口才非常棒,通古博今,古文底子极好,喜欢打趣别人,但绝对不会是个书呆子,从他的文革经历就可以看出来,打架也绝不手软,杨绛得到的评价非常高,从她的文章里我只能看出是一个非常上海化的女人,好像不食人间烟火般的世外高人,字里行间充满了刻意,具体为人如何就不得而知了,个人并无多大的好感。
以遇见为话题写一篇有关钱钟书和杨降的故事
1932年,22岁的杨绛华园偶然碰见了钱钟书。
,杨绛说,“他穿一件青褂,一双毛底布鞋,戴一副老式大眼镜,一点也不翩翩。
”(杨绛 《记钱钟书与<围城>》) 杨绛本来是东吴大学的学生,因东吴大停课,学生借读北平高校,杨绛才来得到清华。
这般的阴差阳错,只能说他俩有姻缘在。
更有意思的是,这种偶遇实在是偶的巧极,杨绛的父亲杨荫杭和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都是无锡的名士,张謇曾把两人称为“江南才子”,江南才子们风流会友自然是往来不绝的,杨绛和钱钟书偶然一遇,再偶然一谈,方才知道,世交不说,原来早在十多年前,8岁的杨绛就曾经跟随父亲拜访过钱家,那时的钱钟书在庭院里跑闹打跳的时候未必注意过这么一个来造访本家的女孩子。
可当下一想,却觉得真是冥冥中自有定数。
后来杨荫杭曾打趣杨绛说,“阿季的脚下拴着月下老人的红丝呢,所以心心念念只想考清华。
”这巧缘,再加上两人文采的惺惺相吸,钱钟书和杨绛的恋爱,自然也不胫而走,流传于整个清华园了。
当时清华女少男多,而女生多住在“古月堂”,因此男生们有事没事都往那里跑去,情侣们也“每于夕阳西下,俪影双双徘徊于西园道上。
”为钱作传的汤晏笔调诙谐的说钱杨二人恐怕也是其中一对。
夏志清说钱锺书“才气高,幽默,很会讽刺人。
他什么人都看不起,当时联大的教授恨他的也不少。
他虽然一方面仍是谦虚,但是恃才傲物。
”这样的钱钟书,他的恋爱如果乏善可陈,与众雷同,那不免于泯灭可惜。
但这种担心是没有必要的,看看《围城》就知道了,什么事放到他手上,就消腾不了。
钱在清华的朋友许振德曾经说说,“钟书兄每将其恋爱经过逐一相告,并朗诵其情书佳作。
”(许振德《水木清华四十年》)这种得意于自己情书文采,倒是不稀奇,可隐私的情书也能当众宣读倒是钱钟书过人之处。
假使有人以此打趣杨绛,不晓得杨绛会不会诧异。
这一时期的钱钟书“好义山、仲则风华绮丽之体,为才子诗,全恃才华为之”,因此“写了很多有李义山风味的爱情诗。
”(汤晏《一代才子钱钟书》)他有一组《壬申年秋杪杂诗并序》就存留了写给杨绛的情诗,大抵可以窥见些风貌。
一首说,“缠绵悱恻好文章,粉恋香凄足断肠。
答报情痴无别物,心酸一把泪千行。
”钱才子诗意虽浅白,一番真情却是谁也不能怀疑得了。
又一首说,“困人节气奈何天,泥煞衾函梦不圆。
苦两泼寒宵似水,百虫声里怯孤眠。
”这是情诗的老调,因天而感人。
当然,钱钟书最让人诧异的就是写情诗用宋明理学入词,真是绝想妙想,当然也古怪的可以。
他自己对这一创举也很是自负,说“用理学家语作情诗,自来无第二人。
”(吴忠匡《记钱钟书先生》)这样的句子,我在别人写的传记里面找到几条,比如“除蛇深草钩难看,御寇颓垣守不坚。
”据说,这是以蛇比做相思,取捉摸不定,难以自持的意思。
做法倒是新奇,可总觉得不像情诗。
当年的杨绛看到这样子的情诗,赞叹之余恐怕要有点苦笑。
汤晏说《围城》实际上很间接的说了钱杨的恋爱。
除了书的写作年代基本契合以外,还透露了一个小故事。
有人曾当面问过钱钟书,说《围城》里的人都被他讽刺过,唯独“唐小姐例外”,最后也只是“fadeout”,这是什么原因。
钱钟书听完狡黠的反问,“难道你的意思说,唐晓芙是我的dream-girl
”钱钟书和杨绛的书信不是很勤快,如《围城》里描写的方鸿渐和唐晓芙一样,不过是“见了七八次,写给她了十几封信,唐小姐也回了五六封。
”放到现实中,假使杨绛回了五六封信,那么有一封肯定落到了钱老爷子钱基博手上,老先生三下五除二坦坦然的拆封一阅,见杨绛信中说,她和钱的事,自己同意没用,需要双方父母兄弟欢喜才好。
老先生看这女孩子通情达理,心里一高兴竟绕过钱钟书直接给杨绛去信一封,把杨绛夸奖了一番。
这种事情,说起来都让人忍俊不禁,这一家子可真是出奇人。
至于杨绛的父亲更是有意思的紧,和女婿钱钟书爱好到了一块,本来有个读书的女婿是差强人意,等知晓了这个女婿和自己一样喜欢读字典,一下子就大为赏识。
有一次偷偷问杨绛,“钟书常那么高兴吗
”一副欢喜关心的样子。
钱杨在双方家长满意后遂举行了婚礼。
杨绛后来回忆说,他们结婚前还有“订婚”一说,很是滑稽“明明是我们自己认识的,明明是我把默存介绍给我爸爸。
……可我们还颠颠倒倒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杨绛《车过古战场—追忆与钱穆先生同行赴京》)婚后,两人即赴英国。
在英国期间杨绛怀孕,钱钟书说,“我不要儿子,我要女儿──只要一个,像你的。
”(杨绛《我们仨》)风雨半个世纪后,1999年,八十八岁的钱钟书从此永远的离开了杨绛。
四年后,杨绛写出了一本散文集《我们仨》,来追忆他和钱钟书的故事,风传一时,人人争相阅读,在书的开头杨绛说她做了一个梦,她梦见“我和锺书一同散步,说说笑笑,走到了不知什么地方。
太阳已经下山,黄昏薄幕,苍苍茫茫中,忽然锺书不见了。
我四顾寻找,不见他的影踪。
我喊他,没人应。
”后来她把梦告诉钱钟书,埋怨钱钟书不等她让她惶急和孤凄,钱钟书说,“那是老人的梦,他也常做。
”(杨绛《我们仨》)这是老人的梦,被杨绛冒冒失的说了出来,而钱钟书则长久的埋在心底。
因为钱钟书知道有一天当他们在古驿道上走散时,这便成了一个真的“长达万里的梦”,他要比杨绛更加勇敢的面对。
当年在和杨绛热恋时,钱钟书曾经写下一首诗,良宵苦被睡相谩,猎猎西风测测寒。
如此星辰如此月,与谁指点与谁看。
我长时间的念着最后的两句,于是久久地不能停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