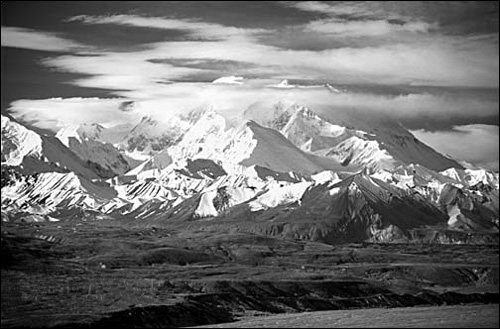老虎凶恶还是狮子凶恶
呵呵,竟然有人说不是,当然是了,但这句子,不成立。
1,因为狮子不是凶恶的明显代表,凶恶的话,可以是狼
。
,2,老虎和狮子是一个级别的动物。
3,再说老虎也能用凶恶来形容
老虎可以用威猛。
重庆方言骂人
重庆“言子儿重庆地方方言,俗语间谚语,歇后语等的总乡土味特别浓厚,语言幽默,也是重庆十八怪之一 。
重庆言子亦称渝语、重庆话,为西南官话独立语系,其内容包罗万象,天文地理,日常琐事无所不涉。
重庆言子的形式更是灵活多样,短小精悍,形象生动。
展言子习惯上叫歇后语、半截话,实际就是隐语。
前半句是譬语或引子,后半句是解语或注语,是说话人的真意所在。
这种语言形式类似“诗经”和陕北民歌信天游常用的“比兴手法”。
在实际语言运用中,常只说出前半句,而将后半句隐去不表,听话人常会心领神会,十分默契,使语言交流不但幽默风趣,而且含蓄生动,显现出特殊的美感和魅力。
例如:“瞎子戴眼境——多余的圈圈”,这是一个完整的言子儿。
但生活中常这么说:“你也不怕麻烦。
其实你做这些无用功完全是瞎子戴眼镜。
”再如:“半天空挂口袋——装风(疯)”。
生活中常说:“他这人神经得很,半天空挂口袋。
”常用言子编辑哈搓搓-----傻呼呼。
例句:你哈搓搓的,高压电能乱摸啊
驼子(皮驼)——拳头。
例句:前天他在街上惹了个疯子,疯子一驼子就把他打昏了。
安逸(巴适)——满意舒服。
例句:累了一天了,泡杯茶躺在上发上,安逸(巴适)得很。
要得——好的(表同意);不错(形容人品)。
例句:要的嘛,我就同意和张幺妹耍朋友嘛,其实亲戚朋友们都说她还要的。
假打——虚伪。
例句:你假打啥子嘛,外头绷浪子,屋头喝浆子。
踏血——鄙视、藐视。
例句:你还踏血人家,你个人的窑裤都还补了三个疤的嘛。
洗白了——输完了。
例句:记得下次打牌子弹要带够,不要几盘就遭洗白了。
过切——过去。
例句:李伯清,贾素芬让你马上过切一下。
不存在——不在乎。
例句:为了爱,不存在。
冒皮皮——显摆、吹牛。
例句:斧头都还没有拿稳,你就敢到鲁班门前去冒皮皮。
千翻儿——调皮。
例句:你娃不要太千翻很了,你把猫的胡子拔了抓子嘛
拈——捡、夹。
例句:那娃太懒了,元宝落了都懒得拈。
耙耳朵——妻管严。
例句:你莫要笑我是耙耳朵,你晚上回去了还不是一样的要跪搓衣板。
好多钱——多少钱。
例句:老板(儿),这个烟好多钱
扑爬——摔跤、绊跤。
例句:刚刚才从庙里面出来,出门就跶个扑爬。
撒子(啥子)——什么。
例句:声音叽叽咕咕的,哪个晓得他说的是啥子。
耍朋友——谈恋爱。
例句:老李,你不晓得,二娃和张幺妹在耍朋友的嘛。
摆龙门阵——闲聊天。
例句:吴文,有空就过我这来坐坐,兄弟几个泡个茶摆龙门阵。
沟子(箩篼)——屁股。
例句:老李昨晚上遭婆娘膼了一脚,他娃如今钩子都还在疼。
惊叫唤:像受惊一样喊叫;乱叫 。
例句:那么大的人还去逗小娃娃,把人家吓得惊叫唤。
筋筋绊绊(bàn):遇到小问题多不顺利、不和睦、不谐调的状况。
精试:耐用。
例句:老李,你娃买的袜子太精试了,穿了3年都没有烂。
经用:耐用。
例句:张二娃自己绑的扫把不经用,两天就扫垮了。
经蹦:精力充沛 。
例句:嘿,你还不要说,莫看起老李都六十几的人了,还那么经蹦。
经丝(咾):有裂纹(口)了。
例句:这个瓷碗不牢实,轻轻一碰就经丝了。
经得拖:身体素质好而能经受疾病、劳累等折磨。
例句:老李,你们爸都在床上躺了七八年了,经得拖哦。
经不得拖:“经得拖”的反义词。
例句:张大爷得的是癌症,身体再好也经不得脱啊。
紧倒:仍旧,还要,不停,不放手。
例句:说你娃求精不懂你还不信,不晓得就不要紧倒整嘛。
挤油渣(糟)儿:儿童的一种游戏,多人用手臂背部推挤,被推挤出划定的区域外的为输。
例句:你们几个莫出息的,又在那儿挤油渣。
假巴意思:假惺惺,假装,假情假意,故意。
例句:老李,人家都输哭起了,你就假巴意思让人家赢一盘嘛。
假比(是):假如,如果是。
例句:换个立场,假比你是他,你怎么办
假扳将:明知无理仍要强词夺理地争论的人。
例句:说你娃是犟拐拐麻古儿仰绊起飞你还不信,人家都说你是假扳将。
椒盐:含麻辣味道的,借代重庆味。
例句:老乡,我一听你就是家乡人,操一口椒盐普通话。
脚耙手软:手脚软弱无力。
例句:我和婆娘玩了一阵抱架子,如今还脚耙手软的。
浃浃:身上的污垢。
例句:你娃半年不洗澡,身上的浃浃到处飞的都是。
谨防:提防。
例句:平时不做作业,谨防期末不及格。
嚼:倔强,凶,不倔服,不服输。
例句:嘴巴不要嚼,事实就摆在眼前的,傻子都懂得起。
揪到:逮住。
例句:说你娃在外面灯晃你还不承认,这下遭我揪到了哇。
揪不动:扭不动,旋不动。
例句:电风扇该换一个了,开关都揪不动。
酱酱:浆状,比浆糊略稀。
例句:下雨天把裤子挽起来,免得在泥巴酱酱里面拖。
紧啷个说:唠叨相同的话或者相同的意思。
例句:你说的我早就晓得了,你还紧啷个说啥子嘛。
夹:剪。
例句:老李,你婆娘有点勤快哦,有事莫事就跑到我们地里去夹豌豆尖儿。
夹磨:磨难,被穿小鞋,艰难,打击。
例句:你是堂堂的局长的嘛,你夹磨人家一个看门的抓子
夹毛拘:给人穿小鞋。
例句:看门的老张遭局长夹毛拘了。
夹暴脚:给人穿小鞋,刁难(一般指针对新人)。
例句:不仅是这样,小张也遭局长夹毛拘了。
架不起势:开不了头。
例句:你们几个前几天不是风风火火的嘛,怎么还架不起势
金阿子:知了。
例句:他们几个昨天去逮金阿子,遭屙了一身的尿。
丁丁猫儿:蜻蜓。
例句:老李,你孙娃子逮了好多丁丁猫儿哦。
瞎块儿:青蛙。
例句:瞎块儿又叫癞疙包,切麻子。
癞疙包:蟾蜍。
例句:草里面跳出来个癞疙包,吓我一跳。
偷油婆:蟑螂。
偷油婆太可恶了,在屋里乱钻,烦死人。
金宝卵:珍贵之物(人),常含讥讽。
例句:他成天拿到那个金宝卵到处显摆。
叫鸡公(儿):爱叫屈喊冤的人,爱显露自己的人,争强好胜的人。
例句:老李是个叫鸡公。
犟拐拐:死不认错,固执己见,不听劝告之人。
例句:犟拐拐麻古儿仰绊起飞。
将就:得过且过,普通。
例句:老李,你看上那个女娃子其实也还将就,搂到算了。
噘(jué):骂 。
例句:哎哟,是那个短命娃儿弄得吗,也不怕人家噘你们妈。
掬(韵母是ú音,而非ǘ音):吮吸。
例句:断奶的娃儿就爱掬个人的手指母儿。
尖脑壳:戴绿帽子的男人;善于钻营的人。
例句:你莫跟人家比,你家的尖脑壳比你算的精。
方脑壳:脑袋不灵活,反应慢,笨,蠢。
例句:人家都笑你是方脑壳我还不信,一加一都不晓得是几,你脑壳硬是方的嗦
尖起耳朵:竖起耳朵。
例句:这些人啊,我布置任务的时候都耷起耳刮子,说发奖金就都尖起耳朵听了。
狙:针刺。
例句:老李,感冒了就早点去狙两针,免得人遭罪。
揪发条:诈骗,骗取他人的钱财后便抛弃他,多通过不正当的男女关系绢起(手、脚):曲(手、腿)。
例句:聪明一世糊涂一时,老李你娃也遭人家揪发条了啊
几个家伙:赶紧,赶快,几下子。
例句:老李吃饭快得很,几个家伙就刨完了。
几爷子:父子几个,一伙人。
例句:我们几爷子在学校篮球队里,算是相当扯的了。
兄弟伙:哥们,朋友。
例句:老李,我们兄弟该要喝哦,不喝就看不起了。
鸡摸眼:夜盲症。
例句:晚上写字把灯开起,免得长大了是个鸡摸眼。
鸡圈(juàn):监狱。
例句:老李你死不悔改哇,才出来几天就又进了鸡圈。
结梁子、结叶子:产生矛盾,结下怨仇。
例句:他们两家是上一代人为了抢一颗花生米子而结梁子的。
级别:级别,水平。
例句:对人家老李你还东说西说的,你和人家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的。
讲怪话:说脏话。
例句:说了不听还要讲怪话,谨防挨几个耳刮子。
捡粑合、捡撇脱:捡便宜,图省事,占便宜。
例句:你们还挑人家张幺妹,哟豁,遭人家老李捡了个粑合。
捡相因:买便宜。
例句:钱不多了,买东西要注意捡相因的。
捡脚脚儿:购买、拿取别人挑剩下的东西。
捡落地桃子:捡现成。
例句:你们忙死忙活,人家倒捡落地桃子。
巾巾吊吊:像乞丐破败的衣衫一样。
例句:不是我说你老李。
你说你都是巴蜀十大笑星了的嘛,袍哥一个,穿个衣裳还巾巾吊吊的。
进高烟囱:进火葬场。
例句:是那个进高烟囱的死娃儿,用火炮儿把我白菜炸一个一个的洞
死教不转:教不会,小孩不听话。
例句:跟你说了一铺拉子好话都听不进去嗦,郎凯死教不转呢
哈批搓搓:傻不垃圾。
例句:那娃儿哈批搓搓的,自己一米二不到,硬是要去惹人家一米八的。
斗是:就是。
例句:先挤牙膏再漱口,斗是郎凯的。
粑粑:油饼一类的饼,也指比较软的食物,如红薯等。
例句:幺儿乖,等哈儿爸爸给你买个粑粑吃。
我想说的是,重庆的方言是巴渝文化的一种体现,展现了当地人们的一种豪爽和不拘小节。
任何一句话用嫌恶的语气说出来都可以是在骂人。
英语高手请进
1.这里的 be true of ...是固定的用法,意思是“对。
。
。
是真的”,“符合。
。
。
”. 2.两种用法都可以的。
这是关于only的位置问题。
英语中,only既可做副词,此时通常放在行为动词之前如楼主的第一句;也可做形容词,如楼主的第二句。
此时是修饰后面的名词one reading 的。
3.选择题 1.正确答案 (D)through 后面有 a difficult time,名词短语,而前面有不及物动词went,故知与went搭配的一定要是介词,而非副词。
此外,根据几个短语的意思来看,went in for是喜爱,参加,与句意相勃。
而went through有经历,度过的意思,符合题意。
故正确答案是 应该是(D)through 2.(D) class 这里 band 是“乐队,组”,等, 意思不符合句意,而 class 有“级别”的意思,符合句意。
4.翻译句子(将下面的句子翻译成英语。
) 1. Those who are more capable and professional lose their opportunities, just because of their unperfect faces.
看钻石要看什么
评价与选购 从以下四个方面考虑(4C): 颜色(Colour) 无色为最好,色调越深,质量越差。
在无色钻石分级里,顶级颜色是D色,依次往下排列到Z,在这里只说从D到J的颜色级别,D-F是无色级别,G-J是近无色级别,从K往下基本没有收藏意义,K色以下的戒托做黄金的也很漂亮。
因为从K往下钻石就会逐渐偏黄,选钻的时候,选H 以上的颜色,I-J级别也在近无色范畴,但也能察觉到一丝微黄.具有彩色的钻石,如:黄色、绿色、蓝色、褐色、粉红色、橙色、红色、黑色、紫色等,属于钻石中珍品,价格昂贵。
红钻最为名贵. 不同国家和地区分别采用不同的颜色分级体系,的分为23个级别,分别用英文字母D-Z来表示。
其中D-N这11个级别是最常用的。
欧洲的颜色级别体系CIBJO为代表。
我国1996年新制定的国家标准综合了GIA、CIBJO,该标准将颜色划分为12个级别,并用D-N和<N来表示,还将百分数法和文字描述并用。
钻石颜色等级 D 100 极白 E 99 F 98 优白 G 97 H 96 白 I 95 微黄白(褐、灰) J 94 K 93 浅黄(褐、灰)白 L 92 M 91 浅黄(褐、灰) N 90 其中 FL - “Flawless”,完美无瑕。 在十倍放大镜下内外俱无瑕疵 IF - “Internally flawless”,内部无瑕。 在十倍放大镜下只有表面有轻微花痕 VVS1, VVS2 - “Very Very Slight”,非常非常小。 在十倍放大镜下有很难看见的瑕疵。 VVS1 净度高于VVS2。 VS1 and VS2 - “Very Slight”,非常小。 在十倍放大镜下可见瑕疵,但肉眼难以辨认。 VS1净度高于VS2。 SI1 and SI2 - “Slight Inclusions”,小瑕疵,肉眼可能看见。 I1, I2 and I3 - “Imperfect”,有瑕疵,可以被肉眼看见。 克拉重量(Carat) 在其他三C相同情况下,钻石价格与重量平方成正比,重量越大,价值越高。 钻石重量是以克拉为单位的。 1克拉(ct)=0.2克(g)。 把一克拉平均分成一百份,每一份是一分,商场价签上标的0.3ct,0.4ct就是所说30分40分.重量也有级别之分,0.30ct-0.39ct,0.40ct-0.49ct,0.50ct-0.69ct,0.70-0.89ct,0.90-0.99ct,1.00ct-1.50ct,1.50-2.00ct(每一级别分别由逗号隔开,不是一个级别的,就算差一分,价格也会相差很多,这就是为什么象0.48~0.49,0.68~0.69,0.88~0.89......会很难买到的原因) 切工(Cut) D级钻石 一颗钻石原石,即使扔到马路也不会有人注意,是切工赋予它,让它有着绚丽火彩.切工是指成品裸钻各种瓣面的几何形状及排列方式.切工分为切割比例,抛光,修饰度三项。 每一项都有五个级别,由高到低依次是EXCELLENT,VERY GOOD,GOOD,FAIR,POOR.一般所见都是标准圆钻型切工。 顶级切工的石头,对于光线反射可以达到一个最接近完美的比例,也就是三项E X(EXCELLENT)切工,但是像这种切工价钱也稍微贵一些,因为它的出成率比较低,比不是三项EX切工的价钱高5%左右,但三项EX的石头火彩绝对是最绚丽的. 几种常见切割形式 圆形 祖母绿型 椭圆形 梨形 公主方型 枕形 心形 八心八箭-邱比特切工 钻石价格的计算公式: 钻石的重量, 颜色color(直栏), 净度(横栏),的单价×100×人民币汇率(6.9)即 非洲之星Ⅰ 可得出钻石的价格。 举例说明: 算52分(0.52ct) F VVS1的价格 先查到该等级钻石单价是54 百美元 则价格计算为:54×100×6.9(人民币汇率)×0.52(钻石克拉)=19375.20元 编辑本段 鉴定 衡量一颗钻石品质的标准主要有四个维度,即重量(CARAT)、净度(CLARITY)、色泽(COLOUR)和切工(CUT),也就是通常所说的“4C标准”。 这个标准由GIA()创立,是目前在世界上包括中国最为主流的钻石评价标准。 钻石由国际认可的宝石学家进行鉴定并签发第三方独立的意见书,基于4C标准,继而决定钻石价格。 目前国际最权威的宝石鉴定鉴定实验室为IGI,GIA 钻石的简易鉴别方法:需要借助一个10-20倍放大镜作辅助并作数个简单的观测。 方法一: 观察钻石的腰部,若是磨沙状腰围就最适合用此方法,钻石因为比任何冒仿品坚硬,因此不会像冒仿品般出现细条状的纹路,钻石的腰围乃呈颗粒状外观。 方法二:钻石比冒仿品坚硬,冒仿品的刻面稜线往往会比钻石的感觉圆钝,而钻石的刻面稜线必是锐利的。 方法三: 基于钻石比冒仿品坚硬,冒仿品的刻面稜线常常出现磨损的情况。 方法四: 若钻石留有天然面,天然面上有机会发现到钻石独有的『三角形生长纹』。 方法五: 若钻石出现崩断口,外观通常皆为阶梯状,而冒仿品则会截然不同地呈弯弧或贝壳状。 汉 语 词 性 新 论问题的提起在系统的汉语语法研究已经开始了一个多世纪、汉语教学语法体系已经确立了几十年的今天,为什么要再提起这个问题呢 笔者认为,那是因为我们至今在这个问题上仍然处在一片混乱的局面、并未从根本上解决好汉语词性问题的缘故。 我认为,有必要来个正本清源。 说起词性(或叫“词类”),我们首先必须搞清楚什么是词性。 问题也正是由此引起的。 如果连什么是词性都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那么,还谈什么给汉语词汇定性分类呢 我们且看一看目前流行的词类的名称吧。 有的把汉语的词汇分词十一类,有的分成十类,有的分成九类,有的分成十二类,有的分得更多,比如十五类……。 但大体上是差不多的,可以说是大同小异。 我们只举代表性的例子说一说。 根据新近出版的邢福义先生的《汉语语法三百问》(其权威著作《汉语语法学》的通俗解释或另一个版本),他把汉语的词分成了三种十一类:第一种: 成分词(能单独充当句子成分的),包括(1)名词、(2)动词、(3)形容词和(4)副词第二种:特殊成分词(能单独充当句子成分,但具有特殊性的),包括(1)数词、(2)量词、(3)代词和(4)拟音词第三种:非成分词(不能单独充当句子成分的),包括(1)介词、(2)连词和(3)助词。 其他体例也与此差不多,比如有的把数量词合为一个词类的,有的还提出了语气词,有的还从传统的形容词中拉出两个新词类,叫什么“状态词”和“区别词”,有的把拟音词叫做象声词,等等。 还有的在大类上把词类概括为“实词”和“虚词”的,比如上面的第一种和第二种应该属于“实词”的范畴,而后面的一种应该算“虚词”。 所谓实虚,基本上就是根据能否充当句子成分尤其是主要的句子成分而言的。 实词比较实在,虚词比较空灵,后者主要起语法作用。 这里不对各种大同小异的分类法一一评论,只从以上这种典型的分类出发,评论一番。 究竟是根据什么把词分成这些种类的呢 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吗 如果仔细考查,不难发现,传统语法的所有这些分类法都是基于两个标准的:一个是语义,一个是功能(语法功能)。 我认为,问题正好就出在了这里 我们无论给什么分类,都只能根据一个标准,而不能使用两个,即“双重标准”。 使用双重标准,是无法做出任何科学的分类的,因为这本身就是一个自相矛盾的做法 比如“男女老少”就不是一个科学的分类:一方面按照年龄,一方面又按照性别,到底按照什么啊 当然,那仅仅是一个成语,说明各种人都有了,并非代表科学的分类(如果作为分类,那显然是行不通的)。 请看,“名词”、“动词”、“形容词”、“数词”、“量词”、“代词”和“拟音词”这些概念都是根据语义而提出的,而只有“介词”、“副词”、“连词”和“助词”是根据语法功能而提出来的。 就是说,在这十一类中,有一多半是按照语义定义的,只有一少半是按照功能定义的。 比如,说名词是“指称事物的”,是“表示人物事地的词”(更早的说法干脆就把它说成是“事物的名称”);说动词是“表示行为活动的词”;说形容词是“表示性质状态的词”;说数词是“起计数作用的词”;说量词是“表示计量单位的词”,说代词是“指代某种思想对象的词”,说拟音词是“对声音的模拟”。 这些概念当然都是语义概念,而非语法概念。 相反,传统上的“介词”(在语法构造中起中介作用的词)、“副词”(作状语的词、修饰谓词的词)、“连词”(起连接作用的词)和“助词”(起附加作用的词)概念则是按照语法功能定义的。 不言而喻,我们是在谈论语法,“词性”本来就是一个语法概念,而非语义概念。 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仅仅按照语法功能(或叫“句法功能”)这一条标准来划分词性呢 谈到这里,我们不禁想到了这些概念的来源。 它们最初是从哪里来的呢 我看是产生于翻译。 因为汉语虽然也有自己的语法但是系统地研究汉语语法仅仅是近代的事,而且是从模仿西方语言的语法体系开始的。 我们的许多语法概念都是从西方语言借用过来的,是翻译的产物。 那么,这些概念的翻译是否准确 由于长期以来就这么用惯了,大多数人似乎已经对此麻木了,不再思考一个为什么了,都觉得很自然了。 其实,我看并不然。 首先,这类翻译就不是那么准确的和科学的。 看一看英语,就可以知道。 所谓的noun(名词)、verb(动词)、adjective(形容词)、adverb(副词),都仅仅是一种语法概念,而非语义概念。 我们的“名词”、“动词”、“形容词”等之类的翻译法都不能反映出原初的含义,而仅仅是按照我们的理解行事的结果。 好像“名词”就一定和“名”有关,“动词”就一定和行为动作有关,“形容词”就一定要和状态性质有关,等等。 其实,这些词类在外语中往往都有自己固定的形态,人们一看就可以知道个差不多(并不是根据词义来判断,首先是根据词形和功能来判断的)。 搬用到汉语里,就麻烦了:语义成了判断的最重要的标准(如果不是唯一的标准的话),而语法功能则退到了次要的地位。 为什么呢 因为汉语的词基本上没有任何固定的词性标志,有的仅仅是意义的不同 那么,对两种根本不同的语言套用这相同的语法概念,能不出错吗 本来,词性是个地地道道的语法概念,而这样一来,它却成了一个语义概念(尤其是翻译的误导所致)。 当初的翻译是不是仅仅出于汉语只有意义区别而无形态区别这一特点而产生的呢 应该说,误解最初是由翻译引起的。 这种翻译的最大要害就是只看见了语义而忽视了语法,而这恰恰就造成了舍本逐末甚至颠倒是非的结果 比如英语,说“revolution”是名词,仅仅因为它是处于名词(noun)的形式,并非是说它不可以表示行为动作(“革命”当然就是一种行为、一种动作啊 )。 说beauty(美、美丽)是名词,也仅仅是因为它处于noun的形式,而非因为它不可表示状态性质之意(“美”当然可以指一种状态或性质啊)。 silence (肃静、寂静)当然就是一种状态,但它只能当名词用,而要想表示“安静的”,就必须变换其形式而使用那个形容词形式的silent。 外语中同一意义的词只要采用不同的形式就可以变成名、动、形、副词等各种词性(比如一个beauty, 可以有beautiful, beautifully, beautify等不同的词性形式)。 所以,词性概念根本就不是根据语义而来的,而只是根据语法作用(包括特殊的语法形式)而来的。 说到底,词性根本就不是一个语义的问题,而仅仅是一个语法功能和语法形式的问题(虽然在具体操作上常常与语义有关联)。 比如外语的“动词”并非指词义上的动(动作、行为之类)而是指在语言中的动态作用——作谓语。 准确的说法应该是“谓词”。 当然,外语中也存在着把语义和语法混淆起来的混乱现象,比如“代词”、“数词”、“拟音词”等,就不是根据句法功能划分的,而它们的语言里也有。 可见,我们汉语的语法中的混乱不仅仅是来源于翻译,也和外语语法本身的不够科学有关。 不过对于外语,我们没有必要说什么,先把我们自己的问题解决好就行了。 汉语词性的新定义那么,汉语究竟有没有词性呢 能仅仅根据汉语单词的形式不固定就说汉语根本就不存在“词性”这种语法概念吗 当然也不能。 因为词性主要是一个语法功能的概念(虽然也包括语法形态),所以,即使形态不固定、无规律的语言,也是有词性的,那就是根据不同的语法作用来定词性。 我以为,只要我们首先搞清了定义的标准,就好办了,一切问题都将迎刃而解。 我发现,“实词”和“虚词”、“体词”和“谓词”这类概念都很好,都是纯粹的语法概念。 不过这些都是较大的概念,需要细化。 我们就循着这样的路线重新给词性定义一下。 能做而且主要做主语和宾语的词属于“体词”(当然也不仅限于做主语和宾语,比如还可以做主语的补语和宾语的补语)。 能做谓语而且主要做谓语的词属于“谓词”。 这两类词都可以归入“实词”的范畴,而介词、连词、助词等可以归入“虚词”的范畴。 此外,在实词中还有两个附加词类——修饰体词的词和修饰谓词的词,就是能作定语的词和能作状语(包括前置和后置)的词。 它们可以分别叫“定词”和“状词(是否仍沿用“副词” )。 “定词”除了做前置的定语外,还可以放在判断性的动词等特殊动词之后做主语的补语(比如在“这个是大的”中,“大的”就是主语补语)。 拟音词基本上属于谓词,有时也属于体词,所以,没必要在语法上单独提出这个概念。 数词和量词也都兼有体词的功能和定词的功能,有时还可以有其他功能,所以,它们是特殊的词类,可以单独讨论,不过也没必要做为单独的词性对待。 代词是个非常复杂的概念,基本上属于体词,有时也可以做定词(体词的附类),有的代词也代指其他词类,比如谓词、定词和状词。 例如,“怎么”就是代指状词的。 可以保留这个术语,但也无必要把它作为一个语法上的词性对待。 拟音词的情况也是如此,仅仅是个语义概念。 在体词中包括传统意义上的“名词”、“代词”、“数词”和“量词”等。 在谓词中包括传统意义上的“动词”和“形容词”。 汉语的“形容词”可以直接作谓语,这是汉语的一大特点;其他语言一般不能,往往还要加上一个动词,即只有动词才能作谓语。 例如:这个很大。 她很幸福。 英语必须说成This is very big. She is very happy. 而不能说This very big, She very happy。 所以,汉语的“形容词”有时可以算作谓词,而其他语言一般不能。 “形容词”的原初英文词是adjective,它本来是“名词的修饰词或描写词、非独立的词”的意思,因而它的基本作用是做定语,即做体词的附属成分),但有时也直接做谓语(如前例)或表语(比如处于判断动词后:这是大的),但不能做状语(前置的或后置的)(注意:按照我的语法体系,传统的“补语”是被我看作“后置状语”的)(做状语的“形容词”应该算作“副词”)。 所以,在这一点上它是和“状词”(副词)有严格的区别的。 从它的整个含义看,它既有“定词”的功能,又有“谓词”的功能,所以可以看作是“体词”和“谓词”两种功能兼有的词类。 具体而言,可以把“形容词”分成“定语形容词”、“谓语形容词”和“补语形容词”三小类(有的词是三种功能兼有的)。 但一定要把它从“状语”或“状词”中排除出去。 那么,“定语形容词”和“补语形容词”(注意:我说的“补语”是指主语补语或宾语补语,不是传统的汉语语法的“补语”)可以并入“定词”之内,而“谓语形容词”可以归入“谓词”之内。 (关于补语和谓语的区别,要根据前面是否有动词。 例如:“这是大的”中的“大的”属于主语补语,而“这个很大”中的“大”则是谓语。 )传统的“副词”概念比较窄,而且确实是按照语法标准提出的,即做状语的词。 所以,这个概念可以保留。 或换一种说法,叫“状词”。 在英语中,“副词”和“状语”同出一源:一个叫adverb, 一个叫adverbial。 那是很科学的。 所以,我仍主张把“副词”改为“状词”。 “动词”这个概念可以保留,但是必须重新定义:它的含义不是指语义上的“行为动作”之类,而是指语法功能上的动态特点,即直接做谓语的功能。 谓词,是句子的核心,是其最活跃的部分(句子的生命之体现。 一般而言,一个句子可以无体词,但是不能无谓词)。 “动词”基本上等于“谓词”,但又不尽然。 应该说,“谓词”是一个较宽的概念,是高一级的概念,而“动词”被包含其中,是下一级的概念。 如果说在其他语言(比如英语)中谓词就是动词,那么,在汉语中谓词还更宽一些,不仅包含动词。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汉语里,甚至“动词”和“形容词”的界限有时都不明显。 例如,在“他很高兴”和“他很同意”这两个句子里,你凭什么说“高兴”就一定是形容词而“同意”就一定是动词 且不说二者在这里起的语法作用是完全一样的,而且,在语义上,“高兴”和“同意”都可以表示一种心理状态啊 如果翻译成外语,我们对这两个都可以使用动词(或形容词)形式,不一定使用形容词和动词两种词类。 因此,在做谓词使用的时候,也很难区别开“动词”和“形容词”。 那么,笼统地叫“谓词”还真似乎是一种更明智的选择呢 总结起来,我的重新定义结果如下:笼统地分成“实词”和“虚词”两大范畴(根据是否直接充当句子成分)。 在“实词”中包括“体词”、“谓词”、“定词”、“状词”四个小类。 而在“体词”中包括“名词”、“代词”(代词也可被包括在其他大类中,因为它不光代替体词)、“数词”和“量词”(数量词也可能具有定词的功能或其他功能)等;在“谓词”中包括“动词”和“形容词”。 在“定词”中包括“定语形容词”和“补语形容词”以及“名词”、“数词”、“量词”,甚至“代词”等。 在“状词”中仅仅包括“副词”,或干脆就把“副词”叫“状词”。 在“虚词”中包括“介词”、“连词”和“助词”。 从最小的级别看,一共11种词性(或叫“词类”):名、代、动、形、数、量、副(状)、拟音、介、连、助。 虽然在最小一级上仍然保留了原来的名称,但是那只是对原来的语义原则的产物的一种尊重,或者说一种过渡吧(原来的分析结果还可以作为参考而使用)。 最重要的是我给定出的四个“二级词类”:体、谓、定、状。 它们是完全按照语法功能定义的。 加上原有的三个虚词“介、连、助”,应该说我的新概念词类一共是7个:体、谓、定、状、介、连、助。 这7个类别也可以被看作是处于一个等级的。 它们都是严格的语法意义上的词类。 而且,它们也可以包含所有的词类(包含原有的以语义定的词类。 原有的词类是可以作为子类而存在的)。 在语法分析上,仅仅按照这7类,就够了。 这样,就可以在汉语词法上实现一场彻底的革命。 从原来意义的词类可以如此广泛地交叉在我的新词类里(几乎没有规律)这一事实,就可以看出以语义定词类是不够科学的。 不过,以语义定词类的确很实用,很便于操作,在这方面也已经积累了大量的实用性的成果,对此,我们还是应当参考的。 也正因为这样,我才仍然保留它们的存在,让它们在一定范围内继续发挥作用(但是也得经常纠正其中的一些错误理论)。 汉语词性的特点下面,我们再看看汉语词性的特点。 总的来说,汉语词性有两大特点:第一,基本上无固定的形态;第二,词性非常灵活多变。 第一点勿庸赘言。 主要看看第二点。 这花很美。 这的确是美的。 你美什么啊 别美了 我欣赏她的语言之美。 她的美震撼了全世界。 这真是美餐啊 你可以美美地睡上一觉了。 歌唱得很美。 一个“美”,在不同的场合就可以有不同的作用:在第一个例子,它是做谓语的(或狭义的“表语”)。 在第二个例子中,它是动词(谓词),直接做谓语。 在第三个例子里,它是体词(“名词”),做宾语或主语。 在第四个例子里,它是定词(做定语,体词的修饰语)。 在第五个例子里,它以重叠的方式变成了状词(“副词”),做状语。 在最后的例子里,它也是状词,做后置状语(传统上所谓的“补语”)。 那么,你说“美”到底是什么词性 再如:孩子,你别傻了。 一般而言,“傻”是个“形容词”,即主要做定语或表语,但是这里用在祈使句中,你还能说它仍然是“形容词”吗 它显然已经变成了动词。 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你别继续傻下去了。 这是典型的动词用法啊(前面有状语、后面有助词) 再如:游泳是一种很好的运动。 我喜欢游泳。 我喜欢在海里游泳。 “游泳”一般是做动词用的,于是,传统的语法就只把它做动词看待。 对于第一句话,他们说是“动词做主语”,而对于第二句话,他们说是“动词做宾语”,而对于第三句话,他们说是“动词短语做宾语”。 按照本人的看法,第一句里的“游泳”就干脆是名词(体词);第二句里的“游泳”也是体词(名词),而第三句里的动词短语其实也是个体词性的短语(整体上相当于一个体词——名词)。 由于汉语并没有特殊的词性标志,我们最好还是干脆按照句法功能判定词性,那样要简单得多。 如果是其他语言,做主语或宾语的时候,一定不能直接使用动词的谓语形式,必须变成“非谓语的形式”(其实就是体词形式,如不定式、动名词、分词)才行。 说“动词做主语(或宾语)”并不符合一般的国际惯例,更何况汉语的词性并不是先天就确定下来的,那么,为何还要如此僵化呢 对于一个单词的情况,很好处理:做什么样的成分,就是什么词性,不必说什么“动词做主语或宾语”(此外还有“形容词做主语或宾语”等等)这样荒唐的话。 对于由动词组成的短语,如果整个短语起的是体词的作用,那么,也不要说这是动词短语做主语或宾语,应该灵活地改为“体词性短语做主语或宾语”。 动词的“体词化”(或“非谓语化”)尤其是在短语里特别明显。 当然,短语是另一个话题,此处不多加论述。 再如:这孩子又高了许多。 天渐渐地黑了。 你能说这“高”和“黑”仍然是“形容词”吗 显然也已经成了动词。 带了个时态助词“了”,或加上个副词“渐渐”,都是明显的动词标志。 在意义上,都表示一种过程,而非状态。 “高”=变高、长高;“黑”=变黑。 应该说,凡是用在祈使句中的“形容词”都已经“动词化”:小心点儿 别大意了 乐观点儿 再高点儿,我看不到。 低点儿 热情点儿 谦虚点儿 应该说,凡是用在能愿动词后面的“形容词”也都已经“动词化”:你得胖点儿了,这样瘦不行。 你必须轻松点儿,随便点儿。 我不能轻松下来啊 你能大声点吗 你能轻点儿吗 再如,所谓的“副词+名词”(“副词修饰名词”)的问题:只两瓶黄酒、仅仅七个学生、最里面、最开始部分、最上头、大约三辆汽车、共二十块钱、又一阵暴风雨、再一个问题、才五张桌子、很现代、很精神……其实,根本不是什么副词修饰名词,实际上有三种可能:第一,那所谓的“副词”已经变成了形容词(定词)(如:只两瓶黄酒、仅仅七个学生。 英语的only就是副词和形容词两种词性兼有的。 这里的“只”和“仅仅”也类似。 同样道理,“最”也可以当形容词用,就像英语的most一样)。 第二,是省略了谓词的结果(如:大约三辆汽车=大约有三辆汽车;共二十块钱=共有二十块钱;又一阵暴风雨=又来一阵暴风雨;再一个问题=再提一个问题;才五张桌子=才有五张桌子。 第三,后面的“名词”已经形容词化(如:很现代=很时髦、很具有现代气息;很精神=很帅、很潇洒)。 再如时间地点词(名词)做状语的问题:今天我休息。 上午我没课。 古代有个大诗人李白。 屋里坐 北京见 其实,这些词都已经“副词化”,因此都可以算作副词(按照我的新叫法是“状词”)。 比如在英语里,today(今天)既是名词,又是副词,就看如何使用了。 你能仅仅根据词义就断定某个词就是什么词吗 再如:连“都”这个“副词”都可以变成其他词类。 都来了吗 都同意。 都不想去。 在这类句子中,如果我们说“都”是做主语的,也可以,因为可以把它理解为代词,代替具体的所有人(或物)。 当然也可以理解为省略了主语,仍然把它做副词看待(“都来了吗 ”=“大家都来了吗 ”、“都同意”=“大家都同意”……)。 在英语中,all就是代词,同时也可做副词。 再如:只要加上一个“地”,就可以把名词、形容词(定词)等词类变成副词(状词):理智地做事、历史地看问题、“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文革时《毛主席语录》的前言)、幽默地讲述一个故事、紧张地看着他…… 传统的语法把“的”、“地”和“得”看作“结构助词”。 笔者认为只有“得”是地地道道的结构助词,而“的”和“地”都可以看作表示词性的词尾(不过在和短语相接的时候例外,比如“有计划地”)。 一个表示形容词(定词),一个表示副词(状词)。 汉语也有这类表示词性的词尾,就像英语的-ful(形容词词尾)和-ly(副词词尾)一样。 可以通过它们随意改变词性。 关于这一点,可以参见本人的另一篇专论。 再如:“五斤重”或“重五斤”。 这是数量词变成了状词的例子(一个做前置状语,一个做后置状语,但实质是一样的,都修饰“重”这个谓词)再如:汉语的动词和介词有时很难分清界限,动词可以当介词用,或相反,因为介词基本上都是由古汉语的动词演化而来。 例如,“用”字在“用电脑翻译”、“用嘴说,用笔记”等等这类句子里,我们完全可以把它看作介词,表示工具、手段之类的意义,而把后面的动词看作句子的谓语动词,因此,不必把这类现象说成什么“连动式”。 通过用“以”字这个地地道道的介词代换它进行试验,就可以证明这一点。 ……凡此种种,这样的例子可以举出无数来。 我们可以对传统的汉语语法体系提出无数这类批评和纠正。 总之,我们必须承认:汉语的词性是随时而变的,特别灵活自由。 由僵化的“语义为准”原则到灵活的“功能为准”的原则转变,就可以自然地理顺许多语法现象,而且可以令分析更加简便(概括性更强,更能以一驭十、驭百、驭千、驭万……)。 当然,其他语言也有一词多性的现象。 但是要比汉语少得多。 汉语的几乎每个词都是不定性的。 如果说外语的词大多有定性,那么,汉语则相反:大多数都无定性。 如果说外语的词性不定是个特殊的现象,那么,汉语的词性不定就是个普遍的现象了。 这正是汉语词性(如果说有的话)的特点 这一点也正是汉语的一大特色 汉语的“一词多性”正如“一词多义”或“一字多义”一样,是一种很经济的语用做法。 “一词多义”在任何一种语言中都是个普遍的现象,但是,“一词多性”,除了汉语以外,在任何一种语言中恐怕都不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一词多性”在汉语中如此普遍,因此我们就可以省去不知多少麻烦 这正是中国人的聪明智慧的体现 一词多义,一般也不会造成什么不便,因为有了一定的语境,意义自然就可以确定了。 一词多性,也不例外。 任何一个词的词性都不是先验地确定好了的,必须到具体的语法环境里根据它所起的作用来确定。 当然,不是说不能根据词义和词形本身来大体地推定词性,如某类意义的词或以某种形式开头或结尾的词一般就是充当某种词性的。 但那都不是绝对的标准。 如果说为了学习的需要尽可能多地知道一些词汇的用法(包括词性特征)是有用的,那么,这个问题恐怕不能交给语法来解决,要由语义学家和词汇学家来解决,那会涉及无穷无尽的实践性的规则,语法学是无法完成此重任的,那至少不是理论语法学所该做的事情。 基础语法或理论语法只是提供一个“大纲”和基本框架,不可能面面俱到地解决具体的语义和用法问题。 从这一点看,也可以说为汉语建立一套科学的语法体系并非无限遥远或无限复杂,可以在短时间内办到。 附带说一点:在词性定义上的“解放”,对汉语来说,还有一个巨大的好处:防止用僵化的思想束缚汉语的发展 归根结底,语言本身的自然发展、约定俗成(自然形成)才是第一性的,而人为的任何规定都是第二性的,是总结实践的产物。 如果规定过了分,就必然会阻碍自然的发展,起到消极的作用。 那样的“语法”可就成了语言的敌人了 比如,说某个词就是某种词性,一变化使用就是“语法错误”、“病句”。 也许,一开始的时候是“病句”,可是慢慢地随着人们的普遍接受,它就成了一个新的语言现象,不再“有病”了。 比如,说“突然”既是副词又是形容词,而“忽然”仅仅是副词。 为什么这么说呢 那是通过语言试验做出的结论:可以说“突然的变化”,但不能说“忽然的变化”。 不过,我认为,也许这仅仅是现在的用法,也许,将来“忽然”也会兼有形容词和副词两种词性的。 当大多数人都说“忽然的什么什么”的时候,它就会变成了形容词。 说不定 再如,“幽默”这个词本来是个音译的外来词,按说是不可拆开的。 但是,我们不是听到过“幽他一默”这种中国化的说法吗 “春风又绿江南柳”这句著名的诗句就是把一般为形容词或名词的“绿”当动词用了,显得特别生动、有创造性 文学中或生活中的新语、新用法层出不穷,最好的做法是采取一种开放的态度,任它们自然选择、自然淘汰。 优秀的创造自然会留下,拙劣的语汇自然会被淘汰。 总的来说,汉语的“词性”的意义并不大,这是由汉语本身的特点决定的。 因此,到了把汉语从几十年来形成的僵化的词性概念中解放出来、恢复其本来面目的时候了 汉语语法的重点应该在句法上,而非在词法上。 本书给出的定义和分析方法也仅仅是个参考,也不必过多地拘泥于这套系统。 尤其是,不要用词法来套句法,不要用“词性”来鉴别句子的对否、判断句子成分,那对汉语来说是一种颠倒的做法(虽然对外语来说可能正好)。 这条基本思路很重要。汉语词汇分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