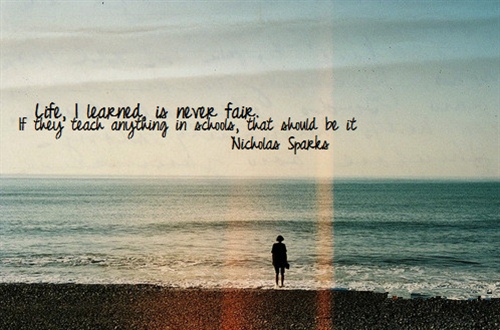关于汽车的唯美句子
车胡秉言车。
载货拉人过岭坡。
油门踩,一路有欢歌。
车。
快跑多拉昼夜逴。
因生计。
虽苦乐呵呵。
车。
酒后疲劳莫乱作。
责任重。
生悔更蹉跎。
祝开大车的顺利的句子
出车在外,老婆交代:滴酒不沾,只准吃菜;稳点开车,不要太快;遵守交规,自由自在;如果累了,歇会再开;家人盼你,平安归来! 千言万语平安是福,千山万水遵规为路,千锤百炼自信有度,千方百计谨慎起步。
让我们忠诚地守卫交通安全,一天又一天;让我们执着地追求幸福,一年又一年;温馨是永远的伴侣,平安是共同的心愿。
文明驾车,平安常相伴;守法行路,畅通好心情。
汽车一般是准点到站,还是准点发车,如果是准点发车的话,是不是应该提前上车
一般汽车都是准点发车的,但到站时间会由于路况和天气原因延迟或提前。
一般提前10—15分钟到候车室等候,有的地方即使晚点了司机也会等个两三分钟最多了。
为了保险起见还是提前去吧。
形容铁轨的句子有哪些
1.拥有博爱和向往自由的人,他们叫----骑士
2. 我可以快过风,但追不回时间 3. 你只看到我的背影,却无法感受我的激情,你有你的A8,我们有属于我们自己的机车,,你嘲笑我,不知四轮的安逸,我可怜你,不懂速度的真谛。
你可以轻视我的极速
描写葬礼的句子
拿着“引”字白纸帖的吴府执事人们,身上是黑大布的长褂,腰间扣 着老大厚重又长又阔整段白布做成的一根腰带,在烈日底下穿梭似的 刚从大门口走到作为灵堂的大客厅前,便又赶回到犬门口再“引”进新 的吊客——一个个都累得满头大汗了。
十点半钟以前,这一班的八个 人有时还能在大门口那班“鼓乐手”旁边的木长凳上尖着屁股坐这么一二分钟,撩起腰间的白布带来擦脸上的汗,又用那“引”字的白纸帖代替 扇子,透一口气,抱怨吴三老爷不肯多用几个人,可是一到了毒太阳直 射头顶的时候,吊客象潮水一般涌到,大门口以及灵堂前的两班鼓乐手 不换气似的吹着打着,这班“引”路的执事人们便简直成为来来往往跑 着的机器,连抱怨吴三老爷的念头也没工夫去想了,至多是偶然望一望 灵堂前伺候的六个执事人,暗暗羡慕他们的运气好。
汽车的喇叭叫,笛子,唢呐,小班锣,混合着的“哀乐”,当差们挤来 挤去高呼着“某处倒茶,某处开汽水”的叫声,发车饭钱处的争吵,大门 口巡捕暗探赶走闲杂人们的吆喝;烟卷的辣味,人身上的汗臭;都结成一片,弥漫了吴公馆的各厅各室以及那个占地八九亩的园子。
(茅盾: 《子夜》第31页) 举行仪式时,我感到一种恐慌,一种对将来的预感,我站不住了。
最后尸首装入棺材钉起来。
然后助葬的人把棺材放在柩车上,就出发 了。
我只伴送着走完了一条街。
走到那儿,赶车的突然把车赶得飞跑 起来,老人跟着柩车跑——大声啼哭,可是跑的动作时时使哭声变得颤 抖,而且。
忽断忽续的。
后来他的帽子掉了,可怜的老人并不停下来拾, 虽然雨打在他头上,又刮起风来,雪雨不住地刺痛,击打他的脸。
他从 柩车这边跑到那边,好象他不了解这件残忍的事一样——他的旧大衣 的两边给风吹起来象一对翅膀似的。
衣服的每一个口袋里都装着书凸起来,他的胳膊底下挟着一本特别大的书,他紧紧的抱在胸前。
送葬的 行列经过时,过路人脱下帽子,在胸前划·十字,有些过路人站住惊愕的 凝视着那司·怜的老人。
不时有书从他的口袋里滑出来,掉到污泥里,因 此,有人叫住他,叫他注意他的书掉了,他就站住,把书拾起来,还是跑 去尾随着柩车。
在街的一个角,一个褴褛的老太婆紧跟着他,最后一直 到柩车拐弯,我的眼睛看不见了。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穷人>>笫 64—65页) 卡拉特特的妻子决不能就把丈夫一人丢在坟墓里。
而且那不幸的女人自己也不愿意独自一人活下去。
这是风俗,同时也是职责,这种殉夫的事例在新西兰的历史里是常见的。
卡拉特特的妻子出场了。
她还很年轻。
她的头发乱披在肩膀上, 又号啕,又哽咽,哀声震天。
她一面啼哭,一面声诉,模模糊湖的活音, 缠缠绵绵的悼念、断断续续的语句都颂扬着死者的品德,哀痛到极点 时,她躺到土墩脚下,把头在地上直擂。
这时,啃骨魔走到了她的跟前。
忽然那可怜的牺牲者又想爬起来, 但是那酋长手里舞动“木擂”——一种可怕的大木槌——一下子又把地 打倒下去。
她气绝了。
([法]凡尔纳:《格兰特船长的儿女》第664页) 他向围立在墓穴四周的人群扫了一眼,全是警察,全都穿着便服, 同样的雨衣,同样的笔挺的黑帽子,雨伞象佩剑一般握在手里,这些奇 异的守灵人,不知风从哪儿把他们刮来的,他们的忠实显得不真实。
在他们后边,排列成梯队的市政府乐队,穿着黑红二色的制服,是匆匆召集来的,都拚命设法把自己金色的乐器在外套下保护起来。
他们就这 样围在棺材周围,它平放在那边,一只木制的匣子,没有花圈,没有鲜 花,但却是唯一的温暖所在,正在这一无休止的雨滴之中安葬,雨水单调地拍溅着地面,始终如一,永无尽止。
牧师早巳读完了。
没有人注意 到。
这里只有雨水,人们只听到雨声。
牧师咳嗽起来,先是一声,接着好几声。
于是低音喇叭、长喇叭、号角、短号,低音笛一齐奏鸣,傲慢而雄壮,乐器在雨帘中闪着金光,但是它们也沉没了,消散了,停止了。
一切全退缩在雨伞之下,雨衣之下了。
雨始终不断地下着。
鞋子陷在泥泞之中,雨水汇成小河流入空的墓穴。
([瑞士]杜仑马特:《法官和他 的刽子手》第45页) 举行葬礼的一切早已准备好了。
元老们把灵轿在火葬的柴堆旁边 放了下来。
范莱丽雅走了上去,阖上了死者的眼皮,又按照当时的风 俗,把一个铜币塞到死人的嘴里,以便他付给兴隆,充作渡过波浪汹涌 的阿凯伦河的船钱。
接着,这位寡妇在死者的嘴唇上吻了一下,按照风俗大声说:“再会了!按照老天安排的次序,我们会跟着你来的。
”乐工开 始演奏哀乐,那些奉献人就在乐声中把好些指定作为牺牲的动物牵过 来杀死,把它们的鲜血与牛奶、蜜和葡萄酒掺和在一起,然后拿来洒在 火葬的柴堆周围。
这一切完毕以后,送葬的人就开始向柴堆上面浇香油,抛掷种种香料,堆上不计其数的桂冠和花圈。
花圈多极了,不但盖满了整个柴堆, 而且在柴堆四周厚厚地叠了起来。
一阵轰雷一般的鼓掌声滚过马尔斯广场,回答这位年轻的凯旋者 和征服阿非利加的元帅对死者所表示的敬意。
一阵火焰突然进发出 来,随即迅速地蔓延开去。
终于,整个柴堆发出无数蜿蜒飘动的火舌, 而且被一阵阵云雾一般的芳香的浓烟所笼罩了。
([意]乔万尼奥里, 《斯巴达克思》第246页) 泰戈尔达斯·穆克吉的年老妻子在连续发了七天高烧之后死了。
老穆克吉先生经营粮食生意发了大财。
他的四个儿子、三个女儿、孙男 孙女、女婿和亲戚朋友以及仆人们全都赶来了,乱哄哄地象是在过大节 日。
村子里的人们也成群结队地赶来参观这一隆重而体面的丧仪。
女儿们哭泣着在母亲的脚跖上浓浓地涂上了一层胭脂,在她的中 分的发缝里抹上了一道朱砂。
儿媳妇们在婆婆的前额上敷上了檀香膏 沫,替婆婆裹上了贵重的纱丽之后,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服,把披在头 上的纱巾拉得低低的,向婆婆行了最后的摸足礼。
五彩缤纷的鲜花,绿色的嫩叶,浓郁的檀香,各色的花环,一片‘喧哗 声里使人嗅不出悲哀的气息——这似乎是豪门的主妇在五十年后又一 次扮作新嫁娘起程到丈夫家里去。
老穆克吉先生平静地向自己老伴做了最后的告别,暗暗地抹去了两滴泪水,开始劝慰起悲哀地哭泣着的女儿和儿媳妇来。
“诃利!诃利!”闷雷般的颂赞声震撼着清展的天空,整个村子的人们眼随着丧仪的行列出发了…… 火葬场在村外河边沙滩上。
在那里焚烧尸体需用的木柴、檀香屑, 酥油、蜂蜜、松香、娑罗树脂……早巳准备妥当。
……当尸体被安置在宽大、堂皇的焚尸的柴堆上的时侯……大家齐声呼唤着“诃利”的圣名,儿子拿着被婆罗门祭师的经咒净化了的火把,点起了葬火……儿子手里的火I这真是谈何容易啊J把丈夫、儿子、 女儿、孙男孙女、亲戚朋友、仆人——尘世间的一切,整个留在熊熊的火焰里,婆罗门老太太升天去了。
([印]查特吉:《奥帕吉的天堂》 《外 国短篇小说》中册第462—4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