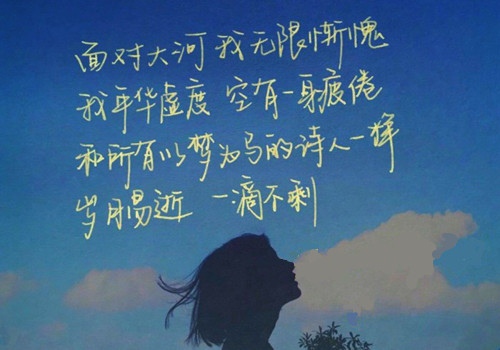怎样才能做一个讲道德,有品行的人
做一个讲道德、有品行的人来源:板桥社区 发布时间:2016-06-13 10:50:16 点击:1040 今天,我很荣幸地站在这里与大家一起学习交流党员如何成为一个讲道德、有品行的人这个话题。
意大利诗人但丁说过:“一个知识不全的人可以用道德去弥补,而一个道德不全的人却难以用知识去弥补。
”我们今天不去讨论道德和知识谁更重要,但我相信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最需要的是具有高尚道德和品行的知识者,对于全国八千七百多万党员同志更是如此。
首先,我想跟大家分享这样一个小故事。
一个单身女子搬了家,晚上忽然停电,她赶紧点起了蜡烛。
忽然听见有人敲门。
开门一看,原来是隔壁的小孩子, 只见他紧张地问:“阿姨,你家有蜡烛吗
” 女子想:天哪,刚来就借东西,以后就更没完没了了。
于是她冷冰冰地说:“没有
小孩笑了,还带着一丝得意: “我就知道你家没有
妈妈怕你害怕,让我给你送蜡烛来了。
” 听到这里,相信大家都跟我一样,心中涌起一股暖流。
城市的钢筋混凝土隔绝了邻里之间的实际距离,但不知从何时开始,人们的心理距离也慢慢拉开,面对许多事情,逐渐变得冷漠,内心慢慢麻木。
邻居之间的感情,不都是一个先付出,另一个才知道回报对方的付出吗
我希望大家都做首先打开心房,付出自己真心的那个人,用一个人的火苗温暖融化大家的心灵,洒下爱的种子,开放出更多的“道德之花”。
有品行,就是重视培养自己高尚的道德和操守。
品行主要依靠个人道德的修养和锤炼,它没有相应的法纪约束。
那么,当代年轻人如何成为一个有品行修养的人
首先,我们要尊重自己的父母。
父母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她们生我们养我们对我们付出了很多,他们总是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给与我们支持和帮助。
做到孝顺父母,关心父母,这样对于我们自身品行而言都是必不可少的。
其次,做事负责,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做任何一件事的时候都要仔细慎重,同样也要对事负责,不要因为怕犯错就不敢于承担责任,这样只会学会临阵脱逃,胆小怕事的,勇于承担、勇于负责是很重要的。
再次,做事成熟稳重。
莫要因为一些小事而显得浮躁慌乱,不要让他人看着显得我们很慌乱,首先要学会冷静的思考,冷静头脑对于处理事情是很重要的。
最后,建立自己的理想,脚踏实地。
很多人在我们的眼里是很幼稚或者很令人生厌的,最主要的是缺少道德修养或文化水平,当然还有价值观或人生观的差别。
想要做一个有品行有修养的人,既要有文化和道德修养,又要有自己的人生目标,树立人生目标,之后脚踏实地的去做,这样才是积极的人生,有意义的人生。
我自己现在正处于创业阶段,从事的是教育行业。
我对自己最基本的要求就是一定要热爱自己的每一位学生,先有热爱学生,再有诲人不倦。
学生都有对爱的本能要求,希望得到老师、家长及社会的热爱,当老师满足了他们的这种需要时,就能有效地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更有利于成才。
热爱学生并不是对学生溺爱、迁就和放纵,而是要从各方面严格要求学生,热爱与严格要求是并行不悖的。
俗语说,“严师出高徒”,“教不严,师之惰”。
这些话是很有道理的。
但是,严格并不等于惩罚,教师对学生要严慈相济,严中有爱,严中有度,严中有方,使学生对自己敬而爱之,而不是敬而远之。
诲人不倦,就是教育学生要特别耐心,全心全意培养他们,希望学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甘当一辈子人梯,使学生真正成才。
我们党员同志只有“讲道德、有品行”,才会牢记使命,牢记入党誓言,才会对得起良心,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才会在重大关键时刻的锻炼和考验中坚定信念,在处理各种复杂问题中经受考验,不断铸就政治品行。
急需一篇《读书让生活更美好》作文 不少于800字 谢谢
使生活更美好书香城市美丽;阅读,让生活变得更加美好。
在长春和深圳,读书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
没有流于形式,而是落地生根。
两座城市和生活在两座城市中的人们,品尝到了读书的益处,感受到了浓郁的文化氛围。
在大力倡导文化建设的今天,这两座城市的书香气息,浓郁芬芳、沁人心脾。
朗朗的读书声,传出了文明、健康、和谐的理念。
经过30年的快速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吃、穿、住、用、行等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今非昔比。
在生活富裕了之后,如何丰富和提升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成为一个迫切需要解答的课题。
一个社会是否和谐、美好,不仅要看经济社会发展,还要看人们的精神境界和文化素养。
通过倡导读书,提升市民的思想文化水平,推动形成崇尚读书学习的良好社会氛围,无疑是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有效途径。
长春和深圳的读书活动,开展得细致、扎实,没有就读书论读书,而是把引导广大市民读书和城市发展的战略规划结合起来。
长春通过倡导市民读书,把民生工程从基本物质生活保障提升到精神文化层次;深圳把读书活动提到实现公民文化权利、提高市民综合素质和城市综合竞争力的高度来抓。
在这些理念指导下,还建立了一整套具体、务实、可行的政策和措施来保障,比如长春举办大讲堂,深圳举办读书月等等。
既有完善的政策指导,又有具体可行的举措,从而保证了读书活动能够持续开展和真正起到实效。
城市文化建设只有长期坚持下去才能见到实效。
文化建设是一项慢功、细活,无论倡导读书还是发展艺术,口号不需响亮,动静不需太大,只需做细、做实。
长春和深圳开展读书活动为城市文化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那就是地方政府和文化部门要转变观念,从幕后站到台前,积极发挥自身功能,主动引导和促进社会文化建设。
读书让我的生活更美好杜甫诗云: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的确,读书多了,眼界和思想自然也会开拓很多。
调入新的单位,阅览室的的藏书多了,读书的机会更多了,每周还有学校自己的特色读物《大家推荐》,教育局组织的读书富脑活动,让我又读到了更多的好书,我深深的体会到读书给我带来快乐,读书让我更深的感悟熟悉的世界,变幻风云,人间诡秘,生活的酸甜苦辣;读书让我开阔了眼界增强了业务素质。
一、读书,充实了我的生活。
从事了教师的职业,让我养成了读书的习惯,读书、反思、整理书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每晚睡前总是拿起床头早已准备好的几本书仔细阅读。
课余时间也经常读一些有关自己专业成长的书籍,同时为了使读书更有助于自己的成长和成熟,我也做了大量的读书笔记,包括剪贴或摘录对自己有启发的内容;不定时的对自己读书的内容进行反思体会,将读书时浮现的感触,随想,联想进行记录。
读书、做笔记的过程充实了我的生活,让我对生活充满乐趣。
二、读书,磨练了我的性格。
宽容是一种美德” “用希望别人对待你的态度去对待别人。
”“宽人律己,换位思考” “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不知何时,这样的词句分类充斥了我整个的心灵,渐渐地,形成了我乐观的生活态度。
对待朋友时让我能够容忍朋友的过错,包容的心态让我拥有了更多的朋友。
读书让我懂得应该耐心地倾听朋友的心声,真诚地分享他们的喜怒哀乐,读书锻炼了我的耐性,让我懂得了真诚。
而这些,应该是最起码的交友之道吧
三、读书,陶冶了我的情操。
记得看到过这样一段话:“山里教师与做官无缘,坐一回小车也是稀罕,他把理想翻弄成破残的教案,喝墨水,空穷酸。
当别人在洋楼里潇洒,他却在油灯下熬战,飞走了的有了高官厚禄,没逃的却在低矮的屋檐下蜗旋。
辞职的已是腰缠万贯,留下的却在筹划着柴米油盐……”读后,我感动的几乎热泪盈眶,被山里教师的那种淡泊名利和安平乐道的精神所深深的折服,不仅仅是感动,更多的是深深的震撼和汗颜。
从那时起,我深深懂得了:当好教师就要淡泊名利。
高尚的师德,是对学生最生动、最具体、最深远的教育。
既然干了这一行,就要对这一行负起责来,就要有淡泊名利的思想。
也是从那时起,我更加热爱教育这一职业,感到自己拥有了超然脱俗的情怀。
能够心平气和地看待自己的职业,自己的工作,对工作充满了激清。
四、读书,增强了我业务素质。
教育学家曾说:“要给学生一杯水,老师要有一桶水。
”我们是人民教师,我们肩负着教育跨世纪的建设价值规律的历史重任。
但在这个信息化飞速发展的时代,知识、技术的更新可谓是一日一个样。
要给学生一杯水,老师有一桶水,已远远不够,教师应拥有整个的汪洋大海。
时代的进步会的发展的,要求教师掌握的东西也越来越多,要多读书,多一些知识的储备,才能满足现在这群小家伙的需要。
要想在自己的课堂上做到够游刃有余,我必须要多读书,读好书,时刻不断的积累能量。
书,改变了我的生活态度,书,丰富了我阅历,书,陶冶我的情操增强了我的业务素质,书,让我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
历史上科举考试中连中三元的牛人都有谁
既然西艺复兴时期的主义就人的物质性存在的当身来探的“幸福”时常会走向面,则显然,以这种方式来探讨人的“幸福”的问题是不够的。
既如此,我们必须为“幸福”寻找一个规范性或限制性原则,使“幸福”能得其正,真正起到滋养、维持、延续人的物质性存在的作用。
要解决这个问题,便牵涉到对人的基本看法。
孟子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孟子·离娄下》);亚里士多德说:人是有理性的动物。
这两种说法大同小异,即都承认人既有理性又有动物性。
但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切就人的物质性存在之当身及其才情之美来看人,则多只陷在动物性的一面,其超越动物性之所在,只表现为才智的成就。
但才智的成就,只成为人进一步追求幸福的工具。
这样一来,追求幸福,成了人的全部。
由此,人们并不能找到一个场域,作为“幸福”的对立面,以便限制、规导人们对“幸福”的追求。
这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因关注人的“幸福”的问题而又陷入肆情纵欲之泥潭的根本原因。
要克服这种流弊,必须为“幸福”寻找一个对立性的场域,以形成一个限制性、规导性的原则。
那么,这个对立性的场域在哪里呢
这依然只能在人的本质中来寻找。
就孟子和亚里士多德对人的本质的定义和解说来看,则这个对立性的场域只能在“几希”或“理性”那里,且这里所说的理性不是“知识理性”,而是“价值理性”。
也就是说,人作为追求价值的动物,对于“幸福”的问题的关注,如何利用手段追求“幸福”是第二位的,而反省自己,是否配享幸福才是第一位的。
因为前者是一个科学问题,后者是一个价值问题。
因此,前面所讲的使“幸福”得其正,便不是一个科学上的适度问题,而是一个价值的反省问题,即人对“幸福”的追求和享受是否是道德的。
通过这一价值反省,则人对“幸福”的追求与享受,借用萨特的话说,则“不但为自己的将来作了抉择,而且通过这一行为同时成了全人类作出抉择的立法者——在这样一个时刻,人是无法摆脱那种整个的和重大的责任感”。
(4)这样,便把“幸福”推到了一个对立性的场域中,在那里得到进一步的规导与限制,而这个对立性的场域,正是由人的“价值理性”(或名“实践理性”、“道德理性”)而确立的。
前面说过,任何文化要关涉到人的“幸福”问题,但幸福本身并不能构成一个自足的体系。
在西方,古希腊的斯多亚派早就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便说出了“德行便是幸福”的名言,但这实际上是取消了幸福在人生中的意义。
康德尽管也认为幸福本身并不能构成一个自足的体系,但他并不取消它在人生中的意义。
在康德看来,一个至善(the supreme good)的世界,也就是说,在一个至善的世界里,一定含有幸福和道德两种成分。
因为仅仅是幸福,对于我们的理性来说远远不是完全的善。
如果幸福不与配享幸福(worthiness to be happy),也就是道德上的善结合起来,理性则并不会赞同这样的幸福,无论人们怎样地热望它。
这样,由于康德把幸福与道德结合起来,便为幸福开显了一个对立性的场域,在那里,幸福得到了道德的规范与限制。
但必须要指出的是,康德这里所说的虽然义理周全,但毕竟是纯粹哲学家的解析,这是一种概念性的,用康德自己的话说,若我们仅从其概念而抽掉一切道德性的障碍,则一个与道德性相结合成正比的幸福的体系的智性世界(intelligible world)是可以被设想为必然的。
显然,康德也很清楚,这样的世界只是一个理念(only an idea),而我们之所以需要这个理念,乃是因为我们必须假定那个世界就是在感官世界(the world of sense)中的行为的一个后果,尽管感官世界并未向我们呈现这样一种联结,我们依然假定那个世界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未来的世界。
这样,康德把幸福和道德相联结,只是先天地解析出人类永恒福祉(general happiness)的必要条件,而这个永恒福祉的未来世界之所以可能,康德认为还必须有两个预设,即上帝(God)和来世(a future life)(5)。
。
康德的这一思路,尽管在义理上很详备,然依然是基于纯粹概念性的推导,他的系统中的上帝和来世的预设,正是这种纯粹概念性推导的有力证明。
但这种推导,有学理上的意义,却无操作的可能,因为它不是基于“人本”的,即依赖于人自身这个“本”并不能直接解决问题,也就是说,“幸福”的规导性的场域在人自身这里并没有被真正确立起来。
但尽管如此,我们仍然不能抹杀康德的理论的价值,这便是:为人类找求永恒的福祉,不使幸福发生流弊乃至走向其反面。
尽管康德只是通过先验批判找到一个先天性的原则,且因这个原则的纯形式性,使其只停留在理论的意义上。
但我们依然可以由康德的理论的价值与不足,来看 “幸福”的规导性的场域如何才能被真正确立起来
康德之所以不能把“幸福”的规导性的场域在人自身这里真正确立起来,乃是因为他始终把道德作为概念来解析,他的实践理性的三大概念——自由、上帝、来世——俱为解析时的必要假设即为明证,他始终不能反省证悟到人自身生命中质实的道德主体,由这个质实的道德主体来开启“幸福”的规导性的场域。
但儒家却一直认为,通过人格的修养工夫,即刻可觉悟到这个质实的道德主体。
这个质实的道德主体,可以是孔子的“吾欲仁,斯仁至矣”的“仁体”,也可以是孟子的“四端之心”的“心体”或“性善”之性的“性体”,亦可以是王阳明的“致良知于事事物物”的“良知”,等等。
儒家正是由这个质实的道德主体来开显出“幸福”的规导性的场域。
一方面,它不像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那样,因只反省到人的气质之性的浑全而开不出“幸福”的规导性的场域;另一方面,它不像康德的批判哲学那样,因限于纯粹概念的推导而使这个场域最终落空。
这表明,一方面它是人文主义,因为它之开显这个规导性的场域纯粹依赖于人自身,无须上帝或来世的假设;另一方面,它不是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因为它能开显出这个规导性的场域。
正因为如此,我们把儒家称为由道德的主体所开启的人文主义。
现在,我们再来看“幸福”的规导性的场域在儒家那里是如何被确立起来的。
康德把幸福和道德联系起来,是想把幸福推向一个对立性的场域以使其得到规范,但因他只是纯哲学的先验批判,因此他只是找到了一个普遍性的原则(Do that through which thou becomest worthy to be happy,即“去做那使你配享幸福的事情吧”。
)。
这条普遍性的原则只有认知和律则的意义,它并没有内在于生命、生活开启一个质实的场域,人在此场域中有切实的觉悟与感通。
于人的生命、生活中不能有切实的觉悟与感通,即表示不仁,不仁即表示生命不健(牟宗三认为:“仁有二特性:一曰觉,二曰健”(6)),生命不健即无力量去执行那条普遍性的原则,这是这条普遍性的原则在康德那里最终落空的根本原因。
要开启一个有切实觉悟与感通的场域,唯有在儒家即道德的主体所开启的人文主义始有可能,因为在这里,人的道德主体是质实的,这个质实的道德主体使人有力量去执行康德所说的那条普遍性的原则,故孔子曰:“力行近乎仁”(《中庸》),此即是说“仁”即质实的道德主体自身即含有实践的力量与可能。
而一旦人的生命中的质实的道德主体呈现,或者说一旦这个场域被确立,则不是去执行在这个场域之外的一条普遍性的原则,而是这个场域自身即是原则,这便是孟子所说的“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孟子·离娄下》),同时,在这个场域中,亦必然是“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孟子·告子上》)。
从上面的疏解中可知,“幸福”的规导性的场域的确立,完全维系于人的生命中的道德主体,一旦通过人格的修养工夫觉悟到这个道德主体,则这个场域便可确立起来。
而一旦这个场域被确立起来,即刻可见康德的理论与儒家由道德的主体所开启的人文主义在“幸福”的问题上的不同。
这种不同,就是徐复观所说的: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在“修己”和“治人”上的区别。
康德在人的“幸福”问题上追求普遍性的原则,而说:去做那使你配享幸福的事情吧。
而德行是构成我们之值得享有幸福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因此,追求幸福必须自修习德行开始,因为唯有德行使他有资格享有幸福(尽管他事实上不一定享有幸福)。
这种思想在中国文化中也有,便是:修其天爵以为人爵的前提条件。
关此,《孟子·告子上》有如下的陈述: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
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
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弃其天爵,则惑之甚者也,终亦必亡而已矣
“天爵”就是“仁义忠信”,依朱子的解释,因“德义可尊,自然之贵也”,故称。
“修其天爵”就是“乐善不倦”,依朱子,就是以“仁义忠信”“以为吾分之所当然者耳”。
故孟子所说“修其天爵”就是修习德行。
“人爵”就是“公卿大夫”,这是世间的富贵,即幸福。
显然,孟子论“天爵”与“人爵”,也就是在论述“德行”与“幸福”的关系。
切就这种关系而言,孟子认为应该是“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而不应该是“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此所谓“有意为善,为善亦私”也),更不是“既得人爵,而弃其天爵”。
所谓“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乃是说:尽“吾分之所当然者”,则人爵“盖不待求之而自至也”。
也就是说,就理想状态而言(孟子以“古之人”、“今之人”对举,并非历史事实,而是以“古之人”寄寓理想也),“修天爵”应为“人爵”的前提条件。
这就同康德所说的德行构成了我们配享幸福的必不可少的条件的讲法一致了。
康德由此而说出“去做那使你配享幸福的事情吧”的普遍原则,儒家亦由此而说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的普遍原则。
所谓“修身”,就是通过人格修养的工夫,让道德主体在生命中动转甚至作主,使整个生命呈现出一个仁者的境界。
这个仁者的境界,才构成了“幸福”的一个质实的场域,人在此才有切实的内在于生命和生活的觉悟、感通,给“幸福”以限制和规导。
何以能如此呢
这同康德的理论相比即可明白。
康德对“幸福”的规导和限制只是基于一条普遍性的原则——“去做那使你配享幸福的事情吧”。
就此一原则,我们可问:我做什么事情才使我配享幸福呢
这种价值上的关连靠什么来肯认呢
康德可回答曰:依人的道德理性。
但在康德那里,这个原则之被遵循,还须要有上帝存在和来世这两个条件。
这样一来,则这个由人的道德理性所确立的内在原则,因与上帝和来世挂搭起来,便不可避免其外在性,成为了悬拟于人的主体之外的上帝的命令。
但其实,我们行事,当下即是。
何以必想到上帝是否存在耶
亦何以必想到是否有来世耶
康德不能见人的生命中的道德主体的纯正与庄严,而涉至那么远,如此“支离”,真是煞费苦心。
若能打开道德的主体,则当下即是,良知的决断即是生命当下的行为,亦即是幸福的规导原则,何等“简易”。
但这个原则(实不能说是原则)并不是悬拟在人的主体之外的一条抽象性、形式性的原则(如康德者然),而是良知的自然发露,是心的不容己,情的不自禁(即孟子所谓“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也。
”)。
这不是外在的智性的认取,而是内在的德性的证悟,不是对外在的原则的服从,而是求自家仁心之安。
这里面有切实的觉悟与感通,这是质实的,而不是形式的。
形式性的原则只追求普遍性,如康德就是要把那普遍性的原则给解析出来。
而对于质实的感通而言,原则的普遍性不是最重要的,求仁心之“安”(“安”即是夫子答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时,所说的“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之“安”也)才是最重要的。
正因为如此,则在“幸福”的问题上,与康德的普遍性原则不同,儒家有“修己”和“治人”上的区别。
用徐复观的话说,即是,在“修己”方面是“教先于养”,在“治人”方面是“养先于教”。
他说:孔孟乃至先秦儒家,在修己方面所提出的标准,亦即在学术上所立的标准,和在治人方面所提出的标准,亦即在政治上所立的标准,显然是不同的。
修己的学术上的标准,总是将自然生命不断底向德性上提,决不在自然生命上立足,决不在自然生命上安设价值。
治人的政治上的标准,当然还是承认德性的标准;但这只是居于第二的地位,而必以人民的自然生命的要求居于第一的地位。
治人的政治上的价值,首先是安设在人民的自然生命的要求之上;其它价值必附丽于此一价值而始有其价值。
(7)按照徐复观的理解,则儒家对于“幸福”的态度,一方面,不能以治人的标准来律己,若然,则是误认为儒家精神乃停顿在自然生命之上,而将其修己以“立人极”的工夫完全抹杀掉;另一方面,亦不能以修己之标准治人,果尔,势必酿成“以理杀人”的悲剧。
儒家之所以能有这种思想,这决不是基于逻辑的分析或先验的批判,而是在道德主体的质实的场域中觉悟,即仁心之不容已而始可能的。
这才是人文主义的切义。
为了进一步表明中国的人文主义在“幸福”的问题上的这种胜义,再列举下面二段文字:子适卫,冉有仆。
子曰:“庶矣哉
”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
”曰:“富之”。
曰:“既富矣,又何加焉
”曰:“教之”。
(《论语·子路》)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
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
此唯救死而恐不瞻,奚暇治礼义哉
(《孟子·梁惠王上》)把这种胜义说得更为清楚明白的,是下面的一段话:是故内治反理以正身,据礼以劝福。
外治推恩以广施,宽制以容众。
孔子谓冉子曰:治民者先富之而后加教。
语樊迟曰:治身者先难而后获。
以此之谓治身之与治民,所先后者不同焉矣。
《诗》云:饮之食之,教之诲之。
先饮食而后教诲,谓治人也。
又曰:坎坎伐辐,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先其事,后其食,谓治身也。
《春秋》刺上之过,而矜下之苦。
……求诸己谓之厚,求诸人谓之薄。
自责以备谓之明,责人以备谓之惑。
是故以自治之节治人,是居上不宽也。
以治人之度自治,是为礼不敬也(《春秋繁露·卷第八·仁义法第二十九》)。
由上所述,在“幸福”的问题上,儒家由道德的主体所开启的人文主义,既不同于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着眼于自然生命本身,其结果是对物欲的满足与欣赏。
亦不同于康德的批判哲学,着眼于纯粹理性的先验批判,其结果只发现抽象的规导原则。
前者因未为幸福确立一个对立的场域,故幸福在那里会发生流弊;后者因只为幸福确立了一个形式性的场域(抽象性的原则其实不能叫做场域,这里用“形式性的场域”正表示它是——依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没有质料塞入的空概念),故人的现实生活却并不能因此而得到规导。
唯有在由内在于人的生命的道德主体所开显的场域中,如前所述,幸福才会切实地调适而上遂。
一方面,它不会流为纯粹的物欲;另一方面,它不会沦为“以理杀人”。
总之,唯有在儒家由道德的主体所开启的人文主义中,幸福才会尽其性,使仁者心安也。
这是儒家对幸福问题的解决的最后结论。
什么时候出生的天蝎座最厉害
1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