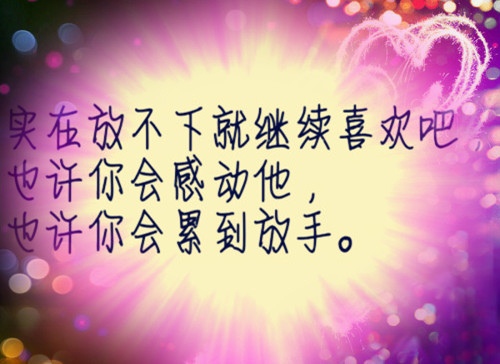辨析:我国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因此国家可以随意征税吗
这句话是错误的
国家当然不可以随意征税
因为税收有固定性,已经确定的税种和税率、每年征税的时间和税额,不经过税法的修改,不能随意征税
一般税率在一定环境下是相对固定的。
税收与其他形式的财政收入相比,具有强制性、无偿性和固定性三项基本特征。
税收的强制性,是指税收参与社会产品的分配是依据国家的政治权力,具体表现在税收是以国家法律的形式规定的,税法作为国家法律的组成部分,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必须遵守。
税收的无偿性,是指在具体征税过程中,国家征税后税款即为国家所有,不再直接归还给纳税人。
税收的无偿性是相对的,从财政活动的整体来看,税收最终通过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等方式用之于纳税人,体现了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本质。
就某一具体的纳税人来说,其所缴纳的税款与其消费的公共产品中的价格并不一定是相等的。
税收决策应当通过公共选择加以进行,这是现代社会的鲜明特征之一。
说白了,即公众作为纳税人掏了钱,就应当由公众(通过一定的程序和公共决策机构)说了算——诚如发达社会公共的钱袋子掌握在国会而非政府手中。
公众通过其代议机构,决定究竟花多少钱用来购买多少由政府提供的公共品。
由此,决定了私人品与公共品的配置以及相应税种和税率。
所以,应当是公众的公共选择而非政府的决策可以体现税收合理的配置功能。
只有税收特定的公共选择完成后,才谈得上政府加以执行的问题。
这一程序是不容颠倒过来的。
中国正在大步迈向现代化,就更应当努力靠近这种程序,而且宪法不也规定了人民代表大会为最高权力机构了吗
假如某个政府的领导人面对一个公共决策的最高权力机关说:“我们终于取消了某某税种”,这种做法正常不正常,对不对
从程序上讲肯定是不对的。
正当的程序是,首先由最高公共决策机构做出并通过取消什么税的决议或议案,然后让政府去执行。
如果关于税率和税收用途的决策没有体现公共选择的意愿,其结果则是令人难堪和令人沮丧的。
记得樊纲在2000年某期《经济研究》的发文中,针对当时政府以大量财政资金用来剥离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透析)和为其提供资本金(输血),曾感言:总要有人为此“埋单”。
当时,他并未指出由谁并以何种方式“埋单”。
后来,我渐渐想明白了——当然是由公众付费的。
不过,付费的方式显得较为奇特。
打个比方:公众作为纳税人,总共依法交纳了2万亿的税,原本可以消费到等额的公共品。
由于抢救国有银行这些“危重病人”花费了1万亿元,那么公众只能获得1万亿真正需要的公共品了。
原来,公众是以在公共品的购买过程中花了“冤枉钱”的方式而“埋单”的。
那么,这桩“买卖”公众到底是否愿意呢
也许这样的例子实在太多了,才会出现一方面税收增加很快而另一方面百姓抱怨用于教育、医疗等公共支出太少的“悖论”。
近来,社会大众对于教育和医疗等领域的诟病,难道不正说明了对于政府强卖公共品(缺斤少量、供非所求)的不满吗
所以,税收及其用途的决策不是通过良好的民主程序下的公共选择,吃亏的必然是广大的人民群众。
从某种意义上说,将税收用于抢救大型国有银行,算是万幸了,因为绝大部分百姓从嘴里抠出的钱都存在这些银行里,一旦这些银行倒闭了,百姓就会血本无归。
如果税收让各级政府用来追求GDP政绩或搞形象工程,那么百姓可真成了名副其实的“冤大头”。
GDP这玩意儿太能哄人,说的极端些——纯粹挖个坑,如果由政府开支,就会造出GDP,说不定数额比政府开支还要大(由于乘数效应);再把坑填上,又将增加GDP。
一来一回,什么效用也没有,GDP却增长了一大截。
这倒解开了存留在我心中许久的一个谜团:为什么官方公布的经济增长率这么高,中国还是在国际竞争的长跑中晃晃悠悠,似乎像韩国这样的“小个儿”也会不经意地流露出某种优越感。
若是从前,又不知会道出几遍“亏对列祖列宗”来
看来,税收及其用途真的需要公共选择了。
那么,可否请经济学家替公众算一算究竟应当上多少税、让政府提供多少公共品呢
很无奈,经济学家充其量知道些诸如最优解的条件等等,尽管有些末流的所谓“大家”总喜欢当众摆弄手中的算盘。
其实,适当的税率和公共品的品种与数量,不是计算出来的,而是通过良好的公共选择程序(或民主程序)在不同利益集团之间博弈出来的。
所幸的是,在发达社会,公共选择的结果至少不会长期偏离公众的意愿,因为合法程序下政党的轮替和政府的更迭将有助于保证这一点。
除配置功能外,税收还具有国民收入再分配和作为宏观调控工具的功能。
这些功能的发挥,仍应当通过公共选择。
就拿税收的国民收入再分配功能来说,比如有一排路灯,你我都享受到了,但是我们花的钱是不一样的,由于我比你富,根据累进的所得税制,所以我多花了钱,这就是物品配置当中国民收入再分配的效应。
而转移支付更能体现国民收入再分配。
那么什么程度的国民收入再分配是合适的呢
假如在一个静态的个人偏好无差异的社会,且存在货币的边际效用递减。
在这种情形下,如果我们遵循的不是帕累托标准而是补偿原则,达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税收安排则是: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将所有国民的可支配收入实现均等化——绝对的均贫富。
道理很简单,富人失去一元所减少的效用要比穷人得到一元钱所增加的效用要低一些。
那么,为什么人们通常不选择这样的一种再分配呢
从动态来看,这一安排是不合理的,因为人们将会失去动力而不会努力去赚钱,社会也就无法进步了。
所以,合适的国民收入再分配势必要在现在与将来的社会福利之间进行权衡,以实现动态的社会福利最大化。
显然,由政府决策而非公共选择来追求动态的社会福利最大化,无异于缘木求鱼。
政府可能会迫于眼前的形势,放大部分民众的诉求,施出某种“小仁政”来。
由于目前的舆论造出来了一种仇富心理、一种原罪说,就是穷人要求对富人进行无限制的国民收入再分配。
对此,尤其一个国家在发展和转型初期是应该谨慎对待的,如果决策不当,等于是“杀鸡取卵”。
当然,要求富人承担相对较多的社会责任,这是无可厚非的,但绝对不能造成一种原罪说,把富人的收入增量全部均分,最后的结果只能是对所有的草根百姓不利。
联想到近期出台的税收政策,颇感不安。
即使不对税收政策的程序合法性加以探究,我也很难弄懂——为什么全国只有年应税收入超过12万元的纳税人必须自行申报。
如果要进行以个人所得税自行申报为内容的税制改革,那么试点应当选择某一地区或某一城市;如果想要公民牢固确立依法纳税的观念,最好先由政府官员做起。
看来,从富人那里进行试验,总能捞得些油水,试验所带来的净收益将会更大。
但愿这一举措不是原罪说和社会仇富心理的一种折射。
税收特征中其核心是什么
公共选择:税收的核心含义\ 税收决策应当通过公共选择加以进行,这是现代社会的鲜明特征之一。
说白了,即公众作为纳税人掏了钱,就应当由公众(通过一定的程序和公共决策机构)说了算——诚如发达社会公共的钱袋子掌握在国会而非政府手中。
公众通过其代议机构,决定究竟花多少钱用来购买多少由政府提供的公共品。
由此,决定了私人品与公共品的配置以及相应税种和税率。
所以,应当是公众的公共选择而非政府的决策可以体现税收合理的配置功能。
\ 只有税收特定的公共选择完成后,才谈得上政府加以执行的问题。
这一程序是不容颠倒过来的。
中国正在大步迈向现代化,就更应当努力靠近这种程序,而且宪法不也规定了人民代表大会为最高权力机构了吗
假如某个政府的领导人面对一个公共决策的最高权力机关说:“我们终于取消了某某税种”,这种做法正常不正常,对不对
从程序上讲肯定是不对的。
正当的程序是,首先由最高公共决策机构做出并通过取消什么税的决议或议案,然后让政府去执行。
\ 如果关于税率和税收用途的决策没有体现公共选择的意愿,其结果则是令人难堪和令人沮丧的。
记得樊纲在2000年某期《经济研究》的发文中,针对当时政府以大量财政资金用来剥离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透析)和为其提供资本金(输血),曾感言:总要有人为此“埋单”。
当时,他并未指出由谁并以何种方式“埋单”。
后来,我渐渐想明白了——当然是由公众付费的。
不过,付费的方式显得较为奇特。
打个比方:公众作为纳税人,总共依法交纳了2万亿的税,原本可以消费到等额的公共品。
由于抢救国有银行这些“危重病人”花费了1万亿元,那么公众只能获得1万亿真正需要的公共品了。
原来,公众是以在公共品的购买过程中花了“冤枉钱”的方式而“埋单”的。
那么,这桩“买卖”公众到底是否愿意呢
\ 也许这样的例子实在太多了,才会出现一方面税收增加很快而另一方面百姓抱怨用于教育、医疗等公共支出太少的“悖论”。
近来,社会大众对于教育和医疗等领域的诟病,难道不正说明了对于政府强卖公共品(缺斤少量、供非所求)的不满吗
所以,税收及其用途的决策不是通过良好的民主程序下的公共选择,吃亏的必然是广大的人民群众。
从某种意义上说,将税收用于抢救大型国有银行,算是万幸了,因为绝大部分百姓从嘴里抠出的钱都存在这些银行里,一旦这些银行倒闭了,百姓就会血本无归。
如果税收让各级政府用来追求GDP政绩或搞形象工程,那么百姓可真成了名副其实的“冤大头”。
GDP这玩意儿太能哄人,说的极端些——纯粹挖个坑,如果由政府开支,就会造出GDP,说不定数额比政府开支还要大(由于乘数效应);再把坑填上,又将增加GDP。
一来一回,什么效用也没有,GDP却增长了一大截。
这倒解开了存留在我心中许久的一个谜团:为什么官方公布的经济增长率这么高,中国还是在国际竞争的长跑中晃晃悠悠,似乎像韩国这样的“小个儿”也会不经意地流露出某种优越感。
若是从前,又不知会道出几遍“亏对列祖列宗”来
\ 看来,税收及其用途真的需要公共选择了。
那么,可否请经济学家替公众算一算究竟应当上多少税、让政府提供多少公共品呢
很无奈,经济学家充其量知道些诸如最优解的条件等等,尽管有些末流的所谓“大家”总喜欢当众摆弄手中的算盘。
其实,适当的税率和公共品的品种与数量,不是计算出来的,而是通过良好的公共选择程序(或民主程序)在不同利益集团之间博弈出来的。
所幸的是,在发达社会,公共选择的结果至少不会长期偏离公众的意愿,因为合法程序下政党的轮替和政府的更迭将有助于保证这一点。
\ 除配置功能外,税收还具有国民收入再分配和作为宏观调控工具的功能。
这些功能的发挥,仍应当通过公共选择。
就拿税收的国民收入再分配功能来说,比如有一排路灯,你我都享受到了,但是我们花的钱是不一样的,由于我比你富,根据累进的所得税制,所以我多花了钱,这就是物品配置当中国民收入再分配的效应。
而转移支付更能体现国民收入再分配。
那么什么程度的国民收入再分配是合适的呢
\ 假如在一个静态的个人偏好无差异的社会,且存在货币的边际效用递减。
在这种情形下,如果我们遵循的不是帕累托标准而是补偿原则,达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税收安排则是: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将所有国民的可支配收入实现均等化——绝对的均贫富。
道理很简单,富人失去一元所减少的效用要比穷人得到一元钱所增加的效用要低一些。
那么,为什么人们通常不选择这样的一种再分配呢
从动态来看,这一安排是不合理的,因为人们将会失去动力而不会努力去赚钱,社会也就无法进步了。
所以,合适的国民收入再分配势必要在现在与将来的社会福利之间进行权衡,以实现动态的社会福利最大化。
\ 显然,由政府决策而非公共选择来追求动态的社会福利最大化,无异于缘木求鱼。
政府可能会迫于眼前的形势,放大部分民众的诉求,施出某种“小仁政”来。
由于目前的舆论造出来了一种仇富心理、一种原罪说,就是穷人要求对富人进行无限制的国民收入再分配。
对此,尤其一个国家在发展和转型初期是应该谨慎对待的,如果决策不当,等于是“杀鸡取卵”。
当然,要求富人承担相对较多的社会责任,这是无可厚非的,但绝对不能造成一种原罪说,把富人的收入增量全部均分,最后的结果只能是对所有的草根百姓不利。
\ 联想到近期出台的税收政策,颇感不安。
即使不对税收政策的程序合法性加以探究,我也很难弄懂——为什么全国只有年应税收入超过12万元的纳税人必须自行申报。
如果要进行以个人所得税自行申报为内容的税制改革,那么试点应当选择某一地区或某一城市;如果想要公民牢固确立依法纳税的观念,最好先由政府官员做起。
看来,从富人那里进行试验,总能捞得些油水,试验所带来的净收益将会更大。
但愿这一举措不是原罪说和社会仇富心理的一种折射。
余华写的《活着》具体内容是什么啊
“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
总书记在很早之前就提出了“弱鸟可望先飞,至贫可能先富”的理念,动员鼓舞群众奋发图强,发展合力的理念。
发展致富是每个老百姓的梦想,奋斗的目标,没有人愿意天生就贫穷,奋斗之心人皆有之。
但是有些人恰相反,随着国家的政策越来越好,民生保障工作越做越完善,却出现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靠政策救济”的“懒汉”。
在某些贫困地区,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戴上贫困帽,实惠少不了”。
这种精神上的贫困,比物质上的贫困更加可怕,对“空得实惠”的依赖性越发严重,就会出现越扶贫却越想保贫的现象,甚至有些地方出现了主动“返贫”的现象,宁当贫困县,不摘“穷帽子”,“苦干不如苦熬”不积极发展农产业,“等着别人送小康”等等这种“贫困思想”。
扶贫,首先要让精神富足。
幸福不会从天而降,好日子是干出来的。
不能有扶而不起、帮而不富、助而不强的思想态度,越是贫穷,就越要有穷则思变,穷则思勤的奋斗精神。
不能让贫瘠思想成为脱贫攻坚路上的绊脚石、拦路虎。
只有引导贫困群众树立“宁愿苦干,不愿苦熬”的观念,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才能真正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实现脱贫致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