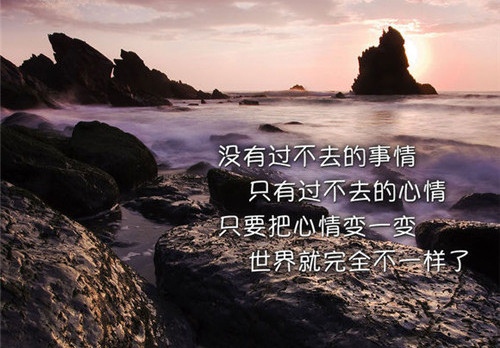《诗经》是中国文化宝库中一颗耀眼的明珠,其价值不仅仅在于优美的语言、动人的描述以及质朴自然的表达方式,更在于它是当时社会生活的一部百科全书。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内容极为丰富。其中婚恋诗占了三分之一,是《诗经》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正如郑振铎先生所述:“在全部《诗经》中,恋歌可说是最晶莹的圆珠圭璧……他们的光辉竟照得全部的《诗经》都金碧辉煌,光彩眩目起来”。[1](P45)这些婚姻爱情诗为我们描绘了关于婚恋的民情风俗图。其中,《卫风·氓》是非常著名的一篇。
围绕着这首诗,学者们大都专注于对男女主人公人物形象的研究,①而对诗中表现出来的婚恋习俗的研究却不多。其实,这首诗包含着这方面的丰富内容。它通过一位弃妇对她和氓恋爱、结婚、被弃的过程的自述,不但深刻反映了古代妇女在婚姻问题上受到的压迫和伤害,而且对当时的婚恋习俗也有深刻的反映。因此,它对研究春秋时期的婚姻生活有着极大的参考价值。
一、自由恋爱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人们的婚姻受到极大地限制。在封建社会的大前提下,儒家伦理思想支配了一切,自由恋爱成为一种奢望。然而,在儒家伦理思想未成为正统的春秋时期,下层人民对婚姻仍有一定的自主权,《氓》中所描述的情景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氓》中的男女主人公均为下层人民,两人青梅竹马、两小无猜。以后,双方关系进一步发展,男主人公“抱布贸丝”、“来即我谋”,向女主人公求婚,最后女主人公私自答应了这门婚事,并“秋以为期”。约定婚期后,女主人公又恋恋不舍,送了心上人许久。婚期将至,女主人公盼望男主人公早点来迎娶她,以至于“乘彼垝垣,以望复关。不见复关,泣涕涟涟。既见复关,载笑载言”。男女双方并肩行走,谈笑风生,这样的情景在以后的封建社会无法得见,从中便可窥见春秋时期下层人民在婚姻行为中的自由。这是诗的前半部分,男女双方从相识、相交直至步入婚姻,未受到太大的阻碍。可见在春秋时期,下层人民在婚恋方面确有不小的自由。
《诗经》中随处可见这样的画面,《邺风·静女》、《郑风·野有蔓草》、《陈风·东门之枌》、《郑风·溱洧》等诗篇也反映了当时下层青年男女自由恋爱的情景。这种事情在当今社会当然非常自然,但在两千多年前,却令人惊叹不已。
为什么春秋时期下层人民的婚姻可以有这样自由选择的空间?这需要从当时的具体环境来分析。当时,人口自然增长率很低,再加上生产力比较落后,因此,必须大量增加劳动力。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政府想方设法促使青年男女结合,甚至以行政命令进行干涉,对再婚行为也不做过多限制。而下层人民是繁衍人口的主要群体,因此下层人民比上层贵族拥有更多的婚姻自由。
二、媒妁之言
春秋时期的婚姻为聘婚制,践行起来便需要“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媒人出现的时间很早,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周代,这类人就已出现。媒人在当时的婚嫁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因而有“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2](P51)的说法。这一点在《氓》中有着充分的反映。
《氓》中的男女主人公虽然两情相悦,但苦于没有“良媒”,因此不得不“将子无怒,秋以为期”。实际上,周代就已设置专门官职管理百姓的婚姻大事。《周礼·地官》记载:“媒氏,掌万民之判。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书年月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凡娶判妻入子者,皆书之。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若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司男女之无夫家者而会之。” [3](P360-P364)从中便可看出媒人在当时婚姻嫁娶中的作用与地位。在春秋时期,没有媒人的证明,这场婚姻便是非法的,不仅不受到保护,还为社会所不容。这正与“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 [4](P143)相符合。
《氓》中,这对青年男女虽然早已私下定情,但女主人公仍然暗示男主人公找位媒人来提亲。不仅是《氓》,《诗经》中的许多其它诗篇也反映了媒人的重要性。在《伐柯》的描述中,娶妻必须通过媒人,而这就如同砍取斧柄必须使用斧头一样。《齐风·南山》记载:“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也反映了媒人的地位与作用。当时,没有媒人,婚姻便难以成功,并且会遭到人们的嘲讽与社会的指责。
三、婚姻六礼
婚姻对周人而言是一件大事,因而对婚姻礼仪极为讲究。即便是在婚姻中拥有较多自由的下层人民对婚姻礼仪也很重视。“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2](P1618) “论其男女之身,谓之嫁娶,指其好合之际,谓之婚姻,嫁娶、婚姻,其事是一” [5](P308)这两段话形象地表达出周人对婚姻的重视。
周代的婚姻礼仪集中体现为聘婚礼。据《仪礼·士昏礼》所载,聘婚礼仪分为纳彩、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六个步骤。“六礼是婚礼的主体,把纳彩、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实践,婚礼才算是严肃的、正式的、合法的。” [6]纳彩,即男女双方进行议婚。问名,即请媒人询问女方情况。纳吉,即问名归来后进行占卜以定吉凶。若男方的卜兆为吉兆,便请媒人前去通知女方,决定正式缔结婚姻。若男方的卜兆为凶兆,那么此门婚事便不能进行。纳征,也称为纳成,即男方将财物聘礼送往女方家中。这是婚姻成立的标志,因而这项礼仪在婚姻礼仪中较为隆重。请期,即男方择定吉日婚期并告知女方。亲迎,俗称为迎亲,即男方前往女方家迎娶女方。亲迎是在黄昏中进行的,这是婚姻礼仪中最为重要的程序。同时,亲迎的仪式也是相当重要的,不能有丝毫马虎。以上即为古代聘婚制的礼仪,极为繁琐。当时,婚礼是被人们看作以血缘伦理道德为出发点的整个礼制的基石,因而婚礼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这种婚姻礼制在《氓》中有着较为集中的体现。诗中第一章有“匪我愆期,子无良媒”的句子,意思就是女主人公提醒男主人公赶快找个好媒人来自己家提亲,这便合了纳彩之礼。第二章写道“尔卜尔噬,体无疚言”,暗合婚姻六礼中的问名、纳吉之礼。诗中虽然只提到纳吉之礼,但问名与纳吉之礼密不可分,如若进行纳吉之礼,则问名之礼必已先行之。第一章最后一句说道:“将子无怒,秋以为期”,合婚姻六礼中的请期之礼。第二章最后一句又说道:“以尔车来,以我贿迁”,这便合了婚姻六礼中的纳征与亲迎之礼。在《诗经》众多婚姻诗中,《氓》应该是较为全面反映婚姻六礼的诗篇,这为后人了解婚姻六礼提供了极好的素材。
四、婚期
春秋时期,婚期也有规定。《氓》中第一章最后一句写道:“将子无怒,秋以为期”,明确指出了以秋天作为婚期。这绝不是信口开河,而是当时婚俗的一种体现。春秋时代婚嫁多在秋冬,这不仅在《诗经》中有所体现,后世的文献也有记载,“霜降逆女,冰泮杀内” [7](P496)就是极好的证明。
春秋时期,人们在秋冬季节嫁女迎娶无论从思想上还是从物质条件上都与当时的社会情况相吻合。董仲舒云:“天之道,向秋冬而阴来,向春夏而阴去,是故古之人霜降而迎女,冰泮而杀内,与阴俱进,与阳俱远也”[8](P450-P451)这是以阴阳观念来解释婚嫁之时。而从农业方面来解释春秋时期人们在秋冬季节进行婚嫁之事,则较为合理。众所周知,春秋处于生产大变革时期,人们已处于农业社会,因此,婚姻嫁娶等社会活动必然会受到农业行为的影响。在农业社会里,只有秋冬之季才适宜于嫁娶。在当时的社会中,人们过着春散于野而秋聚一处的生活。春天无疑是一个异常繁忙的季节,“三之日于耜,四之日举趾,同我妇子,馌彼男亩,田畯至喜。”“十月蟋蟀入我床下。穹窒熏鼠,塞向瑾户。嗟我妇子,曰为改岁,入此室处”,[9](P408)《豳风·七月》的这几句话形象的反映了当时人们在春季散居于各地,秋季迁往城邑内居住的情景。人们由于农耕的缘故,春耕之时,便全家搬往农田附近居住,以利于一年的耕作,这种散居的情况以及忙碌的生活使人们没有足够的时间、人力、物力来进行婚嫁这种耗费精力以及财力的活动。只有到秋天收获作物,人们迁入城邑中居住以后,才有大量的空闲时间,也由于收获了粮食,形成了一定的物质基础,才有可能进行这种耗费时间与财力的活动。由此看来,在秋冬农闲群居时进行婚嫁之事是与当时的社会条件相吻合的。
当然,《诗经》中还有诗篇记载婚期为春季。但这些诗篇要么反映的是周朝早期的情况,要么反映的是王公贵族的情况。从周初到春秋时期已过了几百年,农业不断发展,在春季这个农忙季节进行婚嫁有许多不便之处,因此,婚礼也就自然而然的放在秋冬之季举行。同时,由于贵族不从事农耕活动,因而婚期仍然与几百年前的周初相同,几乎没有变化。而绝大多数的下层人民由于不离农耕,与之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因而婚嫁季节从以前的春天变为秋冬之季,这是社会的主流方向。这便能解释为何《诗经》中的婚期描述有矛盾之处。
五、结语
《氓》是《诗经》众多婚恋诗中的一首,是反映社会生活与民风的典范。它以简练的语言描述了一对青年男女相恋、结合直至婚变的事件。从两人交往过程的描述中可以看到春秋时期的许多婚恋习俗,如“媒妁之言”、“婚姻六礼”、婚期以及儒家思想成为正统之前下层人民的自由婚恋。只要稍加留意,便能从中大概了解当时的婚姻状况。
《诗经・氓》是一篇典型的弃妇诗,揭示了周代社会男尊女卑的不合理制度,反映了妇女地位的卑微。
《诗经・卫风・氓》是一首叙事成分浓重的弃妇诗,运用了回忆倒叙的手法描述这人间悲剧,亦是一位劳动妇女在婚姻问题上被欺骗遗弃后所唱的怨歌。诗歌讲述了最初敦厚老实的男子殷勤地求婚,两人感情美好而甜蜜;婚后,女子“夙兴夜寐”,对丈夫一片赤诚,为家庭任劳任怨,辛勤劳作;而更多地却道出了自己年老色衰,如同桑叶枯黄飘零,并遭到丈夫遗弃的苦痛。在她回顾今昔不同的生活遭遇,哭诉了被弃的悲楚后,最终意识到自己成了不合理的婚姻制度的牺牲品,而对她进行欺骗、摧残的正是先前那“言笑晏晏,信誓旦旦”的伪君子,最终怒不可遏地喊出了“反是不思,亦已焉哉!”,喊出了满腔怨忿,愤然决定和变化无常的丈夫一刀两断,彻底决裂。
《风》中的爱情诗,作为风土之音,里巷歌谣,多是劳动人民的口头创作,把爱情生活和社会生活自然地、天衣无缝地结合在一起,表现了人们纯朴、真挚的爱情理念以及对歧视、遗弃妇女现象的批判。而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学作品,它们的内容和形式无疑和那个时代的政治、文化相联系。正因如此,我们可以通过诗歌中的情节描写,推想出周代社会中的某些习俗。《氓》作为大家熟知的弃妇诗,情节丰富,涵盖了女子从订婚、结婚到受辱、遗弃的全过程,颇具代表性,为我们了解周代先民的婚姻习俗和制度等内容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
一、“仲春会男女”与朴素自由的恋爱风尚
在周代,男女自由恋爱风气尚开,受到礼教的钳制并没有封建制度确立后的那样明显。这时的婚姻形态,包括正规的聘娶婚和非正规的野和。聘娶婚是婚姻的正宗,通行于上层社会,讲究礼仪规范,而野和即是这种对偶婚的残存。不同的等级层次的社会成员,其婚姻程序往往各有差异。统治阶级为了繁衍人口,扩大生产力,鼓励青年男女的结合,这就使得广大平民阶层的恋爱择偶处在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中,具有追求恋爱的自主权利。
《氓》中写到“总角之宴”,可见女子与氓从小亲梅竹马,对氓亦是“不见复关,泣涕涟涟。”女子对氓一片深情,朝思暮想。氓对女子也是“信誓旦旦”,感情非常深厚。从开篇首句“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可以看出,男子主动向女子示爱,二人的结合也有一定的感情基础,并非宗族家长的意愿,也反映出周代先民的情爱自由可见一斑。
《周礼・媒氏》记载:“仲春之月,会令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若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司男女之无夫家者而会之。凡嫁子娶妻,入币纯帛,无过五两。”据此,我们可以看出统治阶级给予了人们恋爱一定的自由空间,对在仲春三月的非正规婚姻不加干涉,并对嫁娶聘礼作了一定限制,规定“入币纯帛,无过五两”,亦即不超过一束帛,这样最大限度地鼓励人们自由婚配。《诗经》中,如《郑风・野有蔓草》《郑风・溱洧》等篇,对“仲春会男女”的婚恋习俗也有着充分的反映,弥漫着劳动人民对朴素自由的恋爱风尚的歌颂。
二、“子无良媒”与周代婚姻的“匪媒不得”
《氓》中女子解释道“匪我愆期,子无良媒”,也从侧面反映出媒人在周代婚姻的重要性,亦为其婚姻悲剧埋下伏笔。《周礼・媒氏》中记载:“媒氏掌万民之判”,郑《注》曰:“判,半也。得藕为合,主合其半,成夫妇也。”《地官・司徒》中专设媒氏一职,“媒氏,下士二人。史二人,徒十人。”可见,周代正规的婚姻仪式的主持者都是由官方机构设置,媒人也已普遍介入到人们的婚姻缔结中。《豳风・伐柯》有言“娶妻如何,匪媒不得。”从诗句中可以看出,媒人是婚姻过程中社会化了的规范,是一个重要的牵线人,亦是宗族社会中家长对子女婚事干涉的产品。《礼记・曲礼上》中便谈到了媒人这一专职的重要作用,“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币不交不亲,故日月以告君,斋戎以告鬼神,为酒食以召乡党僚友,以厚其别也。”由媒人牵连男女,婚礼下达父母,上告祖先,操办酒席以告相邻,强调男女之别。因此,我们知道媒人是周代先民进行正规婚姻流程的前提。
《氓》中女子期待有媒人以进行正规的婚姻步骤,无奈男子未聘良媒,最后只得安慰男子,并许诺“秋以为期”。这也让人对男子的品行引发猜测,为何“子无良媒”?《氓》中男女婚时已过仲春,无媒而自行成婚,女子缺乏对男子的全面了解,并将自己置于违背礼法的不利境地,最后也只得留下深深的悔恨。
我国古代婚姻注重“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说文》中,“媒,谋也,从合二姓;妁,酌也,斟酌二性也。”媒人作为官方特设职位,是古代聘娶婚不可缺少的角色,同时也起着勾连嫁娶两家的重要作用。美满的婚姻,应有媒人的见证和礼法的约束,即使两情相悦,也应按礼法行事。反之,如果男女私定终身,就会遭到家庭和社会的耻笑,《孟子・滕文公下》有言:“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这也说明周代宗法制社会对婚姻的枷锁正在形成,强调宗族社会对婚姻本身的期许。
三、“尔卜尔筮,体无咎言”与周代婚姻的“六礼”
前面说道,媒人是规范化的婚姻的重要前提,因为有了媒人才得进行合乎礼法的“六礼”。男以娶之程序而娶,女以嫁之程序而嫁,男子娶妇当向女方依礼聘娶。正所谓“六礼备,谓之娶;六礼不备,谓之奔。”这也是正式缔结婚姻的主要方式,亦是《氓》中女子所期望的婚礼,不违礼法,获得社会的认可。
《仪礼・士昏礼》记载了当时“士”阶层所通行的婚俗礼仪环节,即“六礼”:⑴纳彩,待女家许亲后,男方聘媒人到女家,持雁行采择之礼;⑵问名,媒人持雁作礼问女子姓名、生辰,以便占卜请示吉凶;⑶纳吉,男方主人在祢庙中对女名进行占卜,得吉兆,再遣媒人到女方告吉;⑷纳征,即男方遣人向女方送聘礼;⑸请期,即请女家主人确定婚期,以表谦虚;⑹亲迎,即结婚当日男子迎娶女子回家。 这六个程序完成后,婚礼完成,男女便确定了正式的婚姻关系。“六礼”中,除纳征用聘礼外,其余五礼用雁,雁作为随阳之鸟,随时而南北,不失时节。飞而成行,长幼有序。意在提醒夫妻在家庭生活中的行为观念,强调守时序、不逾越,也体现先民对新婚夫妻的良好祝愿
《氓》中男子借贸丝亲自行采择之礼,所持布帛也并非雁,并没有遵循礼法。“尔卜尔筮,体无咎言”便包含了“问名”和“纳吉”,亦是男子自行完成,并不完全符合当时的习俗,乃是私订婚姻。明人朱善《毛诗本义・诗解颐》记载:“责之以良媒,是欲谋之人也,而不知人之不吾与也;要之以卜筮,是欲询之神也,而不知神之不吾告也;及其见弃而归兄弟,是欲依其亲也,而不知亲之丑吾行而不见恤也。亦将如之何哉?女之苟合者,色衰而爱弛;士之苟合者,利尽而交绝。合之不可以苟也。”《氓》中男女有违礼俗,这也从某种程度上酿成了婚后的悲剧。
四、“反是不思,亦已焉哉”与周代婚姻的“出妻”制度
《氓》中女子婚后三年日夜操劳,而丈夫却“二三其德”,面对爱情始乱终弃。她对丈夫的薄情表现出深切的悔恨,发出“女之耽兮,不可说也”的叹息。并用桑葚的润泽来比喻自己的年轻美貌,爱情的甜美,用斑鸠鸟贪吃桑葚,来告诫女子切勿迷恋男女之情。经历了最初的`幸福到急切的完婚,最终,女子在夫家辛勤劳作却被抛弃,只得独自渡过淇水而归。这一令人痛心的弃妇形象,也让我们看到了周代女性的地位卑微,面对丈夫的遗弃,也只能默默隐忍。
中国古代的婚制是父方的,关于婚姻的解除,即“出妻”,也完全掌握在男方手中,女子一旦出嫁,终身不改,夫死不嫁。出妻的根据,按《大戴礼・本命》:“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窃盗去。”并列出不去的条件,作为补救:“有所取无所归不去,与更三年丧不去,前贫贱后富贵不去。”此即所谓的“七出三不去”制度,男权制的社会女性的地位可见一斑,丈夫对妻子的离弃是非常轻易的,女子面对婚姻的枷锁并没有更多的话语权。《士昏礼》有言:“父送女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毋违命。’母施矜结��曰:‘勉之敬之,夙夜毋违宫事’。”《丧服》中更有:“妇人有三从之义,无专用之道,故未嫁从夫,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强调妇人对男权的依赖,不允许有独立的思想和人格。“夫者,妻之天也”这种婚姻中的不平等关系便是当时社会男尊女卑的缩影,男子在社会和家庭中的地位占绝对的优势,女子仅是男权的附属,这也是造就《诗经》中众多的弃妇形象的根源。
《氓》中的女子自诉勤俭、貌美,本不应被去。三年里她“夙兴夜寐”,操持家务,毫无怨言,以改善“三岁食贫”,有功于夫家,理应属“前贫贱后富贵”,即不去之列。究其原因,诗中也留下可疑之处,在女子追忆往昔生活,与夫愤然诀别时,唯独不提离别亲生子女的悲痛及对夫家子女的思念,有违母性,不合人之常情。且《氓》通篇未提夫妇育有子女,让人引发猜测,夫妇生育困难,未育子女?“无子,为其绝世也”,在夫权制的宗法社会,无子威胁到世族存亡,是颇为严重的出妻理由,隧把女子归为“无子而去”,也不无可能。亦或是男子婚后“二三其德”,喜新厌旧,始乱终弃,女子述其因年老色衰被弃,满腔愤恨,情真意切,是否属实,今难以定论。但这也确实反映了当时男性对女性的压迫,女性在不合理的婚姻制度下的辛酸场景,也让我们看到了那个时代女性的生活状态和不平等待遇,及在面临婚姻破裂时的悲惨命运走向。
总之,《诗经》作为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描绘了周代鲜活的生活画卷和丰富的历史文化风俗。不仅是璀璨夺目的文学遗产,更具有很高的民俗学价值。中华民族的古老婚俗源远流长,至今在边远的农村,仍有婚姻“六礼”的缩影。《氓》作为一首典型的弃妇诗,全诗虽短,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婚姻制度、习俗和礼仪,以及那个时代的女性生存状态,值得我们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