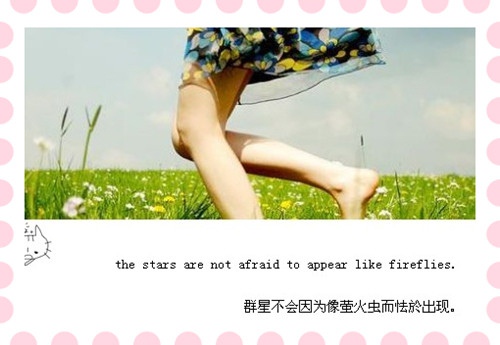汪曾祺其人其事
这世间,可爱的老头儿很多,但可爱成汪曾祺这样的,却不常见。
生活家汪曾祺
他惯于“贪得无厌”,有很多爱好。贪吃,贪喝,贪看,贪玩儿,贪恋人世间。
他好酒异常,喝起酒来,从不会一口一口抿或者呷,而是痛饮酒,一喝一大口。
他还好吃,从他诸多谈吃的文字来看,他简直是吃尽四方的人。从家乡高邮的鸭蛋到北京的豆汁儿,到湖南的腊肉,包括咸菜,酱菜,野菜,他都要追究,琢磨一番。而且时常要发出毫不保留的赞叹:我一辈子没有吃过昆明那样好的牛肉。
暮年因为疾病缠身,医生给立了很多规矩,酒是要戒的,油炸食品也不行,硬东西更要注意。——这可怎么活?他蹙眉,发愁,就偏不沮丧。他不是个容易沮丧的人。他的愁总会有转折——“幸好有天下第一的豆腐,我还能鼓捣出来一桌豆腐席来的,不怕!”他这样给自己打气。
1997年5月16日,离世当天,他想喝口茶水,医生不让,他就“撒娇”:皇恩浩荡,赏我一口喝吧。医生勉强同意沾沾嘴唇后,他对小女儿说“给我来一杯,碧绿!透亮!的龙井!但龙井尚未端来,他就已离世。
对于草木,他也皆有情意。还是少年时,他就有心发现家里的园子里什么花最先开,祖母佛堂里那个铜瓶里的花也是常常由他来换新,换花后的画面也是他眼里的景儿:父亲一醒来,一股香气透进帐子,知道桂花开了,他常是坐起来,抽支烟,看着花,很深远地想着什么。
他对那些草木如数家珍,有着特别的“占有欲”:“那棵龙爪槐是我一个人的。我熟悉它的一切好处,知道哪个枝子适合哪种姿势。”
他贪玩儿,年轻时爱唱戏,吹笛子,后来放弃是因为——“牙齿陆续掉光,撒风漏气。”然后还写写字,画画画,做做菜。
他爱逛菜市场,觉得买菜也是创作,想买冬笋,未果,却碰上荷兰豆,就要“改戏”。
他有一种“无可救药”的天真,容易对琐碎的,稚气的事情发生热情。
1987年9月到12月,老头子到美国爱荷华参加“国际写作计划”,陆续给老伴儿发回一些家书。明明是第一次,到美国,他的信里却无关繁华,他在意的是“爱荷华河里有很多野鸭子,都不怕人。”“美国的猪肉、鸡都便宜,但不香,蔬菜肥而味寡,大白菜煮不烂……”参观林肯墓,他的发现是“林肯的鼻子是可以摸的”,去海明威农场,老人家的发现是海夫人非常胖。“我抱了一下,胖得像一座山!”
而对于大事,他又神经大条,在《随遇而安》中回忆自己当右派的经历时,他居然如此起笔:我当了一回右派,真是三生有幸。要不然,我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
文体家汪曾祺
关于汪曾祺的文字,都知道是“别一家”的。他也自己逗趣,称自己是文体家。曾有评论家说:汪曾祺的语言很怪,拆开来没什么,放在一起,就有点味道。他的句子大都短峭、平实、朴拙,文字直白冲淡,像在水里洗过一样,干净。
曾有文章描述一种豆瓣酱,“清淡,而且还是那种汪曾祺级别的。”其中的妙处对于熟知汪曾祺的人来说,是非常传神的。
汪曾祺师承沈从文,习得最要紧的是“要贴到人物写”和对话不能写成“两个聪明脑壳在打架”,要平实。贴着人物写,后来被他引申为“气氛即人物”。
他惯于写普通人,平常事,市井人生,人间烟火,而且带着沈从文式的“温爱”与同情,因为“我对这些人事最为熟悉”,他说。
尽管他自称是通俗抒情诗人,但能看到他对于抒情是克制的,他说:好的,坏的,都不要叫出来。
他写的父子生活片段,就是非常克制的抒情:有一年夏天,我已经像个大人了,天气郁闷,心上另外又有一点小事使我睡不着,半夜到园里去。一进门,我就停住了。我看见一个火星。咳嗽一声,招我前去,原来是我的父亲。他也正因为睡不着觉在园中徘徊。他让我抽一根烟,我搬了一张藤椅坐下,我们一直没有说话。那一次,我感觉我跟父亲靠得近极了。
朋友汪曾祺
很奇怪,谈到他的朋友,首先想到的却是他的父亲和儿子。因为对老头子来说,父亲,儿子都和他是朋友。从他父亲开始,多年父子成兄弟的话就被挂在嘴边。他也和他们成为了朋友。
在他笔下,父亲是个随和,爱带着孩子玩的孩子王,学业上也任由他随性来,好了,夸奖,差了,不怪。17岁,他初恋,暑假在家写情书,父亲在一旁瞎出主意。因为管教松,十几岁,他就学会抽烟、喝酒。喝酒时,父亲会给自己一杯,给他一杯。抽烟时,父亲自己一根,给他一根,还会给他点上。
对自己的儿子,他同样如此。孩子恋爱,他了解,却不干涉,相信他的决定。孩子们在家有时叫他“爸”,有时叫他“老头子”,甚至孙女也这样跟着叫。
他喜欢这种没大没小,觉得父母让人敬畏,儿女“笔管条直”最没有意思。
散文家苏北曾对汪曾祺1947至1948年在上海的时光着迷。因为那段时间分别是三个可爱老头儿黄永玉,汪曾祺,黄裳的二字头年龄。他们仨一起,那得多带劲!为了解更多,2007年,他写信给黄裳,黄裳在收到苏北寄去的关于汪曾祺作品的新书后,“调皮”地说:山东画报把曾祺细切零卖了,好在曾祺厚实,可以分排骨、后腿……零卖,而且“作料”加得不错……
而黄永玉更是直接表示:我一直对朋友鼓吹三样事:汪曾祺的文章、陆志庠的画、凤凰的风景。
关于汪曾祺的故去,他曾如此叙述:和他太熟了,熟到连他死了我都没有悲哀。他去世时我在佛罗伦萨。一天,我在家里楼上,黑妮回来告诉我:“爸爸,汪伯伯去世了。”我一听,“嗬嗬”了两声,说:“汪曾祺居然也死了。”这有点像京剧《萧何月下追韩信》中,萧何听说韩信走了,先“嗬嗬”笑两声,又有些吃惊、失落地说了一句:“他居然走了。”我真的没有心理准备他走得这么早,总觉得还有机会见面。他走时还不到八十岁呀!要是他还活着,我的万荷堂不会是今天的样子,我的画也不会是后来的样子。他在我心里的分量太重,很难下笔。
已识乾坤大,犹怜草木青
汪曾祺的文字,就是糖衣炮弹。他是为了让你怅惘而生的。
他是美的侦探
已识乾坤大,犹怜草木青。这两句诗是马一浮的,我读了就喜欢,常常提起。现在要写汪曾祺了,才发现,这十个字是应该专门用在他身上的。
他写过多少草木啊,拿他这些文字,可以编一本词典,薄薄的,并不整齐划一的。这种词典不解决什么疑难,就是没事翻翻,让你觉得随身带了一个花园,或者一个不错的菜园。
他对菊花不讨厌,但讨厌菊展,他觉得菊花还是得一棵一棵的看,一朵一朵的看。
确实,很多人成天忙活的就是把美从土里揪出来,搅拌成水泥,去砌墙。汪曾祺就跟这些人着急,上火,这些人就像《茶馆》里说的,“把那点意思弄成了不好意思”。
他夸沈从文的《边城》,他说是“一把花”。真好。多少人会顺嘴夸成是一朵花,可是汪曾祺知道,他老师写的是一把花。美是很多的,不一样的,美和美是在一起的,起码是互相牵挂着的,所以是,一把花。
汪曾祺写过很多次沈从文,我因此才知道沈从文是怎么过日子的,怎么叹气怎么高兴。他也让我知道西南联大是怎么回事,那学校有点像他爱提起的京剧《桑园寄子》:“走青山望白云家乡何在”。青山白云都是真的,家乡不在身边,也是真的。我后来读齐邦媛的《巨流河》,可为印证。
汪曾祺是个老福尔摩斯。他是个针对美的侦探。他夸某寺的罗汉塑得好,就说有个穿草鞋的罗汉,草鞋上一根一根的草茎,都看得清清楚楚。
他记得祖母有个小黄蜂的琥珀扇坠,很好看。晚年在宾馆,看到人工琥珀,各路昆虫齐备,甚至还有完整的蜻蜓,在一个薄薄的琥珀片里。这当然是弄死以后,端端正正地压在里面的。他觉得还是那个扇坠好看,因为是偶然形成的。“美,多少要包含一点偶然。”
白马庙教中学的时候,他看见一个挑粪的,“粪桶是新的,近桶口处画了一圈串枝莲,墨线勾成,笔如铁线,匀匀净净。粪桶上描花,真是少见。”
多少少见的东西,少见的美,被他记录下来,作了呈堂证供。他是个好侦探。
在香港,他看见的是遛鸟的人,记得的也是这个,觉得值得写的也是这个。人家提的是双层鸟笼,楼上楼下,各有一只绣眼。早上九点钟遛鸟?北京这时候早遛完了,回家了。“莫非香港的鸟也醒得晚?”
然后他想起徐州养百灵的汉子,“笼高三四尺,无法手提,只能用一根打磨得极光滑的枣木杆子做扁担,把鸟笼担着,在旧黄河岸,慢慢地走。”
他告诉张辛欣,我看见一个香港遛鸟的人。她说:“你就注意这样的事情!”他也不禁自笑。
“在隔海的大屿山,晨起,听见斑鸠叫。艾芜同志正在散步,驻足而听,说:‘斑鸠。’意态悠远,似乎有所感触,又似乎没听。”
汪曾祺自己,在伊犁也听过斑鸠,他就趁机想家。
他夜宿大屿山,听到蟋蟀叫。“临离香港,被一个记者拉住,问我对于香港的观感。我说我在香港听到了斑鸠和蟋蟀,觉得很亲切。她问我斑鸠是什么,我只好摹仿斑鸠的叫声,她连连点头。”
这画面是有意思的,老头一本正经学斑鸠叫,女记者斑鸠似的`连连点头。
流沙河也为蟋蟀写过诗,孙犁偶也留心,这几个名字,适合放在一起。
《汪曾祺散文》收录了汪曾祺创作的散文作品,下面给大家分享《汪曾祺散文》的
《汪曾祺散文》的读书笔记1
布封说过:“风格即人”。
能够留下伟大作品的人是幸运的,即便风云变化、沧海桑田,有那一份作品为自己正身,验证一段充实丰盈的岁月,抑或是一场别样凝重的征途。
断断续续读完了《汪曾祺散文》,感觉真实纯粹、简单自然。书中有对家乡美食美景的无限眷恋,有对母校西南联大的光辉追忆,有对父亲家人的温情感念,更有对风俗文化的悉心寻探。
我最喜欢的篇章还是作者对大学生活的一段描述,可能每个人骨子里都对逝去的青春年华深深怀念,难怪这几年盛行“致青春”。青春里的自己都是快乐而无羁的,斗志昂扬、意气风发、满腔热血、壮志凌云,如果能掺杂一点爱情的甜蜜那就更完美了。《新校舍》《泡茶馆》《跑警报》让我对西南联大有了更多的了解。“西南联大”可真是一个不朽的历史名词。
百度百科中这样解释: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是中国抗日战争期间设于昆明的一所综合性大学,由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三所著名学府联合而成。具体背景应该为:1937年抗日战争发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先迁至湖南长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同年10月25日开学。1938年4月又西迁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5月4日开始上课,设立文、理、法商、工、师范5个院26个系,两个专修科一个选修班。北大、清华、南开原均为著名的高等学府,组成联大以后,荟集了一批著名专家、学者、教授,师资充实。西南联大在办学的8年中毕业学生约2000人。抗战胜利后,1946年西南联大解散,3校分别迁回北京、天津复校。
西南联大与祖国的命运相关,在特殊的时期孕育了一群卓越的师生。当时的著名教师有:陈寅恪,吴有训,梁思成,金岳霖,朱自清,冯友兰,沈从文,闻一多,钱钟书,吴大猷,
华罗庚,朱光潜,林徽因,吴晗,吴宓,卞之琳,张伯苓。难道有一个研究联大校史的美国教授以为:联大八年,出的人才比北大、清华、南开三十年出的人才都多。答案是:自由、时事。
兵荒马乱,前方抗战,云南联大的学子们却是清净活跃地经营着自己的生活。《泡茶馆》中的茶馆林林总总、规模各异、名目繁多,为学生们提供了休闲读书的好去处。有同学从早到晚泡在茶馆,甚至牙刷都寄存在茶馆,深夜才回宿舍。绍兴的老板惜才爱士,会资助学生奢侈的去南屏电影院看一场电影。《跑警报》中,虽然警报声声刺耳,而学子们更多地在警报声中寻出了乐趣。一位姓马的同学在每次跑警报时,不忘带上一壶水,一点吃的,还要夹上温飞卿或李商隐的诗,才慢悠悠地向后山走去。哲学系的研究生在跑警报时推理出了自己的哲学。“有人带金子,必有人会掉金子,有人掉金子,必有人会捡到金子,我是人,故我可以捡到金子。”故此,每次解除警报时,他都会细心查看路面,还真有两次捡到了金子,由此实践了自己哲学的合理性。更有一位罗同学,在别人都去后山躲警报时,自己一人逍遥自在地在宿舍楼里洗头洗衣,因为此时,没有人和她争抢。形形色色的学子,诙谐幽默的生活。
《湘行二记》令我了神思,我也想去一趟湖南桃花县,去看一眼现实版的桃花源,虽然世人都说不像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但慰藉一下多年的畅想也是可以的。还有岳阳楼,“长江三胜,滕王阁,黄鹤楼都没有了,就剩下这座岳阳楼了”。那么多岳阳楼的诗句,那么多洞庭湖的篇章,影响最深远的还属范仲淹的《岳阳楼记》。而范仲淹恰恰从没有去过岳阳楼,从没有看见洞庭水,却写的如此千回百转、荡气回肠,难得,难得啊!
《林肯的鼻子》一文中写到,林肯的墓前有林肯铜人雕塑,游客们为了借染好运,都要摸一摸林肯的大鼻子,日复一日,林肯的鼻子部位铜漆凋落,格外显眼。作者似乎不太认同这样旅游习俗,而回顾我们周围,不是也存在很多类似的情况吗?我倒觉得摸摸也无妨,游客们不远千里慕名而来,总得亲手碰触一下历史,这样才不留遗憾吧。
我是喜欢吃葡萄的,正应了一句广告“酸酸甜甜真好吃”。而看完《葡萄月令》,才让我对葡萄艰难神奇的生命有了切实了解。从来不知道葡萄的根在冬天是要下埋的,积雪覆盖。来年开春再挖出来,搭架、上棚。从不知道,葡萄的枝叶是一脉水管,将根部的水分尽情吸饮,这是多了多么神奇的植物啊。
《汪曾祺散文》值得翻阅,倘若喜欢,细致咀嚼,不合君意,那就大致浏览。开卷有益,更何况是大家名作呢?
《汪曾祺散文》的读书笔记2
“把感情放在一粒尘埃上。”我想,用这句话来形容我合上书的心情,实在是再好不过的了。洁白的封面略是一点粗糙,点点红粉染缀其中一角,几根粗细不一的黑色水墨枝条穿插其间,轻轻抚摸,仿佛梅香已然。
我们说,散文,有松散的形式。那我想,汪先生的散文可谓是真的“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文字质朴平淡,仿佛只是在娓娓道来,道家常,讲故事。从书画到文学,从文学再到戏曲,更有从美食到花木果蔬,还有家乡与那所南菁中学。生活的一切,其实不过为这些微小细腻的事物而构造的。“夜深闻私语,月落如金盆。”就像张爱玲的一篇《私语》一般——你听我说,我把我的故事,一一道来。
在《葡萄月令》里,有一句话特别迷人:“都说梨花像雪,其实苹果花才像雪,雪是厚重的,不是透明的。梨花像什么呢?——梨花的瓣子是月亮做的。”
我未曾见过梨花,也不曾看过苹果花的风采,但读了这一句,我却犹如嗅到花香,看到了花,她们或许开在低矮的枝头,展开洁白的花瓣。“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岑参的这句诗早被我们吟诵了千百遍,而将梨花的瓣子比作是月亮,一点点弯细玲珑,固然妙意只增不减。那种美感在不经意间就悄悄坠入我目帘,而汪先生又并未写下太多艳丽的辞藻都大说一通,这种微妙的感觉实在是让我困惑。
花,是一滴墨,当你蘸上清淡的水,当淡墨悄然融合,情感溅落宣纸上,才能慢慢渲染弥漫开来。
而在《夏天》中,又好似是花园中百花起舞,各种花朵都不过轻写一个短句:“夏天的花里最为幽静的是珠兰。”“牵牛花短命。早晨沾露才开,午时即已萎谢。”“秋葵也命薄。瓣淡黄,白心,心外有紫晕。风吹薄瓣,楚楚可怜。”好像在文字中,花儿们都换上裙装化为豆蔻女子,各自有自己的性格与宿命,却又各不相争,演绎自然和谐之乐。每一朵花儿,每一颗露珠都被赋予了生命,在平白轻述的文字跳跃。是那样的细微,却又那样的缠人。不是豪放,也不是艳丽而是情感的缱绻将美丽压成一张张纸。抚摸书页,仿佛仍有余香。
生活赋予我们什么?一顿食物,一场天气,一次旅行?我们总说,要用心体验生活,要细细观察,多多思考。从不凡归属平淡,从浩荡终归细节。或许生活不过是一片花瓣一个枕头,一支笔,一张纸,写下我们的故事,写下我们微弱的感触。
我愿执笔轻描,从细节看生活。
《汪曾祺散文》的读书笔记3
周六,我在朋友圈发了一条微信:“在家傻待,谁约我”结果本来在和同学约会的女儿放弃约会,给我回了条微信:“我约你”就和女儿来到东方广场。来到东方书城一个新开的书吧。买了杯饮料开始了我们的周末约会。当时女儿拿起一本汪曾祺散文《随遇而安》说:“我喜欢看汪曾祺的散文”,“为甚”?女儿说:“他有几本是全是写吃的”——汗,又暴露了我的女儿是个吃货。顺着女儿的推介我就拿汪曾祺散文《随遇而安》看起来。
看了几页就吸引了我,他的文字里透着浓浓的“中国味”不乏味,且蕴含着民主心灵和性灵的美质。却又淡淡的,时而把带进了北京的`四合院大街小巷;时而把我带回了童年月光下妈妈在大树底下给我们讲述那些年她做过的“牛鬼蛇神”;时而又把我带进了舌尖上的中国那大川南北的中国民间美食景象。看他书令你身在烦嚣的闹市却犹如穿越到另一个世界。——其实我也挺喜欢这样写作风格。我自己一直也有像他这样写写自己的生活,写写自己的感想以及看到一些事的所见所闻。但当我看到同事们在博客上写的都是专业的,高水平的大作,总觉得自己的文章不适合登大雅之堂。所以一直不敢在这大雅之堂丢人,但为了——你懂的。
表面上看这书其实是一本茶余饭后的消遣书籍,但慢慢品味却也从中得到人生的感悟。书中我感受到了他从容,他淡然,他身处逆境却不以为苦,他达观潇洒,随遇而安!其中我最喜欢他的这一段:“丁玲同志曾说她从被划为右派到北大荒劳动,是”逆来顺受“。我觉得这太苦涩了,”随遇而安“,更轻松一些。”遇“,当然是不顺的境遇,”安“,也是不得已。不”安“,又怎么着呢?既已如此,何不想开些。如北京人所说:”哄自己玩儿“。当然,也不完全是哄自己。生活,是很好玩的。
随遇而安不是一种好的心态,这对民族的亲和力和凝聚力是会产生消极作用的。这种心态的产生,有历史的原因(如受老庄思想的影响),本人气质的原因(我就不是具有抗争性格的人),但是更重要的是客观,是”遇“,是环境的,生活的,尤其是政治环境的原因。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善良的。曾被打成右派的那一代人,除了已经死掉的,大多数都还在努力地工作。他们的工作的动力,一是要实证自己的价值。人活着,总得做一点事。二是对生我养我的故国未免有情。但是,要恢复对在上者的信任,甚至轻信,恢复年轻时的天真的热情,恐怕是很难了。他们对世事看淡了,看透了,对现实多多少少是疏离的。受过伤的心总是有璺的。人的心,是脆的”
所以说做人一门学问,做事更是一门学问。很多人之所以一辈子都碌碌无为,那是因为他活了一辈子都没有弄明白该怎样去做人做事。看了这本书似乎令我有所感悟。
放下书,天已黑了,找吃的,谢谢女儿给了我一个充实的周末!
汪曾祺(qí)(1920.3.5~1997.5.16),江苏高邮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著名的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早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历任中学教师、北京市文联干部、《北京文艺》编辑、北京京剧院编辑。在短篇小说创作上颇有成就。著有小说集《邂逅集》,小说《受戒》《大
内容提要
中华散文,源远流长。数千年的散文创作,或抒情、或言志、成状景、或怀人……莫不反映出时代的风云变幻和人们的'思想情感。中华散文的这些优良传统在二十世纪以降的新文学那里,不仅得到了全面传承,且不断有所创新、有所发展。为了展示二十世纪以来中华散文的创作业绩,编者在新世纪之初即编辑出版过“中华散文珍藏本”凡三十种。时光五载已过,编者又在此基础上精编出这套“中华散文插图珍藏版”十六种。经再次
目录
《我的家乡》
《文游台》
《观音寺》
《午门忆旧》
《一辈古人》
《吴大和尚和七拳半》
《新校舍》
《泡茶馆》
《跑警报》
《自得其乐》
《自报家门》
《随遇而安》
《多年父子成兄弟》
《星斗其文,赤子其人》
《金岳霖先生》
《老舍先生》
《国子监》
《钓鱼台》
《水母》
《城隍·土地·灶王爷》
《老不闲抄》
《胡同文化》
《我是一个中国人》
《故乡的食物》
《吃食和文学》
《宋朝人的吃喝》
《葵·
《五味》
《寻常茶话》
《食豆饮水斋闲笔》
《韭菜花》
《花》
《果园杂记》
《葡萄月令》
《翠湖心影》
《昆明的雨》
《湘行二记》
《泰山片石》
《北京的秋花》
《林肯的鼻子》
《美国短简》
《香港的鸟》
《谈风格》
《谈谈风俗画》
《“揉面”》
《〈大
《关于〈受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