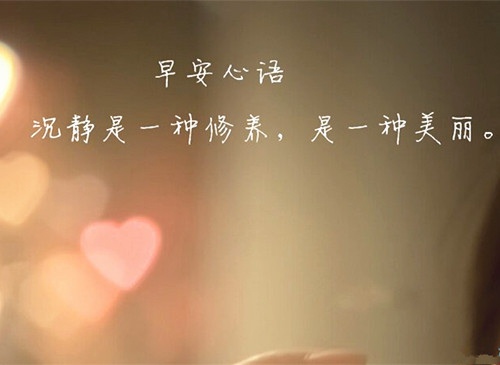《伤逝》是现代文学家鲁迅于1925年创作的一部以爱情为题材反映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命运的短篇小说。小说的优美段落有哪些?一起来了解一下!
1.在一年之前,这寂静和空虚是并不这样的,常常含着期待;期待子君的到来。在久待的焦躁中,一听到皮鞋的高底尖触着砖路 的清响,是怎样地使我骤然生动起来呵!于是就看见带着笑涡的苍白的圆脸,苍 白的瘦的臂膊,布的有条纹的衫子,玄色的裙。她又带了窗外的半枯的槐树的新 叶来,使我看见,还有挂在铁似的老干上的一房一房的紫白的藤花。
2.子君不在我这破屋里时,我什么也看不见。在百无聊赖中,顺手抓过一本书来,科学也好,文学也好,横竖什么都一样;看下去,看下去,忽而自己觉得,已经翻了十多页了,但是毫不记得书上所说的事。只是耳朵却分外地灵,仿佛听到大门外一切往来的履声,从中便有子君的,而且橐橐地逐渐临近,——但是,往往又逐渐渺茫,终于消失在别的步声的杂沓中了。我憎恶那不像子君鞋声的穿布底鞋的长班的儿子,我憎恶那太像子君鞋声的常常穿着新皮鞋的.邻院的 搽雪花膏的小东西!
3.我已经记不清那时怎样地将我的纯真热烈的爱表示给她。岂但现在,那时的事后便已模胡,夜间回想,早只剩了一些断片了;同居以后一两月,便连这些断片也化作无可追踪的梦影。我只记得那时以前的十几天,曾经很仔细地研究过表示的态度,排列过措辞的先后,以及倘或遭了拒绝以后的情形。可是临时似乎都无用,在慌张中,身不由己地竟用了在电影上见过的方法了。后来一想到,就使我很愧恧,但在记忆上却偏只有这一点永远留遗,至今还如暗室的孤灯一般,照见我含泪握着她的手,一条腿跪了下去……。
4.她却是什么都记得:我的言辞,竟至于读熟了的一般,能够滔滔背诵;我的举动,就如有一张我所看不见的影片挂在眼下,叙述得如生,很细微,自然连那使我不愿再想的浅薄的电影的一闪。夜阑人静,是相对温习的时候了,我常是被质问,被考验,并且被命复述当时的言语,然而常须由她补足,由她纠正,像一个丁等的学生。
5.去年的暮春是最为幸福,也是最为忙碌的时光。我的心平静下去了,但又有别一部分和身体一同忙碌起来。我们这时才在路上同行,也到过几回公园,最多的是寻住所。我觉得在路上时时遇到探索,讥笑,猥亵和轻蔑的眼光,一不小心,便使我的全身有些瑟缩,只得即刻提起我的骄傲和反抗来支持。她却是大无畏的,对于这些全不关心,只是镇静地缓缓前行,坦然如入无人之境。
6.每日办公散后,虽然已近黄昏,车夫又一定走得这样慢,但究竟还有二人相对的时候。我们先是沉默的相视,接着是放怀而亲密的交谈,后来又是沉默。大家低头沉思着,却并未想着什么事。我也渐渐清醒地读遍了她的身体,她的灵魂,不过三星期,我似乎于她已经更加了解,揭去许多先前以为了解而现在看来却是隔膜,即所谓真的隔膜了。
7.这是真的,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
8.安宁和幸福是要凝固的,永久是这样的安宁和幸福。我们在会馆里时,还偶有议论的冲突和意思的误会,自从到吉兆胡同以来,连这一点也没有了;我们只在灯下对坐的怀旧谭中,回味那时冲突以后的和解的重生一般的乐趣。
9.待到孤身枯坐,回忆从前,这才觉得大半年来,只为了爱,——盲目的爱,——而将别的人生的要义全盘疏 忽了。第一,便是生活。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世界上并非没有为了奋斗者而开的活路;
10.她早已什么书也不看,已不知道人的生活的第一着是求生,向着这求生的道路,是必须携手同行,或奋身孤往的了,倘使只知道捶着一个人的衣角,那便是虽战士也难于战斗,只得一同灭亡。
11. 我以为将真实说给子君,她便可以毫无顾虑,坚决地毅然前行,一如我们将要同居时那样。但这恐怕是我错误了。她当时的勇敢和无畏是因为爱。
12.我愿意真有所谓鬼魂,真有所谓地狱,那么,即使在孽风怒吼之中,我也将寻觅子君,当面说出我的悔恨和悲哀,祈求她的饶恕;否则,地狱的毒焰将围绕我,猛烈地烧尽我的悔恨和悲哀。
我将在孽风和毒焰中拥抱子君,乞她宽容,或者使她快意……。
13.我活着,我总得向着新的生路跨出去,那第一步,——却不过是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为子君,为自己。
我仍然只有唱歌一般的哭声,给子君送葬,葬在遗忘中。
我要遗忘;我为自己,并且要不再想到这用了遗忘给子君送葬。
我要向着新的生路跨进第一步去,我要将真实深深地藏在心的创伤中,默默地前行,用遗忘和说谎做我的前导……
内容简介
涓生和子君都是五四式新青年。子君认识涓生后,便不断地拜访他,听他讲新文化、新道德、新观念,深受其影响,并与之相恋。之后,子君又坚决地对涓生表示:“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接着,与涓生一起寻住所、筹款子,并不顾亲朋的反对而同居,建立小家庭。但子君很快就陷入家务之中,他们的爱情也未能“时时更新,生长,创造”。不久,涓生为当局所辞,他们便生活无着,涓生对子君的爱情也随之消减以至最后消失;但涓生又不便说出,只好外出躲避。迫于生计,子君宰吃了所饲养的油鸡,放掉了所喂养的狗。最后,涓生对子君坦露自己不再爱她的真实想法,她便被其父亲领回了家,并在无爱的人间死了。当涓生得知实际上是自己说出的真实导致了子君的死时,他追悔莫及,于是,长歌当哭,凄惋地唱出了自己的悔恨和悲哀,写下这篇手记,为子君送葬。
创作背景
“五四”时期,诉说婚姻不自由的痛苦,是许多青年的公意,争取恋爱婚姻自由已成为当时个性解放思想的重要内容。因此,20世纪20年代的小说创作,描写男女恋爱的占了全数的百分之九十八,其中最多的是写婚姻不自由。鲁迅对个性解放的反封建意义,是予以充分肯定的,但同时也敏锐地发现隐藏在恋爱婚姻自由背后的危机。早在1923年底,鲁迅就在《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中指出。妇女要解放应该用“剧烈的战斗”去争取经济权,“如果经济制度竟改革了,那上文当然完全是废话”。到了1925年,鲁迅的世界观已处在根本转变的前夕,这时他则主张用“火与剑”的方式去彻底变革社会制度了。1925年10月写的《伤逝》,不同于当时流行的歌颂恋爱至上的作品,也不同于传统名著中以死殉情的悲剧。鲁迅用小说的形式,把妇女婚姻和青年知识分子的问题跟整个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的变革联系起来,以启示广大青年摆脱个性解放和个人奋斗的束缚,探索新的路。
解
《伤逝》选自鲁迅小说集《彷徨》,是鲁迅唯一的以青年的恋爱和婚姻为题材的作品。恋爱自由、婚姻自主是“五四”以后青年所普遍关心的一个问题。《伤逝》以独特角度,描写了涓生和子君的恋爱及其破灭过程。作者以一般作为追求目标的自主婚姻的完成的喜剧性结局,作为自己所揭示的一出社会悲剧的出发点。小说从正面着力刻画的不是黑暗势力的破坏和迫害,而是作品主人公涓生和子君本身的思想弱点。从涓生和子君冲破阻力争得了自主婚姻,婚后社会迫害的继续存在及由此产生的矛盾,到最后这自主婚姻的破灭的整个过程。深刻地指出了在黑暗社会里,恋爱和婚姻问题不可能是一个孤立的问题,它的最终解决,不能仅靠着个性的解放。它只能是整个社会解放的一个组成部分。
作品采取“涓生手记”的形式,回顾从恋爱到感情破灭的一年的经历,以小说主人公的切身感受来抒发他曾有的热烈的爱情,深切的悲痛和愿入地狱的悔恨,具有很浓的抒情性。小说的细节描写也颇具匠心,油鸡和阿随的命运同子君感情变化的呼应,收到了以小见大的效果。
相关思考:
1.涓生和子君爱情悲剧的原因和意义是什么?
答:《伤逝》是鲁迅惟一的以青年的恋爱和婚姻为题材的小说。恋爱自由、婚姻自主是“五四”时代的青年们所热烈追求的生活理想,也是当时文学创作的热门题材。当时的这类作品,大多致力于描写青年男女冲破封建束缚、追求个性解放和恋爱自由的斗争过程,并往往以自主婚姻的实现作为结局。但鲁迅的《伤逝》却以悲剧收场,而且不是一般的恋爱悲剧,而是自由恋爱成功后的婚恋悲剧。小说的主人公涓生和子君在相爱的过程中,尽管遇到来自家庭和社会的各种阻挠,但他们无所畏惧,毫不退缩,子君的态度尤其坚决。面对父亲和叔父的反对,她坚定地表示:“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权利!”正是靠这种无畏的勇气和坚定的态度,他们终于冲破重重阻碍而结合,实现了婚姻自主的理想。
但涓生和子君婚后的“安宁和幸福”并未维持多久,他们的爱情悲剧恰恰发生在恋爱成功,婚姻自主之后不久。首先来临的打击是涓生被解聘。失去职业后,他们的生计成了问题。虽然他们尝试用其他方法“来开一条新路”,但都没有走通。这使他们的爱情生活蒙上了阴影。加上结婚后,子君以为追求的目标达到了,便日渐沉浸在小家庭琐碎的生活中,不再去上进了,变成了一个目光短浅的甚至有些庸俗的家庭主妇,甘愿做靠丈夫养活的附属品。实际上,子君尚未得到真正的自由就停止了追求。软弱而自私的涓生在感受到婚后生活的平庸和生活的压迫时,只想着“救出自己”,并自欺欺人地把抛弃子君作为自己“向着新的生路跨出去”的第一步,结果是导致了子君的死亡,而他自己也并未真的跨入新的生活,整日在悔恨与悲哀中消磨着生命。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涓生和子君的爱情悲剧的原因,既是那个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和黑暗势力的破坏与迫害,也与他们本身的弱点——如软弱、自私、目光短浅和狭隘自私的个人主义等有关。涓生和子君爱情悲剧的意义在于,它启示人们:在一个不合理的社会中,单纯追求个性解放和婚姻幸福,是不可能成功的。只有在为社会解放而斗争的过程中,才能真正实现个性的解放和个人婚恋的幸福。
2.分
子君是一个受“五四” 新思潮洗礼,但还没有完全脱尽旧思想影响的知识女性。她说:“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是妇女个性解放的宣言,她以此为思想武器,为自己的恋爱婚姻自由而奋斗。她敢于蔑视封建礼教,对个性解放的要求非常强烈。子君为了在两性关系上求得“纯真热烈爱”,不顾族长们的“威严和冷眼”,也毫不畏惧周围的“讥笑,猥亵和轻蔑的眼光”,镇静地、大无畏地走她的路。子君的反封建精神,显示了“五四”时期中国妇女的初步觉醒。
子君的根本问题在于:她作为反抗的主要动力仅是爱情,这本身就决定了她的悲剧。她除了追求个人的爱情幸福之外,没有什么政治理想或社会抱负。她把家庭生活当做整个人生意义,整天忙碌于家务琐事,热心于养“小油鸡”“叭儿狗”,或者浪漫地回味过去爱情生活的乐趣。她与涓生同居以后,完全陶醉于平庸、狭小的生活天地里,先前在会馆里与涓生“谈家庭专制,谈打破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的`热烈气氛也全然消失了。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离开了社会改革,妇女追求个人的自由和幸福,是很难实现的。争取个性解放的子君终于未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妇女解放。子君走出封建家庭,走进了小家庭,在旧势力压迫下,又回到封建家庭,在无爱的人间抑郁而死。子君的悲剧表明:个性解放、个人奋斗不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正确道路,应该别寻出路。
3.分
答:大量的内心独白和深重的抒情性是《伤逝》的主要艺术特色。
在结构上采用第一人称手记的形式,以抒情主人公“我”的思想感情发展为主线,将人物、事件等连缀起来,极富感情色彩。在描写方法上不重外貌描写,而是采取多种形式,细腻逼真的刻画人物的内心世界及其思想感情的变化,如心理描写、内心独白等。
在语言上大量采用反复、排比、比喻等诗歌常用的手法,增强了小说的抒情性。以倒叙的形式,回顾从恋爱到感情破灭的一年的经历,以主人公的切身感受来抒发他曾有的热烈的爱情,深切的悲痛和愿入地狱的悔恨,把主人公的感情发展脉络清楚地表现出来。
此外,小说的细节描写也颇具匠心,油鸡和阿随的命运同子君感情变化相呼应,收到了以小见大的效果。
4.简
《伤逝》是鲁迅惟一的爱情小说。它的思想内涵一方面在于探索妇女解放的道路。子君是受过“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的知识女性。她以个性解放为思想武器,为自己的恋爱婚姻自由而奋斗,和涓生建立起小家庭。但是胜利的喜悦却是悲剧的起点。悲剧的社会根源是封建势力的压迫。封建势力视青年自由恋爱为丧风败俗,涓生的失业加速了涓生和子君感情的分裂。但子君及所信奉的个性解放思想的局限性,也是造成悲剧的思想根源。子君追求的只是恋爱婚姻自由,奋斗目标的实现,就把狭窄的小天地当做整个世界,把小家庭生活当做整个人生意义。这样,人的性格也就必然变得庸俗空虚,胆怯虚弱,爱情也因此褪色,这说明,离开了社会改革,妇女追求个人自由幸福,是很难实现的。另一方面也是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道路的探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涓生的性格悲剧说明首要的是要比较清醒地认识现实,去掉唤醒,才能在严酷的现实中站稳脚跟,不失去“现在”,才可能有未来。
悼亡诗是独特的诗歌题材,它将死亡与爱情结合起来,是对人伦的浓情赞美,对幸福的无限眷恋,对生命的人文关怀。在潘岳于悼亡的定名之功之前,《绿衣》《葛生》已奠定了悼亡传统并对后世悼亡诗产生了深远持久的影响。下面是《诗经》的“悼亡”传统分析,供大家参考。
一、潘岳与悼亡诗的确立
(一)潘岳的定名之功
赵翼《陔余丛考》卷二十四指出:“寿诗、挽诗、悼亡诗,惟悼亡诗最古。潘岳、孙楚皆有《悼亡诗》载入《文选》。《南史》:宋文帝时,袁皇后崩,上令颜延之为哀策,上自益‘抚存悼亡,感今怀昔’八字,此‘悼亡’之名所始也。《崔祖思传》:齐武帝何美人死,帝过其墓,自为《悼亡诗》,使崔元祖和之。则起于齐、梁也。”
王立在《古代悼亡文学的艰难历程――兼谈古代的悼夫诗词》中这样解释赵翼的这段话:“按赵翼的意思,西晋潘岳、孙楚最早作悼亡诗,但最早提出‘悼亡’之名的是宋文帝,而后是齐武帝。至于潘岳的《悼亡诗》之名,乃是《文选》的编者萧统加上的”。于丽《悼亡诗研究》、周如月《宋前悼亡诗研究》均持此观点。
但是,潘岳《悼亡诗》除见于《文选》外,《玉台新咏》亦收前两首,题《悼亡诗二首》,《玉台》有敦煌唐写本残卷,题《悼亡二首》。张溥的《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潘黄门集》收录潘岳《悼亡赋》,张溥辑自《艺文类聚》卷三四“哀伤”类,同卷亦收潘岳《悼亡诗》,当时潘岳集尚存(《旧唐书经籍志》著录《潘岳集》十卷),来源可以说是可信的。此二证可以证明潘岳诚然于悼亡诗有定名之功。此外,李善注潘岳诗引《风俗通》:慎终悼亡。此为《风俗通》佚文,《风俗通》东汉应劭作,则“悼亡”之名又可前推。
(二)从《诗经》时代到西晋年间的悼亡诗
《诗经》后六百年间,由于历经战乱以及大一统时代壮阔宏巨的审美,大量诗作亡佚、个性化的诗歌为数不多,悼亡诗一度中断。但从现有资料看来,汉武帝继承了《诗经》的悼亡传统。汉武帝有一首悼亡诗:“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何姗姗其来迟!”。虽然诗中没有明确的对象,但从大量史实可以得到证实,武帝悼念的便是拥有“倾国倾城”(李延年《佳人曲》)之色的绝代佳人李夫人。虽然只有短短十五个字,但其中思念之情感人至深。
虽然潘岳对于悼亡诗有定名之功,但不等同于他开创了悼亡诗。从赵翼的材料中可以看出,宋文帝、齐武帝以皇帝的身份身体力行,于是上行下效,成一时之风气,对于悼亡的创作与影响的扩大有不可磨灭的功勋。王立在上文中详细论述了“帝王垂范与突破礼之束缚”,在此不赘。
二、《诗经》中的“悼亡诗”
笔者认为《邶风绿衣》与《唐风葛生》均属悼亡之作。首先从学者对此二者的解读来看,现当代学者均认定其为悼亡诗。例如刘大白在《白屋诗话》(北京市中国书店,1983)说毛诗的(二)(三)中指出“所以我底见解,以为不如说绿衣是一篇悼亡诗”,“绿衣是一篇悼亡诗,唐风葛生也是一篇悼亡诗”。其次从上文中悼亡诗的定义出发,就文本本身进行分析。
诗经邶风绿衣
绿兮衣兮,绿衣黄里/心之忧矣,曷维其已/绿兮衣兮,绿衣黄裳/心之忧矣,曷维其亡/绿兮丝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无兮/兮兮,凄其以风/我思古人,实获我心。
《绿衣》中,抒情主人公自述其情,从“女所治兮”、“我思古人”可以看出是丈夫对亡妻的悼念。丈夫思及旧物“绿衣”而念及妻子为其制衣的贤淑。通过天气转凉与无人制衣的对比,写出对亡妻的怀念,心中的悲伤,不能停止。
诗经唐风葛生
葛生蒙楚,蔹蔓于野/予美亡此。谁与?独处/葛生蒙棘,蔹蔓于域/予美亡此。谁与?独息/角枕粲兮,锦衾烂兮/予美亡此。谁与?独旦/夏之日,冬之夜/百岁之后,归於其居/冬之夜,夏之日/百岁之后,归於其室!
《葛生》现多认为是妻悼夫之作。全诗从城外墓室之景兴起,野葛缠绕着荆棘,蔹草爬满了坟茔。一二章首句读来,凄凉之景跃然纸上。而后女子缓缓叙述,那是其亡夫埋葬之所。第三章写床笫之物,斯人已去,只留我独宿到天明。后半首诗关注季节,写夏季的白日,因其长而热;写冬季的夜晚,因其漫而寒。妻子不堪忍受无人相伴的夏日冬夜,只能寄希望于百年之后,能与丈夫在坟茔中相会,不负生同床,死同穴的誓言。
三、《绿衣》《葛生》对后世悼亡诗(词)的影响
(一)爱情与死亡的情感接受
从《绿衣》《葛生》伊始,再到《李夫人歌》,以及后世无数悼亡名篇,接受者在阅读时的独特情感正是接受了爱情与死亡的诗歌母题。
我们在阅读悼亡诗作时常常嘘唏不以,为举案齐眉的深情,为相濡以沫的扶持。其实细细想来,诗歌的动人之处在于将诗人的个人遭遇无限放大,上升到人类的生命共识。而悼亡诗显然只能使我们怜悯同情却不能感同身受――丧妻之痛,除非经历,无法共鸣。所以,我们感慨的是悼亡的母题:爱情与死亡。当然,我们更希望能够长相守,所以对于悼亡诗中有情人的`死别离更感其悲。又因死之必然与无常,生之美好与不常,使我们无可奈何又感同身受,所以对悼亡之作更加喟叹。
(二)跨越时空、沟通死生的内容表达
从《葛生》中失去丈夫的妻子喊出“百岁之后,归于其居”的誓词之后,悼亡诗作便蒙上了奇幻色彩。
死者已矣,而生者犹自哀恸。当回忆过去生活的点点滴滴已不能承载诗人的悲哀,于是只能盟约百岁,遥想妻子在天上地下的生活。刘克庄发誓“留取断弦来世娶”(《石塘感旧》),李濂成说“百年尘梦断,同穴此山阿”。张耒的《悼亡九首》靠佛家来排遣悲伤。刘克庄之妻“定归兜率蓬莱去”(《风入松》四首)独留诗人在人间,茫茫求索却不得,诗人又希望她能够“辽鹤归来”,以慰余生。
于是只能日思夜梦,借梦境沟通死生与亡妻相会。苏轼在《江城子》中梦见妻子于故居梳妆,而十年不见,纵使相逢应不识,只能相顾却无言。纳兰性德的《沁园春》(瞬息浮生)即“梦亡妇淡妆素服”而作。此外,还有许多悼亡之作托巫山云雨入梦与妻相会,笔者以为有失庄重颇近艳情,故不录。
(三)特定时节与特殊空间的抒情发端
《葛生》中的妻子由夏日的漫长与冬日的苦寒而想到“谁与”的惨怛。后世在其基础上发展,一是将特定季节、时令作为其抒情发端。自宋玉悲秋之后,每逢边缘季节,诗人将内心痛苦与时序变化结合起来,倍增其哀。如王彦泓在妻亡后的第一个冬天,念及羁旅苦寒,却已无斯人为之寄衣而作《客中苦寒作》。潘岳《悼亡诗》也均感时而作。而时节所寓的特殊意义也成为悼亡的缘由。寒食、中元、冬至等祭祀之节使诗人能纵情地哀悼。如李濂于妻卒后次年寒食前后作《悼亡杂诗》十首。纳兰性德在中元写下《眼儿媚中元节有感》。而七夕、除夕等喜庆之节诗人又因妻亡家破的对比更显其哀。二是在特殊的节日如妻子周年、冥诞等追忆往事,怀念亡妻。如孙楚在妻子周年写下《除妇服诗》,徐贲作《伤往诗》。纳兰性德在妻子祭日作《金缕曲亡妇忌日有感》,王十朋在妻子冥诞写下《令人生日哭以小诗》,李濂写下《悼亡》二首。
诗人们进行悼亡时还处于特定的空间状态。其一,是位于仕途不达的彷徨之境。在考察历代悼亡之作时,通常很难界定,正是因为诗人们不仅悼念亡妻亦悼自己仕途。李商隐一生徘徊在牛李党争,他的很多爱情诗都不能很清楚地界定,正是因为他将二者结合起来,赋予了诗作更为广阔的内涵。其二,是处于才高位卑的穷困之境。且不去说是否每一位诗人都如他们自视的那般有经世济民的大才,但一个人的期望与自己所处的地位落差越大,则牢骚越多,加上妻子的离去,使他们将郁闷凝结在诗作中并借此宣泄。其三,是处于丧子之痛的苦难之境。经历丧妻前后丧子的诗人有江淹、元稹、孟郊、李煜、梅尧臣、王士祯、博尔都、毕沅等等。
(四)睹物思人的抒情方式与特殊意象的符号化
《绿衣》中亡妻遗物“绿衣”,《葛生》中内室寝具“角枕”、“锦衾”开创了后世悼亡诗睹物思人的抒情方式。几乎所有的悼亡之作均把亡妻遗物作为抒情发端,入室所见作为情感兴起。
《绿衣》中抓住“女所治兮”的旧物绿衣,运用细节描写,以小见大极言其悲。“制衣”这一特殊意象在后世广泛运用并逐渐符号化。言及制衣,便仿佛看到囊昔妻子坐在灯下一针一线地缝补,从而思念妻子的贤淑与美好。如元稹在《遣悲怀》中“衣裳已施行看尽,针线犹存未忍看”,几乎全由《绿衣》化出。“身上穿的衣服是包裹灵魂最切身的东西,故衣服对于表达爱情,具有极大的作用”。所以江淹《悼室人》“秋至捣罗纨,泪满未能开”,李商隐《悼伤后赴东蜀辟至散关遇雪》“无家与寄衣”,梅尧臣《悲书》“衣裳昔所制”,贺铸《鹧鸪天半死桐》“空床卧听南窗雨,谁复挑灯夜补衣”,王士祯《悼亡》二十四首“年年辛苦寄冬衣”,赵翼《悼亡》“手泽尚存衣线补”等等作品中,用“衣”的意象希望“与穿着佩戴者产生心灵或超乎心灵的交流”,表达了对妻子的深切思念。
《葛生》中“角枕”、“锦衾”同样是旧物,但又与“绿衣”不同。“角枕”、“锦衾”是床笫之物,表示着夫妻间的亲密之情。看到“角枕”、“锦衾”,便仿佛重温往日与妻子在一起的耳鬓厮磨,从而感怀往日的欢愉与幸福。后世悼亡在意象的选择上同样具有这个特点。潘岳在《悼亡诗三首》(其一)中“入室”所见“帏屏无仿佛,翰墨有余迹”,正是帷屏仍在,而诗人却不能如武帝招魂,连亡妻的影子都不曾见到。笔墨仍留有余香,而书写之人已逝。又如沈约《悼亡诗》“帘屏既毁撤,帷席更施张。游尘掩虚座,孤帐覆空床”,李煜《书灵筵手巾》“汗手遗香渍,痕眉染黛烟”,元稹《六年春遣怀八首》“重纩犹存孤枕在”等等。
(五)对比与白描的写作手法
白描作为诗歌初级阶段自发手段,在《诗经》中的大量运用十分寻常。《绿衣》中叙述丈夫抚摸亡妇遗衣,感到凄风与寒意,从而思古人;《葛生》由远及近,逐步叙述夫妻生活点滴。而魏晋以降,诗歌进入自觉阶段并以“缘情而绮靡”(陆机《文赋》)为审美、实际创作中也表现出“稍入轻绮”(《文心雕龙明诗》)的诗风之后,白描手法在悼亡诗中的运用远远高于其他诗别。诗人用白描的手法缓缓叙述夫妻间的琐屑点滴,其情更深其事更真也更加感人。如韦应物在同德精舍旧居伤怀时所作《伤逝》《往富平伤怀》《出还》《送终》等。“斯人既已矣”但留下旧物、故居与幼子。“今者掩药扉,但闻童稚悲”,幼女无知,庭下嬉戏,“见余哀泣,亦复涕咽。试问知有所失”、(韦应物《故夫人河南元氏墓志铭》),童稚亦知失母,捉住父亲衣裳紧紧不放,嚎啕大哭。悱恻之痛,“益不能胜”,历代学者,不忍卒读。元稹在《三遣悲怀》叙述公侯贵女婚后与自己相濡以沫的贫贱生活:为我无衣而搜荩箧,为我沽酒而拔金钗。无粮以野蔬为食,无柴以落叶为薪。浅入平出,至情至性。又如王十朋《述怀》、吴嘉纪《哭妻王氏》等。
对比是《诗经》中的常用手法,《绿衣》中斯人已去而绿衣尤存,凄其以风而无人制衣;《葛生》中坟外景物荒凉衬愈发托出内心的枯寂,夏日冬夜的漫长愈发衬托出独处的孤独。对比在后世悼亡诗中也十分常见。主要表现为物是人亡的对比。如纳兰性德在卢氏棺柩暂厝之地双林禅院写下多篇悼亡之作,《望江南宿双林禅院有感》、《青衫湿悼亡》等。又有物移人非的对比。如江淹《悼室人诗十首》中“窗尘岁时阻,闺芜日夜深”,妻子亡故经年,尘灰不扫,整年的堆积,而庭院中的荒草无情,只是日夜地滋长,以物自依旧愈发衬托出人事代谢的无奈与悲痛。又如韦应物《除日》“忽惊年复新,独恨人成故”、《对芳树》“对此伤人心,还如故时绿”等。
四、悼亡诗的界定
从悼亡情感来说,悼亡是深沉真切的情感流露。悼亡诗需要承载真情实感。顾炎武与妻王氏结缡五十载,在进行抗清大业的同时身边终有妾婢,而王氏无子,死后凄凉,其悼亡之作无甚内容且矫揉虚伪,徒有悼亡之名。悼亡诗需要符合现实经历。客观评价而言,无论是从写作技巧还是感人程度,元稹的悼亡诗略胜于韦应物。但“古今悼亡之作,惟韦公应物十数篇,澹缓凄楚,真切动人,不必语语沉痛,而幽忧郁堙之气,直灌输其中,诚绝调也”,而评价元稹则说“综其一生行迹,巧宦固不待言,而巧婚尤为可恶也。岂其多情哉?实多诈而已矣”。
从悼亡对象来说,悼亡诗适用于夫妻间。不论是从《葛生》《绿衣》的悼亡对象,还是从有定名之功的潘岳诗作的悼亡对象来说,悼亡诗是“夫妻间丧偶后生者哀悼亡者的诗篇”。关于悼亡中“夫妻间”的指向性,笔者认为从最早的悼亡诗《葛生》中便能证明妻悼夫的存在,此外后世许多作品中亦能看到女性视角的悼亡之作。虽然由于女性受教育的程度较低,文学史上女性悼亡诗数量较少,我们也不能将“悼亡诗”完全指向夫悼妻。对于“夫妻”的含义我们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中国式文人生来带有忧郁气质,感伤成为中国诗歌的重要内容与表现形式。诗人们以穷困的精神世界作为感伤的基础,沉重的才命之叹作为其源泉,无果的爱情追求作为其土壤,以人事代谢、王朝更迭的家国之悲为凄风,以死亡来临、末世无称的生命之惨为苦雨,用有限有情的主体浇灌无限无情的感伤之花,完成从心灵到洪荒的自我救赎。悼亡诗人们用审美的眼光审视死亡,将死亡与爱情这两大主题结合,是感伤主义的生命意识的延续,更充实了感伤的文学传统。其中体现的对人伦的浓情赞美,对幸福的无限眷恋,对生命的人文关怀,具有普世精神并为全人类所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