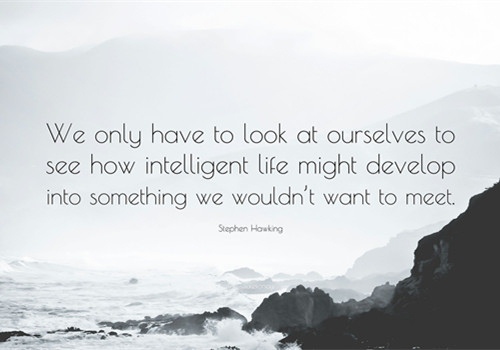我写我的“中夏夜梦”罢。有些踪迹是事后追寻,恍如梦寐,这是习见不鲜的;有些,简直当前就是不多不少的一个梦,那更不用提什么忆了。这儿所写的正是佳例之一。
在杭州住着的,都该记得阴历六月十八这一个节日罢。它比什么寒食,上巳,重九……都强,在西湖上可以看见。
杭州人士向来是那么寒乞相的;(不要见气,我不算例外。)惟有当六月十八的晚上,他们的发狂倒很像有点彻底的。(这是鲁迅君赞美蚊子的说法。)这真是佛力庇护——虽然那时班禅还没有去。
说杭州是佛地,如其是有佛的话,我不否认它配有这称号。即此地所说的六月十八,其实也是个佛节日。观世音菩萨的生日听说在六月十九,这句话从来远矣,是千真万确的了,而十八正是它的前夜。
三天竺和灵隐本来是江南的圣地,何况又恭逢这位“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的芳诞,——又用靓丽的字样了,死罪,死罪!——自然在进香者的心中,香烧得早,便越恭敬,得福越多,这所谓“烧头香”。他们默认以下的方式:
得福的多少以烧香的早晚为正比例,得福不嫌多,故烧香不怕早。一来二去,越提越早,反而晚了。(您说这多们费解。)
于是便宜了六月十八的一夜。
不知是谁的诗我忘怀了,只记得一句,可以想像从前西子湖的光景,这是“三面云山一面城”。现在打桨于湖上的,却永无缘拜识了。云山是依然,但濒湖女墙的影子哪里去了?
我们凝视东方,在白日只是成列的市廛,在黄昏只是星星的灯火,虽亦不见得丑劣;但没出息的我总会时常去默想曾有这么一带森严曲折颓败的雉堞,倒印于湖水的纹奁里。
从前既有城,即不能没有城门。滨湖之门自南而北凡三:
曰清波,曰涌金,曰钱塘,到了夜深,都要下锁的。烧香客人们既要赶得早,且要越早越好,则不得不设法飞跨这三座门。他们的妙法不是爬城,不是学鸡叫,(这多们下作而且险!)
只是隔夜赶出城。那时城外荒荒凉凉的,没有湖滨聚英,更别提西湖饭店新新旅馆之流了,于是只好作不夜之游,强颜与湖山结伴了。好在天气既大热,又是好月亮,不会得受罪的。至于放放荷灯这种把戏,都因为惯住城中的不甘清寂,才想出来的花头,未必真有什么雅趣。杭州人有了西湖,乃老躲在城里,必要被官府(关城门)佛菩萨(做生日)两重逼近着方始出来晃荡这一夜;这真是寒乞相之至了。拆了城依旧如此,我看还是惰性难除罢,不见得是彻底发泄狂气呢。
我在杭州一住五年,却只过了一个六月十八夜;暑中往往他去,不是在美国就是在北京。记得有一年上,正当六月十八的早晨我动身北去的,莹环他们却在那晚上讨了一支疲惫的划子,在湖中飘泛了半晌。据说那晚的船很破烂,游得也不畅快;但她既告我以游踪,毕竟使我愕然。
去年住在俞楼,真是躬逢其盛。是时和H君一家还同住着。H君平日兴致是极好的,他的儿女们更渴望着这佳节。年年住居城中,与湖山究不免隔膜,现在却移家湖上了。上一天先忙着到岳坟去定船。在平时泛月一度,约费杖头资四五角,现在非三元不办了。到十八下午,我们商量着去到城市买些零食,备嬉游时的咬嚼。我俩和Y.L两小姐,背着夕阳,打桨悠悠然去。
归途车上白沙堤,则流水般的车儿马儿或先或后和我们同走。其时已黄昏了。呀,湖楼附近竟成一小小的市集。楼外楼高悬着炫目的石油灯,酒人已如蚁聚。小楼上下及楼前路畔,填溢着喧哗和繁热。夹道树下的小摊儿们,啾啾唧唧在那边做买卖。如是直接于公园,行人来往,曾无闲歇。偏西一望,从岳坟的灯火,瞥见人气的浮涌,与此地一般无二。
这和平素萧萧的绿杨,寂寂的明湖大相径庭了。我不自觉的动了孩子的兴奋。
饭很不得味的匆匆吃了,马上就想坐船。——但是不巧,来了一群女客,须得尽先让她们耍子儿;我们惟有落后了。H君是好静的,主张在西泠桥畔露地憩息着,到月上了再去荡桨。我们只得答应着;而且我们也没有船,大家感着轻微的失意。
西泠桥畔依然冷冷清清的。我们坐了一会儿,听远处的箫鼓声,人的语笑都迷蒙疏阔得很,顿遭逢一种凄寂,迥异我们先前所期待的了。偶然有两三盏浮漾在湖面的'荷灯飘近我们,弟弟妹妹们便说灯来了。我瞅着那伶俜摇摆的神气,也实在可怜得很呢。后来有日本仁丹的广告船,一队一队,带着成列的红灯笼,沉填的空大鼓,火龙般的在里湖外湖间穿走着,似乎抖散了一堆寂寞。但不久映入水心的红意越宕越远越淡,我们以没有船赶它们不上,更添许多无聊。——淡黄月已在东方涌起,天和水都微明了。我们的船尚在渺茫中。
月儿渐高了,大家终于坐不住,一个一个的陆续溜回俞楼去。H君因此不高兴,也走回家。那边倒还是热闹的。看见许多灯,许多人影子,竟有归来之感,我一身尽是俗骨罢?
嚼着方才亲自买来的火腿,咸得很,乏味乏味!幸而客人们不久散尽了,船儿重系于柳下,时候虽不早,我们还得下湖去。我鼓舞起孩子的兴致来:“我们去。我们快去罢!”
红明的莲花飘流于银碧的夜波上,我们的划子追随着它们去。其实那时的荷灯已零零落落,无复方才的盛。放的灯真不少,无奈抢灯的更多。他们把灯都从波心里攫起来,摆在船上明晃晃地,方始踌躇满志而去。到烛烬灯昏时,依然是条怪蹩脚的划子,而湖面上却非常寥落;这真是杀风景。
“摇摆,上三潭印月。”
西湖的画舫不如秦淮河的美丽;只今宵一律妆点以温明的灯饰,嘹亮的声歌,在群山互拥,孤月中天,上下莹澈,四顾空灵的湖上,这样的穿梭走动,也觉别具丰致,决不弱于她的姊妹们。用老旧的比况,西湖的夏是“林下之风”,秦淮河的是“闺房之秀”。何况秦淮是夜夜如斯的;在西湖只是一年一度的美景良辰,风雨来时还不免虚度了。
公园码头上大船小船挨挤着。岸上石油灯的苍白芒角,把其他的灯姿和月色都逼得很黯淡了,我们不如别处去。我们甫下船时,远远听得那边船上正缓歌《南吕懒画眉》,等到我们船拢近来,早已歌阑人静了,这也很觉怅然。我们不如别处去。船渐渐的向三潭印月划动了。
中宵月华皎洁,是难于言说的。湖心悄且冷;四岸浮动着的歌声人语,灯火的微芒,合拢来却晕成一个繁热的光圈儿围裹着它。我们的心因此也不落于全寂,如平时夜泛的光景;只是伴着少一半的兴奋,多一半的怅惘,软软地跳动着。
灯影的历乱,波痕的皴皱,云气的奔驰,船身的动荡……一切都和心象相溶合。柔滑是入梦的惟一象征,故在当时已是不多不少的一个梦。
及至到了三潭印月,灯歌又烂漫起来,人反而倦了。停泊了一歇,绕这小洲而游,渐入荒寒境界;上面欹侧的树根,旁边披离的宿草,三个圆尖石潭,一支秃笔样的雷峰塔,尚同立于月明中。湖南没有什么灯,愈显出波寒月白;我们的眼渐渐饧涩得抬不起来了,终于摇了回去。另一划船上奏着最流行的三六,柔曼的和音依依地送我们的归船。记得从前H君有一断句是“遥灯出树明如柿”,我对了一句“倦桨投波密过饧”;虽不是今宵的眼前事,移用却也正好。我们转船,望灯火的丛中归去。
梦中行走般的上了岸,H君夫妇回湖楼去,我们还恋恋于白沙堤上尽徘徊着。楼外楼仍然上下通明,酒人尚未散尽。
路上行人三三五五,络绎不绝。我们回头再往公园方面走,泊着的灯船少了一些,但也还有五六条。其中有一船挂着招帘,灯亦特别亮,是卖凉饮及吃食的,我们上去喝了些汽水。中舱端坐着一个华妆的女郎,虽然不见得美,我们乍见,误认她也是客人,后来不知从那儿领悟出是船上的活招牌,才恍然失笑,走了。
不论如何的疲惫无聊,总得拚到东方发白才返高楼寻梦去;我们谁都是这般期待的。奈事不从人厘,H君夫妇不放心儿女们在湖上深更浪荡,毕竟来叫他们回去。顶小的一位L君临去时只咕噜着:“今儿顽得真不畅快!”但仍旧垂着头踱回去了。只剩下我们,踽踽凉凉如何是了?环又是不耐夜凉的。“我们一淘走罢!”
他们都上重楼高卧去了。我俩同凭着疏朗的水泥栏,一桁楼廊满载着月色,见方才卖凉饮的灯船复向湖心动了。活招牌式的女人必定还支撑着倦眼端坐着呢,我俩同时作此想。
叮叮当,叮叮冬,那船在西倾的圆月下响着。远了,渐渐听不真,一阵夜风过来,又是叮……当。叮……冬。
一切都和我疏阔,连自己在明月中的影子看起来也朦胧得甚于烟雾。才想转身去睡;不知怎的脚下踌躇了一步,于是箭逝的残梦俄然一顿,虽然马上又脱镞般飞驶了。这场怪短的“中夏夜梦”,我事后至今不省得如何对它。它究竟回过头瞟了我一眼才走的,我哪能怪它。喜欢它吗?不,一点不!
一九二五年四月十三日作于北京。
【作者简介】琦君,1917年7月24日生,浙江温州市瓯海区人。曾任台湾中国文化学院、中央大学中文系教授。有散文集、小说集及儿童文学作品30余种,主要著作《青灯有味似儿时》《永是有情人》《水是故乡甜》《万水千山师友情》《三更有梦书当枕》《桂花雨》《细雨灯花落》《读书与生活》《母亲的金手表》。
西湖忆旧
我生长在杭州,也曾在苏州住过短短一段时期。两处都被称为天堂,可是一样天堂,两般情味。这也许因为“钱塘苏小是乡亲”,杭州是我的第二故乡,我对它格外有一份亲切之感。平心而论,杭州风物,确胜苏州。打一个比喻,居苏州如与从名利场中退下的隐者相处,于寂寞中见深远,而年轻人久居便感单调少变化。住杭州则心灵有多种感受。由湖似明眸皓齿的佳人,令人满怀喜悦。古寺名塔似遗世独立的高人逸士,引人发思古幽情。何况秋月春花,四时风光无限,湖山有幸,灵秀独钟。可惜我当时年少春衫薄,把天堂中岁月,等闲过了。莫说旧游似梦,怕的是年事渐长,灵心迟钝,连梦都将梦不到了。因此我要从既清晰亦朦胧的梦境中,追忆点滴往事,以为来日的印证。若他年重回西湖,孤山梅鹤,是否还认得白发故人呢?
居近湖滨归钓迟
我的家在旗下营一条闹中取静的街道上。街名花市路,后因纪念宋教仁改名教仁街。这条路全长不及三公里,而被一条浣纱溪隔为两段,溪的东边环境清幽。东西浣沙路两岸桃柳缤纷,溪流清澈。过小溪行数百步便是湖滨公园。入夜灯火辉煌,行人如织。先父卜居于此,就为了可以朝夕饱览湖光山色之胜。他曾有两句咏寓所的诗:“门临花市占春早,居近湖滨归钓迟。”父亲不谙钓鱼之术,却极爱钓鱼。春日的傍晚,尤其是微雨天,他就带我打着伞,提着小木桶,走向湖滨,雇一只小船,荡到湖边僻静之处,垂下钓线,然后点起一支烟,慢慢儿喷着,望着水面微微牵动的浮沉子而笑。他说钓鱼不是为了要获得鱼,只是享受那一份耐心等待中的快乐。他仿着陶渊明的口吻说:“但识静中趣,何须鱼上钓。”他曾随口吟了两句诗:“不钓浮名不约愁,轻风细内六桥舟。”我马上接着打油道:“归来莫笑空空桶,洒满清樽月满楼。”父亲拍手说“好”,我也就大大地得意起来。
夏夜,由断桥上了垂柳桃花相间的白公堤,缓步行去,就到了平潮秋月。凭着栏杆,可以享受清凉的湖水湖风,可以远
六月十八是荷花生日,湖上放起荷花灯,杭州人名之谓“落夜湖”。这一晚,船价大涨,无论谁都乐于被巧笑倩兮的船娘“刨”一次“黄瓜儿”。十八夜的月亮虽已不太圆,却显得分外明亮。湖面上朵朵粉红色的荷花灯,随着摇荡的碧波,飘浮在摇荡的风荷之间,红绿相间。把小小船儿摇进荷叶丛中,头顶上绿云微动,清香的湖风轻柔地吹拂着面颊。耳中听远处笙歌,抬眼望天空的淡月疏星。此时,你真不知道白己是在天上还是人间。如果是无月无灯的夜晚,十里宽的湖面,郁沉沉的,便有一片烟水苍茫之感。
圆荷滴露寄相思
荷花是如此高尚的一种花,宋朝周濂溪赞它出污泥而不染。它的每一部分又都可以吃。有如一位隐士,有出尘的高格,又有济世的胸怀。所以吃莲花也不可认为是煞风景的俗客,而调冰雪藕,更是文人们暑天的韵事。新剥莲蓬,清香可门,莲心可以泡茶,清心养目,莲梗可以作药。诗人还想拿藕丝制衣服。有诗云:“自制藕丝衫子薄,为怜辛苦赦春蚕。”如果真有藕丝衫,一定比现代的什么“龙”都柔软凉爽呢。倒是荷衣确是隐者之服,词人说:“新着荷衣人未识,年年江海客。”我想只要能泛小舟徜徉于荷花丛中,也就是远离烦
写至此,我却想起了荷花中的一段故事:那一年仲夏,我陪着从远道归来的姑丈,和见了他就一往情深的云,三人荡舟湖上。从傍晚直至深夜,大家都默默地很少说话。小几上堆了刚出水的红菱,还带着绿色茎叶,云为我们—一地剥着红菱。她细白如兰的手指尖,与鲜嫩的红菱相映成趣。船儿在圆圆的荷叶之间穿来穿去,波光荡漾中,云娇媚的面容有如初绽的红莲。她摘下一片荷叶,漂在水面,水珠儿纷纷滚动在碧绿的丝绒上。我伸手上捉时,它们就顽皮地从手指缝中溜跑了。云说:“谁能捉住水珠呢?”姑丈说:“找们不就像这些水珠吗?”她深湛的眼神注视了他半晌,低下头微喟一声,没有再说什么。沉默的空气重重地压着我的心,想想他们这一段无可奈何的爱,将如何了结呢?云捡起一片藕,双手折断,藕丝牵得长长的。在细细的风中飘着。她凝视一问,把藕扔在水中。藕丝是否还连着,我就看不清楚了,只看见云的眼中满是泪水。
对岸五彩霓虹灯在闪烁,岸边的世界依旧
我们舍舟登岸,从湖堤归来,三人并肩走在柏油马路上。尽管荷香阵阵,湖水清凉,我的心却十分沉重,相信他们的心比我更重。姑丈忽然拍拍我的肩说:“希望你不要去捉荷叶上的水珠,那是永远捉不住的。”他这话是对我说的吗?
桂花香里
中秋前后,满觉陇桂花盛开。在桂林中散步,脚下踩的是一片黄金色的桂花,像地毯,软绵绵的,一定比西方极乐世界的金沙铺地更舒适!浓郁的桂花香,格外亲切。我那时正读过郁达夫的小说《迟桂花》,文人笔下的哀伤,也深深感染了我。仿佛那可爱的女孩,正从桂花中冉冉而来。
桂花林中还产一种嫩栗,剥出来一粒粒都带桂花香。满觉陇一路上都有小竹棚,专卖白莲藕粉票子羹。走累了,坐下来喝一碗票子羹,顿觉精神饱满,齿颊留芬。母亲拿手的点心是桂花枣泥糕,所以趁每回远足满觉陇,都要捧一大包撒落的桂花回来,供她做糕。留一部分晒干和入雨前清茶中,更是清香可口。
不知何故,桂花最引我乡愁。在台湾很少闻到桂花香,可是乡愁却更浓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