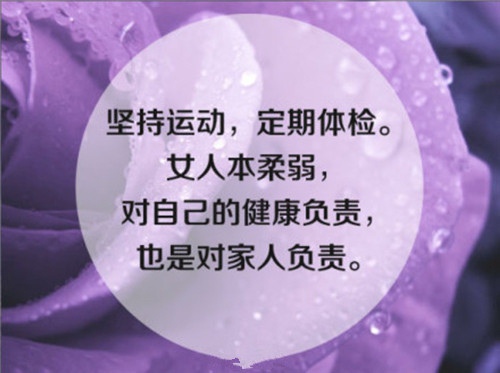关于“慎独”的名言10条
相传古时贤者编了《不可录》一书,记载了淫欲之害、戒淫格言以及福善祸淫的实例,详细而有条理地分析和陈述了持戒的方法、日期以及其中的忌讳,以警世人。
后来印光大师将《不可录》加以增补修订,并取名为《寿康宝鉴》,再为这本书募捐印刷、令其广泛流通。
印光大师是大势至菩萨再来。
推荐一些最值得一读的佛经
佛精髓即:佛教的一心在佛教有许多名字:真自性、法身、实相、佛性、法性、藏、圆成实性、本来面目、本地风光、大圆镜智等。
心的真谛不可思议,不可思即禅宗的“动念即乖、心行处灭”,不可议即禅宗的“开口便错、言语道断”。
在此,只好引用莲池大师的话作一个牵强的比喻:“心是无形相的,所以没有任何东西可作为比喻。
大凡用来比喻心的,都是不得已,姑且取其仿佛与心的作用有些近似的东西来形容它,使人对于心的概念多少有所领会,但不可以认为心当真如某种东西。
试举一例,譬如以镜子比喻心,大家都知道镜能照物,当物还没有对着镜子的时候,镜子不会把物的影像摄入镜中;当物正对着镜子的时候,镜子不会因为物的好恶美丑而生憎爱;当物离开镜子的时候,镜子也不会把物的影像保留在镜子里。
圣人的心常寂常照,寂则一尘不染,照则遍觉十方。
此心既不住内,不住外,不住中间,三际空寂,而又无所不住,无物不照。
所以用镜子来比喻心,只是取其某些略似而已。
究极而论,镜子毕竟是一种没有知觉的物体,心难道也象镜子那样无知吗
而且镜子在黑暗中便失去作用,怎能比得上心的妙明真体常寂常照。
以此类推,或以宝珠喻心,或以虚空喻心,无论用哪一种比喻,其道理都是一样的。
只有苦没有生命救缘分尽了是不是就只有苦了
民族英雄——林则徐林则徐,字元抚,又字少穆、石麟,晚号俟村老人,谥“文忠”,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民族英雄,禁烟运动的杰出先驱,鸦片战争时著名的抵抗派领袖。
稍微熟悉近代史者,无不被其爱国精神所感动。
少为人知的是,在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样的大无畏精神背后,有着“众生无边誓愿度”的佛教愿力作为支撑与贯注。
林则徐之信仰佛教,尤其倾心于净土法门,在佛教界也算是为人所津津乐道的佳话美谈了。
早在青年时代,林公就笃信佛教。
嘉庆十二年(一八○七年)二十三岁时,即手书《佛说阿弥陀经》、《金刚经般若波罗蜜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和《大悲咒》、《往生咒》五种经咒,共贮一函,上题“行舆日课”、“净土资粮”八字,作为每日必诵的功课。
其经本只有四寸多长、三寸多宽,每面六行,每行十二字,以便于随身携带。
所写经咒,字迹工楷,一笔不苟,足见其对佛教的虔诚和恭敬,林公逝世后,其后人合订为一册,题为《林文忠公手书经咒日课》。
林公除在日理万机和戎马倥偬中,坚持“行舆日课”,不废诵经念佛外,在《林则徐日记》中还可以查找到不少供佛礼佛、求佛祈雨、写经赠友、忌日持斋、参拜佛寺的记述。
嘉庆二十四年(一八一九年)七月,林公赴云南任考官,路过贵州黄平州飞云岩,岩上有观音大士立象,林公立即下车合十参拜诵经,在七古《飞云岩》中有句云:“中有古佛立亭亭,苾刍合十朝诵经。
催落山泉作钟磬,秋色满岩云有声。
”道光十年(一八三○年)六月,有七律《次韵酬潘星斋莹见怀之作》,中有句云:“懒吟回避债,倦客且参禅。
”表明林公宁愿趺坐参禅而不愿会见众多的俗客。
道光二十九年(一八四九年)秋,林公在云贵总督任内,以频年积劳。
旧疾复发,奏请开缺回籍调理,已蒙恩准。
因宦海浮沉多年,深感仕途险恶,加之相依为命的郑夫人于上年十月病逝于昆明,他本人年迈多病,因而萌发了看破红尘,归隐寺院的意向。
离滇前有《袁午桥礼部甲三闻余乞疾寄赠,依韵答之》七律三首,其中一首云:身似闲僧退院初,维摩丈室暗踟躇。
养病只合颓然卧,怀旧真惭迹也疏。
但得支公怜病鹤,肯同赵壹赋枯鱼。
愿君早拥南天节,或许相逢退食余。
此诗首联,林公把自己比为“退院”(即却去方丈等领导职务)初期的“闲僧”、“维摩”即摩诘菩萨名,林公在书斋中供佛或挂有菩萨画像,故称“维摩丈室”。
第三联的“支公”即东晋著名高僧支遁,曾养鹤,“病鹤”为林公自喻。
《枯鱼赋》典出《南史。
文学传。
卞彬》传因屡以直言忤帝,虽有才干仍被署数年不得仕进,乃做赵壹《穷鸟》作《枯鱼赋》,自伤不遇。
林公这两句诗表明其心迹中:只要有某位高僧大德发慈悲心,怜其病衰,愿意引渡,他宁可追随遁入空门,也决不肯再像赵壹、卞彬那样衷仕途了。
在诸佛菩萨中,林公最崇敬的是观音大士,除多次向大士行香、祈雨外,道光十八戊戌(公元1838年),在担任湖广总督期间,还在督署内建了观音庙,每日行香设供。
在《戊戌日记》中,即有诣署中大士前行香,“大士神诞,黎明诣本署庙内设供行香”的记述。
此外,林公担任江苏巡抚时,还为苏州观音庙题写了一副充满佛性的对联,联云:大慈悲能布福田,曰雨而雨,曰旸而旸,祝率土丰穰,长使众生蒙乐利;诸善信愿登觉岸,说法非法,说相非相,学普门功德,只凭片念起修行。
此联颇能反映出林公慈悲济世的佛化心襟。
林则徐的曾孙曾把林则徐亲笔书写的《阿弥陀经》等课诵本拿给印光大师看。
《文钞》中载说:一日文忠公曾孙翔,字璧予者,以公亲书之《弥陀》《金刚》《心经》《大悲》《往生》各经咒之梵册课本见示。
其卷面题曰“净土资粮”,其匣面题曰“行舆日课”。
大师赞说:其字恭楷,一笔不苟。
足见其恭敬至诚,不敢稍涉疏忽也。
印光大师对林则徐的成就功绩以及其虔心净土,做了很高的评价:林文忠公则徐,其学问、智识、志节、忠义,为前清一代所仅见。
虽政事冗繁,而修持净业,不稍间断。
以学佛,乃学问、志节、忠义之根本。
大师还说:“详观古之大忠大孝,建大功,立大业,道济当时,德被后世,浩气塞天地,精忠贯日月者,皆由学佛得力而来。
”鸦片战争前夕,林则徐针对世风日下的时弊,于1839年9月巡视澳门后,在前山写了“十无益”格言:存心不善,风水无益;父母不孝,奉视无益;兄弟不和,交友无益;行止不端,读书无益;作事乖张,聪明无益;心高气傲,博学无益;为富不仁,积聚无益;巧取人财,布施无益;不惜元气,服药无益。
淫逸骄奢,仕途无益。
这“十无益”格言对现代人仍然有深刻的教育和鞭策意义。
金安清《林文忠公传》记载:“公易箦时,以指向天,呼星斗南三字。
”即林则徐在弥留之际以手指天,大呼“星斗南”三字。
星斗南是人
还是物
亦或是林则徐想要抒发的某种情感
他到底想告诉我们什么呢
其后的谜团直至百年后的今天仍未能被参透。
下面我们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提供三种猜测。
林则徐笃信佛教,是一位虔诚的佛门弟子,早在青年时代,就恭恭敬敬的誊抄《心经》、《金刚经》、《大悲咒》等,并亲题“行舆日课”、“净土资粮”八个字,贮于一匣,随身携带,便于诵读。
从政后,林则徐仍坚持“日课”,不忘诵经念佛。
因此便有人猜测,林则徐在行将与世诀别的时刻,心生佛念才最符合当时情境,所以林则徐去世前喊的,很可能不是“星斗南”,而是“心大南”(心即《心经》和《金刚经》;大即《大悲咒》;南即念佛声如“南无阿弥陀佛”等),是诵经念佛的简称。
意思是,希望儿子代替自己完成“日课”,往生净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