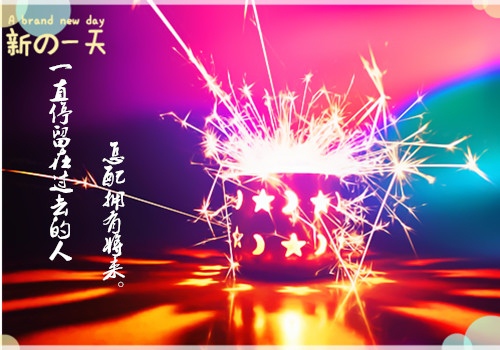清新文艺的句子
1 埋下一座关了所有灯。
2 你的夕阳、我的容颜、谁的三分之。
3 摇曳在笔尖的、是聚光灯下最浓烈的一抹艳红。
4 我目送沿海的日落、紧抱一个醉生梦死的枕头、游不出回忆却学不会放手、怎么走。
5 用一根火柴烧一座蜃楼、借这场大雨让自己逃走。
6 躲在万劫不复的街头、微笑参透覆水难收。
7 睫毛下的伤城路过了谁的风景谁的心。
8 当掉的浅色寂语、你开了一家收购店、等来了遗忘的海角天光。
9 女巫亲吻过的咒语破天而来、浇湿的誓言漉漉退场、我坐在海上补一张网、你伏在海底披星戴月的歌 唱。
10 等一个人、还是等一个故事。
11 泅渡一个世界、共一场生死。
12 那首关于我们的歌、你把结局唱给了谁听。
13 你掌心华丽的情色线条纠结进了谁的城池里欢声笑语。
14 把爱写成兵临城下的不朽传奇、那么、你会不会不辞冰雪披荆斩棘地奔赴而来。
15 把我们的故事刻在被风化的山墙上、路人看到的时候哭了。
16 你是谁朝思暮想的笔尖少年、在绝城的荒途里辗转成歌。
17 用一千年的时间去爱你、再用一万年的时间去忘记。
18 谁眼角朱红的泪痣成全了你的繁华一世、你金戈铁马的江山赠与谁一场石破惊天的空欢喜。
19 下一世的情歌、把词交由你填、看看你仍旧是谁高高在上的王。
20 橱窗里盛放的琳琅满目、是阜盛而过的年华栩栩生辉。
21 那首情歌有关风月、却无关你我。
22 戏子入画、一生天涯。
23 如花美眷 也敌不过似水流年。
26 绘一场生死契阔的游戏、为我们的故事写一个结局。
24 路过的风景、有没有人为你好好收藏。
25 我在漫天风雪的回忆里披荆斩棘、你却在哪一个的字典里演绎皈依。
26 绘一场生死契阔的游戏、为我们的故事写一个结局。
27 爱尔兰雪、土耳其蓝、莫斯科眼泪。
我都收藏在小小的太阳里、还有晴天和微笑。
波斯湾海、维也纳厅、阿拉伯传说。
我都纪念在厚厚的相集里。
还有七粉和公主。
28 把悲伤掩饰得天衣无缝。
29 为谁唱离歌、对谁说情话、给谁写天涯。
30 谁用微笑假装自己不悲伤。
31 把醉了的明天寄托在潘多拉的琴弦、浮沉余生虚伪地歌咏天上人间。
32 是宿命的悲、还是轮回的痛。
33 辗转在谁的年华谁的天涯。
34 那一场盛世流年、我们守着寂寞伤得面目全非。
35 寂寞这么多、在承受的有几个。
36 谁把谁的明媚尽收眼底、谁把谁的难过感同身受。
37 我有没有跟你说过爱是我不变的信仰、我有没有告诉过你爱就是永远把一个人放在心上。
38 喜欢的歌、静静地听。
喜欢的人、远远的看。
39 过程和结局都有了、再去纠缠、连自己都觉得贪婪。
40 悲伤自找的,幸福是你给的。
41 怕冷的女子,心一定是凉的。
42 守住的是仓皇而班驳的灾难、是用整个生命也敌不过的假象。
43 只身步步海天涯、路无归、霜满颜。
44 如果有一双眼睛为我流泪、我愿意再次相信这个悲凉的人生。
45 星星的故事、是陪你走在人海里、却不会让你走丢。
46 舌间搁浅的妙蔓、是想为你舞一曲最后倾国倾城。
47 夜微凉、灯微暗、暧昧散尽、笙歌婉转。
48 繁杂的经历在眼角镌刻深深的纹、我转身雕下一朵花。
49 我徒手唱歌、你弹奏的肖邦、却盲了我的眼。
50 我流浪了那么久、还不想回家、因为你不在家、我便永远没有家。
51 那些纠缠到深夜里的流言蜚语我不怕让你听到、也不怕让全世界听到。
我是怕你听到了、并相信。
52 只要心中有景、何处不是花香满径。
53 那些上演着繁华不肯谢幕的年华里开出一朵地老天荒的花。
54 来生我再来典当、来世我再来与你歃血为盟。
55 爱你、给你我生命所有的美好、然后退场、让万花筒灿烂你的眼瞳。
56 蔷薇开出的花朵没有芬芳、想念一个人、怀念一段伤、不流泪、不说话。
57 幸福右边、荒芜人烟。
58 始终在做着重复的两件事、爱他以及守护。
59 嘘、我的伤才刚刚睡着。
60 只为他放弃一座城池、在天光大亮的时候、奔赴一场或生或死的未知。
61 我想看一场盛大的流行陨落的过程、我要一直不停许愿、许到沧海桑田瞬息万变直到靠近你微笑淡晴的脸。
62 错过的年华在北漠开出斑斓的紫薇花、却荒芜了轮回的春夏。
63 你走过多少条街、会想起多少次我呢。
64 一再的隐忍,一再的退让,却换来了盛宴上的谎言。
65 曾听人说,回忆是一座桥,却是通向寂寞的牢。
66 我把所有的伤心走一遍,最伤心的是你不在终点。
我把所有的绝望走一遍,最绝望的是你还在起点。
67 这年头,谁不是带着一箱子的面具走天涯
68 我只是难过不能陪你一起老,再也没有机会,看到你的笑。
69 你我形同陌路,相遇也是恩泽一场。
70 我祈望,在某个风光明媚的街角,我遇见你,然后遇见我自己...
形容文化人的句子
1、胸无:肚子里没有一点墨水指人没有文化。
2、蹶角受化:蹶角:叩头;受化:文化。
原指四方夷族和外国人来中国朝贡,接受教化。
形容声威极大。
3、知文达理:知、达:懂得。
有文化,讲道理。
形容有教养。
4、雅俗共赏:形容某些文艺作品既优美,又通俗,各种文化程度的人都能够欣赏。
5、美雨欧风:欧:欧洲。
比喻来自欧美的思想文化等方面的侵袭。
6、用夏变夷:夏,诸夏,古代中原地区周王朝所分封的各诸侯国;夷,指中原地区以外的各族。
以诸夏文化影响中原地区以外的僻远部族。
7、胸中无墨:胸中没有墨水。
比喻人没有学问,文化水平低。
8、卖弄才学:指故意显示自己有文化水平。
9、一穷二白:穷:指物质基础差;白:指文化和科学落后。
比喻基础差,底子薄。
10、兼收并蓄:把不同内容、不同性质的东西收下来,保存起来。
11、黄金时代:指人一生中最为宝贵的时期。
也指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最繁荣的时期。
12、识字知书:指有文化知识。
60年代生的人过的苦不苦?
你说的 是中国人吗
1958年和1959年都饿死那么多人了,到处移民流浪,60年代过的也不会好到哪里去啊。
为什么80年代被称作文艺复兴的年代,这期间文学有什么代表人物?
80年代文学概况 一 过程:80年代前期 1976年底“文革”结束后的一段时间,文学并未在较大的范围里实现从“文革文学”的转变。
写作者的文学观念、取材和艺术方法,仍是“文革文学”的沿袭。
出现对于“文革”模式的明显脱离,是从1979年开始。
因此,不少批评家在谈到“新时期”文学的开端时,并不以“文革”结束作为界限。
(注:如朱寨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指出,他们把“当代文学思潮史”的下限划在1979年,而不是划在“粉碎‘四人帮’的1976年”,原因是1979年以前,“文艺思想并没有从根本上解除禁锢”;“文艺思想上的拨乱反正,文艺创作有了新的突破”,是在1978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开始。
而“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第四次全国文代会,成为文艺史上转折的里程碑”。
《中国当代文学思想史》第8-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
)当然,在此之前,已有一些作品预示了这种“转变”的发生。
如发表于1977年11月的短篇小说《班主任》(刘心武)和发表于1978年8月的短篇《伤痕》(卢新华)(注:分别刊载于1977年第11期《人民文学》和1978年8月11日《文汇报》(上海)。
)。
这些艺术上显得粗糙的作品,提示了文学“解冻”的一些重要特征:对个人的命运、情感创伤的关注,和作家对于“主体意识”的寻找的自觉。
以1985年前后为界,80年代文学可以区分为两个阶段。
80年代前期,文学界和思想文化界存在着相当集中的关注点。
刚刚过去的“文革”,在当时被广泛看作是“封建专制主义”的“肆虐”。
因此,挣脱“文化专制”的枷锁,更新全民族观念的“文化启蒙”(“新启蒙”),是思想文化的“主潮”。
与此相关,文学是对于“现实主义”的“传统”的呼唤。
在这几年间,文学主题可以说都与“文革”的“历史记忆”有关,是亲历者对“历史灾难”所提供的“证言”,以及对于“历史责任”(“谁之罪”)所作的思考和探究。
在小说创作上,出现了“伤痕小说”和“反思小说”的潮流;诗歌创作的主要构成,则是“复出诗人”的“归来的歌”,和青年诗人的“朦胧诗”创作;戏剧,特别是话剧也大多是与“文革”有关的“社会问题剧”。
已经在酝酿着艺术观念和方法上的更为深入的变革,但还未成为显在的、受到普遍关注的现象。
从总体而言,这几年文学的取材和主题,是指向社会一政治层面的,也大多具有社会—政治的“干预”性质。
涉及的问题,表达的情绪,与社会各阶层的思考与情绪同步。
文学创作与社会政治、与公众的生活和情感的密切关系,是后来不再重视、并为一些人怀恋的“昔日的光荣”。
由于“文革”被看作是中国现代文艺史的“最黑暗的一页”,文艺的“园地”受到严重摧残而“百花凋零”,因此,“新时期文学”被看作是“文学复兴”,“复兴”的提出,又通常与“五四”文学相联系,看成是对“五四”的“复归”。
在80年代初,人们最为向往的,是他们心目中“五四”文学的那种自由的、“多元共生”局面。
但从80年代前期的中心问题看,所要“复活”的,主要是“五四”提倡“科学、民主”的启蒙精神,和以“五四”为旗帜的、在50至70年代被当作“异端”批判的文学思潮。
许多批评家和作家的努力,是继续四五十年代胡风、冯雪峰、秦兆阳(也包括周扬等在60年代)以悲剧结局告终的工作。
一方面,在承认文学的“革命”性质的前提下,推动文学挣脱图解政治概念、复制社会生活表象和僵化艺术模式控制的状况;另一方面,在维护文学作为“艺术”的“特质”,和重视文学社会承担、批判职能,倡导作家的“启蒙”精神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和结合。
对“写真实”和“现实主义”的重申和坚持,公开发表周恩来、陈毅60年代初关于文艺政策“调整”的讲话(注:周恩来《在文艺工作者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1961年6月19日),陈毅《在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1962年3月6日)等。
),为50年代以来受到批判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秦兆阳)等文章的观点辩护,对“文艺为政治服务”的质疑,都说明了推动“新时期”文学“复兴”的人们,最初继续的是五六十年代“未竟”的工作,接过的是他们的旗帜(注:见《文艺报》1979年3月召开的文艺理论批评工作座谈会上,作家、批评家的发言,《文艺报》1979年第4期《总结经验,把文艺理论批评工作搞上去》。
)。
1979年4月,《上海文学》评论员文章(《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注:当时文艺界对这篇文章反响热烈,《上海文学》等刊物还组织了有较大规模的讨论。
),对于这一在中国左翼文学界长期流传的“根本性”观念的质疑,也是在左翼文学观的框架内,来反对把文艺变成单纯的政治传声筒,而寻求不离开文艺“特性”的文艺的政治功用:它申明的是左翼文学中受压抑的派别(胡风、冯雪峰、秦兆阳等)的思想路线。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新时期”开端所处理的问题,展开的论争,是五六十年代,或更早时间发生于左翼文学的“陈旧”话题,或这些话题的延伸。
这包括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写真实”,“现代派”文学,人性和人道主义等。
在80年代初与文学有关的思想理论问题的论争中,周扬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问题的探讨》(注:刊发于1983年3月16日《人民日报》。
据王元化《为周扬起草文章始末》(广州《南方周末》1997年12月12日)称,在周扬与王元化、王若水、顾骧一起讨论后,由王元化、王若水、顾骧起草。
王元化主要撰写有关重视认识论问题的部分,王若水撰写有关人道主义部分。
在此之前,王元化已就认识论和知性方法的问题,发表过文章(刊发于1979年上海《学术月刊》和1981年《上海文学》上的《论知性的分析方法》等)。
王若水在这一时期,也撰写了多篇论人道主义的文章。
最著名的是《为人道主义辩护》(上海《文汇报》1983年1月17日)。
周扬的文章由王元化定稿,周扬作最后润色,并由周扬于1983年3月7日,在中共中央党校召开的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学术报告会上演讲。
)是重要的、产生很大争议的文章。
文章试图清算几十年来中国“左”的政治思想路线的哲学根源,来推动思想解放的深化。
它的影响与其说是在理论上的,不如说更主要是现实问题的针对性上的。
它指出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学说,批评了“终极真理”的观点。
提出在认识论上考虑用感性、知性、理性的三范畴,去代替感性和理性的两范畴,以划分知性与理性的区别;认为知性和理性相混淆,以为一旦形成概念,就掌握了本质,是导致简单化、概念化的根源。
文章提出的另一重要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
文章不同意把马克思主义全部归结为人道主义,但认为马克思主义包含人道主义。
在阐释马克思早期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它是80年代前期“思想解放运动”思潮中的主要理论依据之一)的“异化”概念时,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理想中的人类解放,不仅是从剥削制度下的解放,而且是从一切异化形式束缚下的解放。
文章引出的最大“麻烦”,是认为不仅是资本主义,而且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也存在“异化”,包括经济领域的异化,政治领域的异化(权力异化)和思想领域的异化(个人崇拜,或宗教异化)。
这篇文章既得到热烈支持,也很快受到激烈批评(注:在周扬发表讲话后,本来定于3月9日结束的“学术报告会”突然决定延期,并开始对讲话的观点进行批评。
3月16日,《人民日报》在发表周扬讲话时,同时刊发会上对这一讲话的批评发言:《黄楠森等在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学术报告会上的发言摘要》。
)。
对周扬文章系统的、最具权威性的批评,由胡乔木在《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注:这是胡乔木1984年1月3日在中共中央党校的讲话。
经修改后刊于《红旗》1984年第2期。
)一文中进行,指出“宣传人道主义世界观、历史观和社会主义异化论的”“带有根本性质错误的”思潮,不是一般的学术理论问题,而“牵涉到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诱发对社会主义的不信任情绪”的问题。
随后,周扬做了公开的自我批评(注:1983年11月,周扬在对新华社记者谈话中作了自我批评。
在11月中国文联召开的座谈会上说,“我在今年3月份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报告会上发表了那样一篇有缺点、错误的文章。
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参见《文艺报》1983年第12期。
)。
1983年至1984年间开展的抵制和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文学问题和现象被作为“精神污染”列举的事项,除了周扬等的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观点外,还包括:“把西方‘现代派’作为我国文艺发展的方向和道路”,创作上“热衷于表现抽象的人性和人道主义”,“渲染各种悲观、失望孤独、恐惧的阴暗心理”,“把‘表现自我’当成惟一的和最高的目的”等等。
(注:参见1983年第11期《文艺报》社论和12期座谈会报道。
) 二 过程:80年代后期 80年代文学在走过一段路程之后,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
80年代的文学主题,作家的基本构成,文学的接受和流通方式等等,在主要的方面仍在延续,但也出现了新的因素。
这种“变化”,可以理解为文学创作和理论的某些方面,已经超越五六十年代中国左翼文学的“话题”的范围,创作的风貌脱离了较为单一的模式,艺术方法的探索和革新以更大的步伐推进,而文学与读者的关系,也变得远为复杂。
在80年代中期或稍后,“文革”后一度享誉的“复出”作家、诗人,有的创作仍获取新的进展,而许多人则已越过自己创作“高峰”。
在面对文学观念、方法变革的巨大压力下,缺乏调整自己步调的潜力,或者显得迟滞,或者新作日见减少。
“朦胧诗”的作者也大多走过他们的鼎盛期,80年代初大量涌现的青年诗人,到80年代中期以后仍保持活跃姿态的,并不是很多。
有的“知青”小说家的创作也出现了停滞状态。
显然,当代作家和作品的“生命力”普遍短暂的问题,在80年代并没有成为历史。
为文学写作所作的准备的不足,和开放之后文学潮流急遽的变化,使作家的更替出现超出一般时期的速度。
当然,各种“类型”作家中,都存在沉稳而坚实者,尤其是被称为“知青作家”中的一部分。
他们和更年轻的作者一起,构成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文学创作的“中坚力量”。
80年代中期文学的变化,因1985年这一年发生的许多事件,使这一年份成为一些批评家所认定的文学“转折”的“标志”。
对“文革”和当代历史的书写仍为许多作家所直接或间接关注,但一批与“伤痕”、“反思”小说在思想艺术形态上不同的作品已经出现。
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张辛欣、桑晔的《北京人》,史铁生的《命若琴弦》,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王安忆的《小鲍庄》,陈村的《少男少女,一共七个》,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韩少功的《爸爸爸》,残雪的《山上的小屋》,扎西达娃的《系在皮绳扣上的魂》等,均发表于这一年(注:马原等的这些小说,分别刊于1995年的《上海文学》第2期、《上海文学》第1、7期、《现代人》第2期、《人民文学》第3期、《中国作家》第2期、《文学月报》1985年第5期、《中国作家》第2期、《人民文学》第6期、《人民文学》第8期、《西藏文学》第1期。
)。
对于长期习惯于确定的主题意向和“写实”的表现方法的读者和批评家来说,它们令人耳目一新,也因此引起阐释和评价上的分歧。
这些作品的主要部分,表现了似乎正相反对的倾向,并在创作成果上昭示了发生于这一年的两个重要的文学潮流。
一是所谓文学的“寻根”,和由此产生的“寻根文学”。
另一是“现代派”的文学潮流。
前者由一批青年作家发动,其主旨在于突出文学存在的“文化”意义(对抗文学作为社会政治观念的载体),试图从传统文化心理、性格上推进“反思文学”的深化,并发掘、重构民族文化精神,以此作为文学发展的根基。
当时被指认为“现代派”文学的,有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蓝天绿海》,徐星的《无主题变奏》,残雪、陈村、韩少功的一些小说。
这是因为它们有着和西方“现代派”文学相似的主题:表现对于世界的荒谬感,写人的孤独,有的又有“反文化”、“反崇高”的意味,且常用象征、意识流、“黑色幽默”等艺术方法。
文学“寻根”引起了争论,“现代派”文学也同样。
和几年前的争论相比,这次对“现代派的”争论,提出问题的方式虽没有很大的不同,但批评者和支持者意见本身,却已发生分裂。
热烈赞扬这些作品的,有的认为中国当代终于有了自己的“现代派”,这是文学观念和审美意识的创新;有的则指出这些小说的核心是表现时代的进步,“而不是精神的颓废”,在“荒诞”、“魔幻”的外衣下是“现实主义的真实性”。
在批评的意见中,违背了社会主义文学的原则,是文学的“堕落”的严厉指责依然存在;但又出现了这些作品还不够“现代派”(以西方某些“现代派”文本为标尺),而有了“伪现代派”的谑称(注:参见黄子平《关于“伪现代派”及其批评》(《北京文学》1988年第2期),李陀《也谈“伪现代派”及其批评》(《北京文学》1988年第4期)等文章。
)。
1985年或更早一点时间,“朦胧诗”已经“式微”。
除了杨炼、顾城还不断有新作问世外,其他作者的作品日见减少。
与此同时,出现了更多的被称为“新生代”的诗歌写作者。
他们不仅反叛当代的诗歌“传统”、而且揭起超越、“反叛”“朦胧诗”的旗帜。
他们组织了名目繁多的,存在或不存在的诗歌社团。
比起其他的文学样式来,“新生代”诗歌的“实验”要更大胆、激进;加上诗歌界由于观念等的歧异所形成的严重分裂,他们的诗一般难以得到“主流”诗界的承认,在正式报刊上发表的机会也不多。
自编、自印诗报、诗刊、诗集,是作品“发表”的主要方式。
(注:据1986年9月30日《深圳青年报》对“现代诗群体大展”的预告(徐敬亚执笔)称:1986年,“全国二千多家诗社和千倍百倍于此数字的自谓诗人,以成千上万的诗集、诗报、诗刊与传统实行着决裂”,“至1986年7月,全国已出的非正式打印诗集达905种,不定期的打印诗刊70种,非正式发行的铅印诗刊和诗报22种。
”这则消息没有提供上述数字来源的说明。
)为显示“新生代”诗的实绩,1986年的九十月间,《诗歌报》(安徽合肥)和《深圳青年报》联合举办了“现代诗群体大展”,先后用九个整版的篇幅,刊登几十家“诗派”(“诗社”)的宣言,代表诗人的简历和代表作。
在这些“诗派”、诗人之中,既有许多真诚的艺术探索者,也不乏“闹剧”的热衷者;“大展”的策划者清楚这一点,但并不在意,因为“挑战性”的展示,是他们主要的意图。
(注:“大展”的主要策划者徐敬亚在“大展”的《编后》(《深圳青年报》1986年10月24日)中写道,“在正式的报刊上,人们就是不能看到诗坛探索的全部真实,漠视、片面、歪曲——已远非个人性习惯”。
“大展”材料在报纸刊出后,由徐敬亚、孟浪、曹长青、吕贵品调整、补充,编为《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1986-1988)》,由同济大学出版社(上海)1988年出版。
) 在80年代中期,理论批评的变化也值得重视。
虽说这期间对文学批评的“科学方法”(强调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方法对文学研究的渗透)的重视异乎寻常且最引人瞩目(1985年也因此被称为文艺学的“方法年”),但改变理论批评界的面貌和格局的,是一批中青年批评家和研究者的出现。
有异于上一代批评家的知识背景,尤其是生命体验在批评中的融入,建设起他们批评的个性品格和思想深度。
(注:浙江文艺出版社的“新人文论”丛书,和上海文艺出版社的“文艺探索书系”,出版了这些中青年批评家的专集。
列入“新人文论”的主要有:吴亮《文学的选择》,程德培《小说家的世界》,许子东《郁达夫新论》,季红真《文明与愚昧的冲突》,周政保《小说与诗的艺术》,刘纳《论“五四”新文学》,黄子平《沉思的老树的精灵》,南帆《理解与感悟》,赵园《论小说十家》,蔡翔《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精神漫游》,王富仁《先驱者的形象》,陈平原《在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中》,蓝棣之《正统的与异端的》,王晓明《所罗门的瓶子》,陈思和《批评与想像》,李劼《个性
自我
创造》等。
“文艺探索书系的理论部分,出版了刘再复《性格组合论》、赵园《艰难的选择》、鲁枢元《文艺心理阐释》、夏中义《艺术链》、钱理群《心灵的探寻》、宋耀良《十年文学主潮》等批评论著。
)在这一年,刘再复发表了引起争论的《论文学主体性》(注:刊于《文学评论》(北京)1985年第6期和1986年第1期。
)的长文。
他以人道主义作为理论基础,来建立了他的“以人为思维中心的文学理论和文学史研究系统”——这一“体系”构造的现实动力,来自于对文学的政治功能和文学创作上的机械反映的厌恶和批判。
1985年,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的《论“20世纪中国文学”》,和陈思和的《新文学史研究中的整体观》先后发表。
(注:黄子平等的文章刊于《文学评论》(北京)第5期,他们三人并在这一年的《读书》(北京)上,连续就“20世纪中国文学”的问题,发表“三人谈”的对话。
论文和对话等,编为《20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出版。
陈思和的文章刊于《复旦学报》(上海)1985年第3期。
)提出“20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并强调对20世纪中国文学进行“宏观”、“整体”把握的主张,不仅推动研究视角、方法的更新,而且暗含着一种重要的观察、评价中国现代文学的尺度的提出,因而其影响不仅限于文学史研究的范围。
在80年代中期,“回到文学自身”和“文学自觉”是批评家和作家的热门话题。
这些命题的提出,表达了作家对文学在人的精神活动领域的独特性地位的关切。
在涉及当代文学存在的问题上,则包容着多个方面,如对于要文学承担过多的社会责任的清理(“干预生活”这一口号这时受到广泛怀疑),对文学只关注现实社会政治层面问题的反省,以及长期以来忽视文学的“本体”问题的检讨。
这说明,当代作家原先过分注重社会政治问题的“传统”,出现了分裂。
在此时,“文学自觉”既是一种期待,也可以说是对已存在的部分状况的描述。
不过,期待之物所带来的苦涩“后果”,也开始体味到。
1988年初,《文艺报》发表的《文学:失去轰动效应以后》(注:载1988年1月30日《文艺报》,作者王蒙,署名阳雨。
)一文,反映了在作家分化、“严肃文学”(或“纯文学”)“边缘化”、读者对“严肃文学”的关注程度降低等趋势面前,文学界的复杂的心理反应。
对于“失去轰动效应”的文学,有的认为是文学的“疲软状态”,是作家“脱离现实”、失去对社会迫切问题的敏感和把握能力所致。
另外的看法则认为,这正是文学走向自觉、深沉,走向成熟的开端。
四 总体风格和作家姿态 在80年代,尽管“文学自觉”曾是激动人心的口号,不过,即使是最强调“艺术至上”的作家,也有着相当强烈的民族关切和历史责任的承担,面临着具体境遇中的“历史”的提问。
这种责任承担,使有关“历史”清算和(群体的和个人的)“历史记忆”的书写,几乎是80年代作家或有意,或无意的选择。
这不仅是“题材”意义上的,而且是创作视域、精神意向上的。
作家的意识和题材状况,影响了80年代文学的内部结构和美感基调。
在相当多的作品中,可以感受到一种沉重、紧张的基调。
(注:对于“新时期”文学的某一方面的特征,黄子平曾用“紧张”这一语词来描述。
见他为《1990年度小说选》撰写的序言。
香港三联书店1991年版。
)这里的沉重、紧张,既是指情感“色调”,但也指结构形态,作品的“质地”。
在不同阶段,或不同的作家那里,这种“基调”呈现为多样的表现方式。
从情感“色调”而言,有那么多的悲剧性事件需要讲述,那么多长期被压抑的情绪需要释放、宣泄(“激情的作用往往胜过技巧的效果”),那么多的社会、人生问题需要探讨,而若干基本观念也需要重估。
80年代的社会政治、人生问题,个体与群体,生命与文化,时间与空间,现实与历史,传统与革新,东方与西方等问题,都要求进入文学文本,试图在创作中涉及和讨论。
在“文体”上和“结构”上,则是较少空隙的密度。
叙述语调既是那样的紧张急迫,而作品中又常拥挤着众多的意象、隐喻、象征和寓言,以此来承担过重过多的“意义”和“问题”。
在80年代,能够以较为裕如和放松的笔调与风格来写作的作家并不多(汪曾祺可能是其中的一个)。
这种相当普遍的“美感”基调,与作家的现实处境有关,事实上,这也是中国当代普遍性的象征思维方式和审美风尚的延伸。
探索、创新,是80年代文学界的普遍的强烈意识。
探索、创新、突破、超越等,是文学批评界使用频率很高的几个词语。
开放的环境提供的文学比较(与西方现代文学,也与本国“五四”到40年代的文学,以及当代台湾等地区的文学),使作家意识到中国当代文学不尽人意的状况,而产生了普遍、持久的“走向世界”的愿望,期望在不长的时间里,出现一批有思想深度和艺术独创性的作品。
不同知识背景和不同年龄段的作家,都努力从各个方面,去获取激活“超越性”的创造力的因素,追求“从题材内容到表现手段,从文艺观念到研究方法”的“全方位的跃动”(注:上海文艺出版社“文艺探索书系”《编辑前言》。
该书系出版于1986-1988年间,收“探索色彩更为浓厚而又确实在某些方面实现了突破和超越的作品”。
创作方面有《探索诗集》、《探索小说集》、《探索戏剧集》等,理论有刘再复等多人的专著。
)。
不同的思想艺术基点和不同层面上的文学探索,表现为多样的情形:发掘以前曾被禁止、或很少涉猎的题材(爱情,监狱和劳改队,性,庸常琐屑的生活,私人性的经验……);创造很难用“正面”、“反面”,“伟大”、“渺小”的标准加以划分,在道德判断上暧昧含糊的人物;尝试某种美学风格(悲剧,悲喜剧,反讽,“零度情感”的叙述,……),运用前此当代文学中罕见的艺术方法(意识流,开放性结构,多层视角,纪实与虚构的互相渗透)……其间,最为重要的探索也许表现在“哲学”、世界观的层面上。
这包括对文学的“本质”、对文学与现实世界的关系的理解。
这自然会在文学的思想艺术形态上得到体现。
创新的强烈愿望,既是文学界充满活力的证明,但也是浮躁心态的流露。
不少作家(特别是“复出作家”和“知青作家”)意识到留给他们的时间很有限,长久的文化封闭所造成的吸取人类文化成果的任务又如此艰巨,这种种压力,是普遍性焦躁情绪产生的主要原因。
概述50-60-年代文学思潮
第一节 50年代、60年代文学运动与文学思潮 一、第一次文代会 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于1949年7月2日至19日在北平举行。
大会总结了五四以来文艺工作的成绩与经验,确定了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新中国文艺事业的总方针,指出了新中国成立以后文艺必须为人民服务、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总方向,成立了以郭沫若为主席、茅盾、周扬为副主席的全国文艺界的组织-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这次大会标志着中国新文学以此为起点,进入了当代文学的阶段。
第一次文代会对50年代初期文学思潮的形成和后来文学思潮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它以解放区文艺为新中国文学的楷模,继承和发展了解放区文艺的精神内核:以文艺为政治服务并从属于政治为文艺工作的性质和地位,以工农兵生活和工农兵形象为文艺表现的主要内容,以民族化和大众化为文艺创作的主导风格,以“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为文艺批评的标准,以作家深入工农兵、改造世界观为实现上述任务的保证。
第一次文代会存在的局限:首先,由于对新的形势、新的环境估计不足,对建国后和平时期文艺工作的新特点研究得不够充分,以至于简单地照搬了战争年代解放区文艺运动的政策、经验和做法,致使文艺工作产生简单化、教条化的毛病。
其次,由于沿用了解放区文艺的做法,因此对指明的文艺与生活的关系做出了狭隘的理解,具体说来就是由文艺服务于政治,到文艺服务于政策、服务于当前中心任务,忽略了文艺自身的规律,导致创作中出现公式化、概念化倾向。
再次,由于把解放区文艺作为新中国文艺的楷模,相比之下对于国统区的文学艺术成就估计偏低,不能正确对待从国统区出来的广大作家,把他们一概视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再加上文艺队伍中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宗派主义情绪未能清除干净,因此不免影响到作家队伍的团结,影响了一些作家的积极性。
建国初期的文艺批判运动就是在这样的指导思想的影响下开展起来的。
二、建国初期的文艺思想斗争1、1951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武训传》是编导孙瑜根据山东贫苦农民武训“行乞兴学”的事迹改编而成的,影片摄制于1948年,建国后剧本做了修改重新拍摄,1950年底在全国上映。
影片描写武训为了让穷苦的孩子也能念书,忍受屈辱行乞40余年,兴办三所义学,从而歌颂了武训精神,肯定了武训所走的道路。
影片放映之初获得一片赞美之声。
不久,对《武训传》的宣传与赞扬引起了中央有关部门的重视,认为这种现象反映了文艺界严重的思想混乱,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撰写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严厉批评了《武训传》。
“讨论”随即转变为声势浩大的批判运动。
2、1954年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俞平伯与胡适等同是“新红学派”的主要代表,20年代出版了《红楼梦辨》,后经修改,于1952年以《红楼梦研究》重新出版,还将新写的论文辑成《红楼梦简论》出版。
对《红楼梦》的版本、作者和文学上的承继关系进行了大量去伪存真、核实正误的工作,并且吸收了西方现代人文精神与美学观点,对《红楼梦》的艺术手法、艺术风格作出了有别于传统的批评、阐释,开创了红学研究的现代格局。
俞平伯的观点和方法受到刚从山东大学毕业的李希凡、蓝翎的质疑与批评,他们的文章受到了的重视。
指出,李、蓝二人的文章“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
……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
”。
的意见改变了这场学术讨论的性质,使之发展成波及整个思想文化界的大批判运动。
3、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胡风(1902-1985)是我国现代著名的诗人、文艺理论家。
原名张光人,湖北蓟春县人,他的文艺思想极为复杂,其核心在于强调作家的“主观战斗精神”,提倡创作主体的“自我扩张”与“自我斗争”,用主观拥入“客观”,表现描写对象“精神奴役的创伤”,主张创作方法大于世界观,认为它们是现实主义的关键所在。
对胡风文艺思想的论争,可以追溯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只是当时属于正常的理论论争。
1952年文艺整风期间,胡风发表了对文艺问题的不同意见,不久受到文艺界部分同志的批评。
1953年《文艺报》先后发表林默涵、何其芳的《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和《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
》,对胡风文艺思想进一步展开批判,胡风不服,于1954年向党中央递交了30万言的《关于解放以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反驳了林、何等人对他的批评,同时全面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文艺观点,受到的首肯,然而时至1955年1月,《人民日报》开始看在批判胡风观点的文章,2月,中国作协主席团决定对胡风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展开全面、彻底的批判。
5月《人民日报》将胡风等人的私人通信作了摘录,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升级为政治上的对敌斗争,在全国掀起了粉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高潮。
胡风被捕入狱,2100人受到株连,造成新中国成立以来罕见的冤假错案。
1980年9月,胡风以及“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在政治上得到平反。
1988年6月,中央有关部门又对胡风文艺思想等方面的几个问题复查,撤销和纠正了以往的一些错误提法。
胡风(1902~1985)现代文艺理论家、诗人、文学翻译家。
原名张光人,笔名谷非、高荒、张果等。
湖北蕲春人。
1920年起就读于武昌和南京的中学,其间开始接触“五四”新文学作品。
1925年进北京大学预料,一年后改入清华大学英文系。
不久辍学,回乡参加革命活动,后一度任职于国民党的宣传、文化部门。
1929年到日本东京,进庆应大学英文科,曾参加日本普罗科学研究所艺术研究会,从事普罗文学活动。
1933年因在留日学生中组织抗日文化团体被驱逐出境。
回到上海,任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宣传部长、行政书记,与鲁迅常有来往。
1935年编辑秘密丛刊《木屑文丛》。
翌年与人合编《海燕》文学杂志,写了《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
》,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革命文艺队伍内部由此开始了一场关于“两个口号”的论争。
这一时期发表大量文艺理论批评文章,结集出版了《文艺笔谈》和《密云期风习小记》,还出版了诗集《野花与箭》与一些译作。
抗日战争爆发后,胡风主编《七月》杂志,编辑出版了《七月诗丛》和《七月文丛》,并悉心扶植文学新人,对现代文学史上重要创作流派“七月”派的形成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曾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常委、研究股主任,辗转于汉口、重庆、香港、桂林等地从事抗战文艺活动。
1945年初主编文学杂志《希望》。
这一时期著有诗集《为祖国而歌》,杂文集《棘原草》,文艺批评论文集《剑•文艺•人民》、《论民族形式问题》、《在混乱里面》、《逆流的日子》、《为了明天》、《论现实主义的路》,散文集《人环二记》,译文集《人与文学》等。
1949年起任中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其间写有抒情长诗《时间开始了》,特写集《和新人物在一起》,杂文短记《从源头到洪流》等。
胡风的理论批评文字涉及多种文体及中外作家作品、“五四”新文学运动中出现的理论问题等,但中心是围绕着现实主义的原则、实践及其发展而展开的。
对胡风的一些理论主张,长时期内一直存在着不同意见,展开过批评,发生过论争,胡风坚持自己的观点,进行了反批评。
1954年向中共中央写了《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三十万言书”),被毛主席亲自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之首,被捕入狱,并开展全国范围的批判、斗争。
1979年获释。
1980年平反。
后出任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和文化部文学艺术研究院顾问等职。
他的文学理论著述辑为3卷本《胡风评论集》出版。
三、“双百”方针的提出与反右斗争扩大化1、“双百”方针的提出 1956年5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其内容的核心是:主张在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确定“双百”方针是发展科学和文化事业的重要方针。
随后中央发表了关于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动员各阶层人士“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
整风运动的动员和开展使人们畅所欲言,作家们批判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给新中国文艺事业带来的危害,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活跃局面。
2、文艺界的反右派斗争1957年6月,经知识和亲自部署的反击“右派分子”的斗争迅速在全国展开。
“双百”方针的提出所带来的令人欣喜的活跃局面很快发生了逆转,创作自由和学术自由被打成资产阶级的反动口号,许多文学作品和争鸣文章被打成“大毒草”、“修正主义的文艺观点”,连同冯雪峰、丁玲等在内的一大批评家、作家被打成“右派分子”。
1958年2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周扬的《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对文艺界反右派斗争作了总结,并对这场斗争的意义作了高度的评价。
文艺界开展的反右派斗争全然否定了贯彻“双百”方针、批判教条主义的积极成果,使“左”的思潮进一步蔓延,给新中国的文艺事业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四、党的文艺政策的调整与“左”倾思潮的泛滥1、党对文艺政策的调整 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由于政治和经济工作中的“左”的作物,加上严重的自然灾害等客观原因,我国进入了连续三年的国民经济严重困难时期。
1960年冬,中央决定对各方面的工作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
与此同时,文艺政策相应调整,周扬、夏衍、邵荃麟等文艺工作负责人在周恩来、陈毅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支持下,在力所能及范围内纠正“左”的偏向,给文艺工作带来了生机。
1961年第三期《文艺报》发表了《题材问题》的专论,提倡题材的多样化,破除题材问题上的清规戒律。
同年6月,召开了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新侨会议),会上,周恩来做了重要讲话。
希望发扬民主,改变文艺界的作风。
1962年3月,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在广州举行,周恩来到会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着重阐述了如何正确评价与对待知识分子、如何改善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
陈毅也到会讲了话,高度评价了中国知识分子在党的领导下所取得的成就和做出的贡献。
同年5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的社论,社论指出文艺的服务对象,应由为工农兵服务,扩展到“为以工农兵为主体的全体人民服务”。
同年8月,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在大连举行。
着重研讨文艺创作如何反映人民内部矛盾,更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问题,邵荃麟提出“现实主义深化”、“写中间人物”的主张。
这几次会议和社论都在不同程度上总结汲取了前一阶段文学工作的经验教训,澄清了一些理论是非。
文艺创作方面有的一些新的变化,出现了一些表现普通人生活的较优秀的作品。
2、“左”倾思潮的泛滥党对文艺政策的调整所带来的某些新局面,很快又被“左”倾思潮的升级淹没。
由于同志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致使他在1962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向全党全民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
从1962年到1965年,林彪、康生、江青一伙相互勾结,利用对文艺形势的错误判断,策划了一系列全国性的大批判,其中影响最为恶劣、规模最大的是1965年11月开始的对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
第二节 “文化大革命”十年文艺思潮一、“文艺黑线专政论” 为了对文艺界实行“全面专政”,林彪委托江青于1966年2月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形成《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炮制了所谓“文艺黑线专政论”。
林彪、江青一伙对新中国文艺事业的洗劫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他们把新中国成立以来文艺理论方面的代表论点归纳为“黑八论”,即“写真实”、“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现实主义深化”、反“题材决定论”、“写中间人物”、反“火药味”论、“时代精神汇合论”和“离经叛道论”。
其次是把大批优秀作品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
第三、大兴文字狱,文艺工作者或被关进牛棚,或被流放监禁,致使冯雪峰、邵荃麟、老舍、田汉、赵树理、闻、杨朔、海默等数百名文艺家被迫害而死。
蒙受冤假错案劫难的更是不计其数。
第四,强行解散全国文联、作协及其各地分会。
全国文艺刊物,除《解放军文艺》外,全部被迫停刊。
各种文艺团体、文化设施,一律停止活动。
二、帮派文艺江青攫取《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等京剧改革的成果,又炮制了京剧《奇袭白虎团》《海港》《龙江颂》,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等,封为“革命样板戏”。
炮制了小说《虹南作战史》《初春的早晨》和电影《欢腾的小凉河》《反击》《春苗》《决裂》等,作为向老一辈革命家发起进攻的武器,这些所谓的文艺作品是文艺与江青等人的政治阴谋结合的产物。
江青一伙根据他们的创作经验总结出一套理论纲领,即“根本任务论”“三突出原则”“主题先行论”。
进步文艺 一类是不愿完全遵从政治之命的文学。
长篇小说又黎汝清的《万山红遍》、克非的《春潮急》、姚雪垠的《李自成》(第二部)、曲波的《山呼海啸》等,中短篇有李心田的《闪闪的红星》、蒋子龙的《机电局长的一天》、话剧《万水千山》、湘剧《园丁之歌》、晋剧《三上桃峰》,电影《创业》《海霞》等。
一类是地下文学。
小说有张扬的《第二次握手》、靳凡的《公开的情书》,诗歌有郭小川的《团泊洼的秋天〉,舒婷的《春夜》《船》,食指的《相信未来》等,以及1976年“四五”天安门诗歌。
天安门诗歌推动地下文学进入可歌可泣的高潮,谱写了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最为悲壮的挽歌与战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