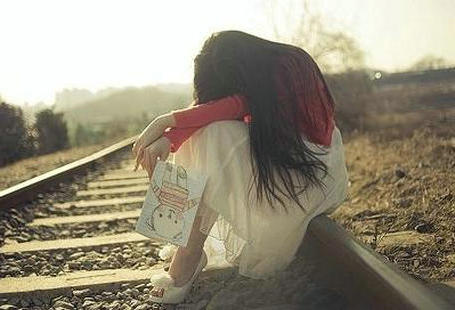“乡村衰败”是什么造成的
朋友,你知道我的家乡在哪儿
告诉你吧,我的家乡是一座春天栖息的城市——中国航天城·西昌。
西昌是山好、水好、人更好的地方。
这里土地肥沃、气候暖和、雨水充沛,很适合各种农作物的生长,特别是适合水稻的生长。
宽阔、美丽、富饶的西昌坝子,又有“四川第二粮仓”的美称。
再加上四A级著名的邛海、泸山风景区,西昌就成了著名的旅游胜地了
在这里我仅向大家介绍一下西昌的田园吧
我们这些生活在城里的孩子,总觉得城里有高楼大厦,宽阔、整洁的大街,美丽、宽广的广场,物品丰富的超市、商场……对广阔的田园、农村有些看不起
可使我印像最深的是:每当学校每年组织春游,特别是每年一放寒、暑假,爸爸、妈妈都要带我登泸山,环游邛海。
或到农村走亲、访友。
啊
一到郊外、乡村,总觉得一切都格外的新鲜,水格外的清,天格外的蓝,树木和草格外的绿,空气是格外的新鲜。
使人感到格外神清气爽,一点儿也不厌倦。
朋友,当我们走进西昌的田园,春天万物复苏,桃红柳绿。
迎春花盛开,银燕从南方飞来……好一派春意盎然的景像。
夏天,万物生长盛旺,百花盛开,稻田里的秧苗绿油油的,就好像给大地铺上了绿色的大地毯。
果园里枝繁叶茂,果实累累、生机盎然……秋天,稻团里的稻谷金灿灿的,好像是给稻田铺上了金黄色的大地毯,从远处望去格外耀眼。
果园里的石榴一个个露出圆圆的笑脸。
柿子树挂满了许多红红的小灯笼,好似在向人们传递着丰收的喜讯,农民伯伯个个都笑开颜。
啊
朋友,城市、乡村、田园大不一样,让我们在学习之余,迈开双脚走出城市,去到乡村,去田园,去欣赏大自然的美景,去饱偿清新的空气,去开阔我们的眼界
乡村的风光是一副美好的画卷,他们的习俗和我们大大的不一样,他们的习俗有他们的特点,让我来给大家说一说我看到的乡村吧
在我八岁那年,跟爷爷奶奶去过一个古老的村庄,不仅是个乡村还是一个旅游胜地,有许多人不是在那儿观景啊,就是在那儿画画,不是在那儿画画呀就是在那儿记录这儿的美景
乡村的房子很偏僻,和古代乡村的房子差不多,他们这家家户户的都有一条小沟,这个小沟不论是在什么时间,都在流淌着,他就是这些房屋的动脉。
那里的柳树也很吸引人,看那长长的垂柳真像是柳树姑娘的辫子,那样鲜嫩、那样柔滑
开着粉红色、白色的荷花真美啊。
上面还不时地有几只蜻蜓落在荷花上,忽然,这情景使我想起一首诗,其中有这么一句“优秀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荷花是美丽的,湖是神奇的,那里还有一条清澈的湖水是有灵性的,在早上7点到8,水能让人们喝,如果仔细品味,就能品出点甜滋滋的味道;下午4点到5点时能让妇女们跪在石板上捣衣,现在我已经看到了一些妇女们在捣衣了
湖边有许多画画的人,柳树倒映在湖面上,湖水变绿了;荷花倒映在湖面上,湖水变充实了;蜻蜓倒映在湖面上,湖水变欢快了
啊
我仿佛陶醉在这美丽的乡村里了,真是:“舟行碧波上,人在画中游啊”
田园的空气是清新的,田园的天空是蔚蓝的,田园的景色是独特的,田园会是你留恋往返。
早晨,空气清新迎面吹来的凉风会是你神清气爽,看
鸟儿在叽叽喳喳的唱晨歌,小溪慢慢的流淌,太阳把温暖的阳光洒向田园,柳树吸取阳光变得充满活力并在津津有味地听小鸟唱歌。
中午,天气闷热不想早晨那么凉爽,知了齐声合唱“知知知”……早晨的小鸟累了无精打采地趴在树杈上,柳树累得也弯下了腰,乡下的孩子们一个接着一个地跳进小溪里小溪很欢迎孩子们的到来用浪花拥抱着孩子们,孩子玩打水仗泼水球,孩子的笑声和快乐的心情融进了空气中,给闷热的中午增添了几分乐趣。
黄昏,在远处的小山顶冒出一缕青烟,用手摸摸地面还有一丝余热,凉爽的微风中带着一丝暖意。
瞧天空中只见深红的晚霞已经染红了半边天空,蔚蓝的天空换了一件深红色的裙子,美丽的晚霞形状不同千姿百态,两匹马在空中赛跑跑着跑着不见了消失了踪影,是哪位魔术师把黄昏装扮得如此美丽迷人
夜晚,太阳依依不舍地离开天空,美丽的月亮给幽静的大地洒下一片银辉,温柔的月光照在小溪里小溪显得更加美丽,天空好像一张蓝色的波斯毯上面镶嵌着黄色的“小宝石”“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小星星唱起了悦耳动听的歌。
宁静的夜晚安静而又迷人,鸡。
狗。
猫。
鸭。
都睡了,花儿小草也睡了,人们也进入了甜美的梦想。
田园像一幅画,像一首诗,像一首歌,田园美的让你留恋
形容衰败的成语
[东零西落] 零散稀疏。
形容衰败。
[鞫为茂草] 指杂草塞道。
形容衰败荒芜的景象。
[鞠为茂草] 指杂草塞道。
形容衰败荒芜的景象。
鞠,通“鞫”。
[月缺花残] 形容衰败零落的景象。
也比喻感情破裂,两相离异。
[花残月缺] 形容衰败零落的景象。
也比喻感情破裂,两相离异。
[西风残照] 秋天的风,落日的光。
比喻衰败没落的景象。
多用来衬托国家的残破和心境的凄凉。
”[百业萧条] 萧条:冷落、凋敝。
指各行各业都很冷落、不兴旺。
形容社会的衰败。
乡村衰败到底是什么造成的
这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是表示中国从一个农业大国向一个工业大国的转变。
乡村衰败是工业化进程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正常现象。
从文化传承与创新的角度,说明乡村文化的衰败为什么会引起学者的担忧和焦虑
一的确,“农业”问题如果作为产业经济问题,在中国并不十分突出,至少它比传统时代甚至改革初期的重要性已经明显下降,同时也没有盛行“大农业”的许多发达国家那么重要――大家知道农业问题已经成为现代国际经济问题、尤其是发达国家间经济关系问题的一个关键,世贸谈判多哈回合经历这么多年而始终卡壳,主要卡在了农业问题上。
但是发达国家却基本没有所谓的“农民”问题,不仅因为他们农业人口比例已经很少,而且他们的那么一点务农者也已经完全“公民化”,没有人把他们视为弱势者,甚至他们百分之几、至多百分之十几的人口却对“多数决定”的议会政治具有极大的影响力。
以至于有人戏言今天西方的民主制如果说有点“虚伪”的话,那与其说是少数资本家、不如说是少数农民在影响和左右着多数意志。
另一方面,许多发展中国家,包括我国在内,在改革前还没有解决“吃饭问题”,农产品供给严重短缺,处于“民以食为天”的状态,解决“民食”问题的农业自然也是“天大的事”,是重中之重,更不用说农业社会的经济问题基本上就是农业问题了。
而我国现在与上面两种情况都已完全不同。
一方面,经过30多年农业的长足发展,如今的中国已不再像改革开放前那样操心“吃饭”问题,受困于农产品供给不足。
但另一方面我国也不像美国、法国、加拿大、阿根廷、巴西等国家那样定位为面向全球市场的战略性大农业出口国,对农业生产过剩、农业经济周期和国际农贸谈判之类问题极为关切。
我们的资源禀赋决定了中国农业基本上是内需型的,尽管存在品种调剂问题,就总量而言,我们的农业也能够满足内需。
今后我国农业发展的技术路线和经营方式路线当然还有大量可议的话题,但是几十年来的经验,尤其是当年“农业纲要四十条”和人民公社制度的实践经验表明,如果脱离农民自身的意愿和自由选择的权利,政府“过分热心”地干预乃至决定农业技术与经营方式,往往变成“折腾”农民,效果并不好。
过去诸如技术上推广双轮双铧犁、一味提高复种指数、普及杂交高粱和小麦取代青稞,经营上从“大公社”到“队为基础”,都留下了许多教训。
历史地看,作为一个农业文明积淀深厚而又幅员广大、各地条件极其多样的大国,我国各地农业的适宜技术和适宜经营方式其实更多是农民自主选择的结果。
正是在农民自主性得到较大尊重的改革时代,农民以“三三得九不如二五一十”的智慧解决了复种问题,以大型农机专业户为众多小农提供商业化服务的途径,解决了过去政府认为最适合机械化的“大公社”时代长期无解的机械化问题,摆脱了一会儿押宝双轮双铧犁,一会儿突出手扶拖拉机,天天号召“农业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而手工―畜力农业依旧的长期困境。
在经营方式上,摆脱强制集体化后的农民无论是99%以上选择了家庭经营的农户,还是原先95万个“大队”中显示出经济活力而能让农民选择留在“集体”中的7000多个“村”,经济都有了显著的改善。
农户普遍摆脱贫困而走向程度不等的富裕,极少数“集体”也大都发展成为超级“明星村”。
曾经有人以后者的成就论证小岗农民走错了路,而南街村的选择才是对的。
其实他们是不顾常识地根本颠倒了因果关系:不是“明星村”由于强行禁止农民离开而得到了发展、小岗则因为没有“捆住”农民而停滞,恰恰相反,正是由于原来的强制集体化农村绝大多数历经20多年实践都没让农民感到“优越性”,使他们在能够自主后都选择了离去;而能让农民选择留下的自然只有鹤立鸡群的极少数。
这些极少数有超常绩效是理所当然、完全正常的――今天的“集体”如果没有绩效而强行禁锢农民不让离开,那就不仅不是“明星村”的问题,而是有犯罪之嫌了。
而能让农民自愿留下的“集体”是如此之少,这难道还不足以体现改革前农业体制的大失败么
且不说像以色列的基布兹那种纯自愿的集体化尽管时过境迁也有风光不再的问题,但仍然可以留住相当部分成员,甚至国际上公认为失败的前苏联集体农庄,尽管它的弊病众所周知,但所谓叶利钦“复辟资本主义”以来的20多年,获得了选择自由的俄罗斯农民也仍有约三分之一愿意留在改良后的集体农庄中。
而我们的公社体制在农民获准退出后仅仅几年就土崩瓦解,95万个“集体”仅有约7000个,即不到百分之一能够留住其成员
公社化时代是严禁“单干”的,改革后农民获得了“退出权”,但是并没有禁止自愿的“集体”,而农民能够相对自主选择后,无论“单干”还是“集体”,都比以前成功得多。
所以,改革后农业的成功表面,似乎是“经营方式”上“单干”对于“集体”的成功,其实从本质上看,它是相对自由的选择权对没有自由的选择权的成功。
农民有没有选择经营方式的权利,远比“哪一种经营方式好”更重要。
公社解体后,我国改革时代的农业经营方式也发生了和正在发生着种种变化。
但无论公司加农户、合作社加农户还是规模化农场,也无论规模化是通过农民间土地流转还是通过外部公司包租农民土地的方式,能够被农民接受的成功选择也往往出于农民的意愿,与政府原先的设想常常出入很大。
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证明,正如农业新技术只有在市场上供农民自主采纳才有前途一样,新经营方式也只有在自愿前提下,让农民因地制宜才能站得住脚。
而政府应农民之需要做好服务工作才是功德无量的事情。
近年来农业问题方面有许多讨论,诸如是坚守耕地“红线”保证粮食自给,还是充分利用国际市场扩大进口;公司加农户好还是合作社加农户好;继续保持农民兼业化作为打工者的“退路”,还是发展规模化专业经营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等等。
但是一些地方在忽视农民权利的基础上讨论经营方式,往往哪种主张都会出问题。
例如在“只许官‘圈’不许民‘卖’”的格局下,强调坚守“红线”,农民就更没法自主开发土地,但政府要“圈地”仍然照样可以大圈特圈。
而如果“红线”被认为不必坚守呢,那官方的“圈地”就更会形成狂潮,但是老百姓想“卖地”照样不行。
过去说农民应该兼业化,“农民工”在城安家就受到种种阻挠,“重庆模式”走红时有官员甚至声称让农民工做“两栖人”是防止重庆出现贫民窟的不二法门。
但是后来官员和公司盯上了农民的土地,同样的官员又开始大讲“两栖人”如何造成“土地利用不经济”,开始用种种手段强迫农民变“市民”了。
再如土地“确权”和推动“流转”也是过去民间多年的要求。
可是具体怎么搞至今也还是语焉不详。
农户被“确”给的到底是什么“权”
面对强势者的侵权,农户的这个“权”能得到保障吗
“土地流转”近年来常被当作政府推行“规模化农业”的手段来提倡,而“发展家庭农场”的说法也把国际上泛指的家庭农业(这个意义上的家庭农场我国在大包干改革后就普及了,何须现在“发展”呢
)偷换成了“上规模的”家庭农场概念。
这当然不一定是坏事,可是只提土地“流转”不是买卖和交易,甚至不是“使用权”或“承包权”的交易,是否暗示这种“流转”可以是非自由交易性质的,即可以是“政府动员”下的强制“流转”
我们看到的情况是《决定》公布后各地强制圈地之风并未消弭,甚至由于《决定》提倡市场经济的利好,引发各地新一轮“招商引资”热潮,此风还有日长之势,不能不让人忧虑。
二总之,我国现在面临的关键性问题不是“农业问题”而是农民问题。
“农村问题”同样如此。
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会导致农村人口下降,许多乡村社区因此消失,这是几乎所有现代化成功的国家都经历过的阶段。
但是像我国如今这种关于“乡村衰败”的强烈呼声却是很少见的。
其实表面看来,与一般国家农民进城初期形成都市贫民社会、乡村中无人居住的房子破败不堪相比,我国由于强制禁止进城农民低成本安家造成普遍的“两栖人”或“流动劳工”现象,城市中号称没有贫民窟,农村中充斥着“两栖人”血汗换来的“无人新居”,但在光鲜外表下的社会性“衰败”却比人家有过之而无不及。
取代大型贫民窟和乡间废村的是我国无与伦比的家庭离散现象和“候鸟”人口,农村中的“三留守”现象(留守老人、留守妇女、留守儿童)造成许多骇人听闻的人伦惨剧。
典型的如云南镇雄一个貌丑人穷的乡间无赖竟能长期霸占村中十余名留守妇女;广西兴业一名11岁留守女童竟遭同村十余名中老年人(44~76岁)频繁强X奸、轮X奸两年之久;这类古今罕见的恶性丑闻反映的“衰败”,岂是一般的建筑破旧、治安不良所能相比
有人甚至以此做了“文化”文章,说什么中国传统文化重视家庭伦理是讹言,中国人其实最重金钱而无视亲情,很少有哪个民族会有如此高比例的人群为打工挣钱甘愿常年家庭离散。
这样的说法真叫人无语,难道他们愿意这样
“两栖人”取代贫民窟真是他们的选择吗
实际上,尽管城市的棚户和乡村的败屋令人扼腕,但是真正自由的迁徙无论是进城还是留乡都应该是比从前更好的理性选择。
即便像东亚四小龙这样发展很快、现在基本没有贫民窟问题的“新兴工业化地区”,穷人进城之初住棚户也不罕见,只是在经济增长快的条件下他们或因申请政府福利或因就业机会多,境况逐渐改善,而不至于久困于此,而那些经济增长慢的国家就会出现贫民窟长期存在的弊病。
但是我们现在不也是同样依靠高速增长来使“两栖人”可以有钱汇回家乡建设“面子房”吗
一旦高增长阶段结束,过去积累转化成的家乡“面子房”并不能用于谋生,而他们又没有在高增长时期“化”入城市(哪怕是化入城市下层),到时社会性“衰败”在那种“两栖”不靠的状态下就不是光鲜外表能遮住的了。
显然,问题不在于乡村该不该复兴,也不在于所谓“西方式的城市化”能不能超越――什么叫“西方城市化”
西方这么多国家难道有什么统一的“城市化模式”
哪怕是同一个国家比如美国,纽约与拉斯维加斯的“城市化”难道是一回事
关键在于农民的命运由谁决定
农民选择进城,付出劳动就应该得到尊重,不能“上等人”看不顺眼就赶走他们。
农民选择在村,他们的地权就应该得到维护,不能“上等人”看上了眼就一把抢来,无论“圈地招商建大城”还是“收地拆房盖新村”,都得以尊重农民的权利为基础。
这些道理难道只是在“西方”成立吗
可见,我们所说的农业问题很多并非产业经济问题,我们所说的农村问题很多也并非乡村社区问题,实际上它们都是农民问题,主要是农民的人身和财产权问题的不同表现。
今天我国的农业在经济中所占比重已经很低,真正务农的劳动力和真正安居乡间的人口占比也在明显下降,但“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却没有降低。
我国独特的“农民问题”不仅存在于非农产业(所谓的“农民工”),也存在于大城市(所谓的“外地人”)。
应该说改革30多年来我国解决农民问题,即农民权利问题上已经取得较大进展,但是该做未做的事还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