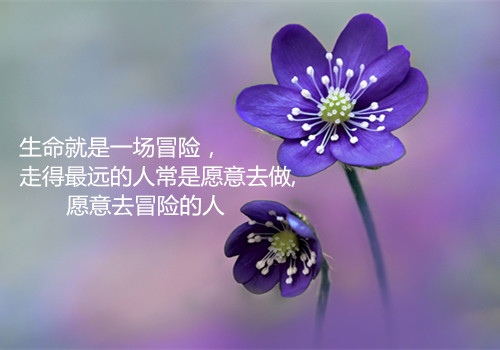党争哪个朝代最激烈
唐朝吧从开科举以来,唐朝有牛李党争,宋朝有新旧党争,明朝有阉党与东林的党争。
从时间的长度上来看,恐怕宋朝的新旧党争的时间最长,从王荆公变法以来,直到南宋灭亡,宋廷的党争都可以被视为是新旧党争的延续。
牛李党争垂40年,而所谓阉党与东林的党争更加短暂。
从党争的开端原因来看,新旧党争算是真正的因为不同的政治理念而引起的,至少有一个新法的大靶子放在那里,争其存废还算有迹可循。
双方第一代的领袖人物在个人的政治操守上也都没什么可以挑剔的,但是后来双方人物的政治道德和能力都血崩,这就是后话了。
而唐朝的牛李党争最开始就是官僚之间的私怨,牛李二人本来就都不是什么争公义是非之人,纯粹就是狭隘的私怨,我觉得陈寅恪先生对于牛李党争的概括失之穿凿了,把一些现代政党代表社会特定利益群体的思想代入了,至少以我读牛李党争的历史的主观感受来说,这帮官僚士大夫之间的抱团撕逼,纯粹就是你赞成的我就反对,并没有守正不易的政治立场,是斗人,不是斗法。
至于阉党和东林党之间还要更复杂一些,所谓的阉党在万历年间只是个皇帝利用宦官作为黑手套,把官僚士大夫集团中的边缘成员捏起来形成一个团体试图从垄断朝纲的清流官僚士大夫们手中抢回权力的手段而已。
但是天启这傻孩子实际上是控制不住魏忠贤的,不管九千岁是公忠体国还是权奸竖阉,至少有一点是肯定的,天启皇帝缺乏控制魏忠贤的手段和能力。
于是阉党就此失控了。
由于阉党中只能吸收朝廷中士大夫集团的边缘人物,那么一定意味着相比东林,阉党成员个人的政治操守肯定是比较糟糕的。
虽然晚明士大夫作为一个整体的操守在明清板荡之际已经被扒的底裤都不剩了,但是坦白说,东林党及其余脉里中还是颇出了几个壮烈殉国的烈士。
你可以说他们清流空谈误国,政斗祸国,但是这是封建官僚士大夫的历史局限性决定的。
不得不承认,这帮人确实已经是当时官僚集团当中私德比较好的一拨了。
古时候的党争大都是因是非而产生的是否
“朋党”之本意:有一批人追随一位或少数领袖,形成组织,并互相协助。
他们或有“共同理想”,或有“共同利益。
而为了实现共同的理想或获取共同利益,则必须要权。
于是,权力之争亦就成了历代党争的原罪。
而所谓引起党争的是非,不过是适逢其会成为党争的借口。
试看历代之党争之最如下:东汉党争之“党锢之祸” 东汉王朝建立后,对于宦官与外戚,最高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的限制措施。
于宦官,废罢中书宦官;于外戚,则令后宫之家不得封侯与政(《后汉书·明帝纪》)。
这些措施的实行,为稳固东汉王朝的政治起了重大作用。
东汉宦官集团的崛起是从汉和帝开始的。
此后的东汉王朝都出现了一个类似的现象:即位的帝王年幼,皇后临朝,垂帘,自然多引用其兄弟之属,称为外戚;而当帝王年长之后,女主为守权,则必然多依靠那些自己信得过的外戚。
幼主生于深宫,长于深宫,内外臣僚,莫由亲接,所与居者,唯阉宦而已(《后汉书·宦者传序》)。
因此,幼帝欲亲政,不得不依靠伴随自己长大的宦官。
以帝王为中心的宦官集团就开始了与外戚集团争夺朝政大权的抗争。
宦官集团与外戚集团的权力之争,便成为东汉王朝自和帝以后最主要的政治内容,而宦官与外戚之间的起伏消长,也成为东汉中后期最显著的政治特征。
除了宦官与外戚两大政治集团之外,东汉还有一个以朝廷大臣为主所组成的士人官僚集团,史称钩党。
其目标即为反抗和抵制宦官擅政与外戚专权。
当然,这三个政治集团之间的关系并不那么单纯,士大夫或投靠宦官集团,或依赖外戚集团,如此现象当时并不罕见。
以李膺为核心的钩党,其目标主要指向东汉的宦官集团。
东汉的士人官僚集团虽然将斗争的目标指向了擅政的宦官集团,但其力量终不能与宦官为敌,故而终致党锢之祸。
桓帝时,李膺等二百余名钩党人员先后下狱,后皆赦归故里,禁锢终身(《后汉书·党锢列传》)。
东汉王朝便在宦官与外戚、宦官与士人官僚的不断冲突中走向灭亡。
实质:是皇权,外戚,士族之间的利益冲突。
实质:是皇权,外戚,士族之间的利益冲突。
唐代党争:之“牛李党争”: 牛李党争,没有受到宦官与外戚两大政治集团的直接干预,然牛李两党之交攻,也曾借助于宦官势力。
如大和三年,时裴度荐李德裕,将大用。
德裕自浙西入朝,为中人助宗闵者所沮,复出镇。
寻引牛僧孺同知政事,二人唱和,凡是德裕之党皆逐之“(《旧唐书》)。
因此,它更多的是士人官僚集团内部的交争。
其实,这唐代党争的实质是,魏晋以来门阀士族与寒门庶族所进行的交锋。
南北朝时期,门阀势力占据主导地位,且丝毫不可动摇。
入唐,门阀士族虽日渐衰落,在唐初依然有相当的力量。
唐太宗的《氏族志》,武则天的《姓氏志》,即为抬高庶族地位和贬低士族威望而作。
门阀士族与寒门庶族自唐宪宗以后,经过前后四十余年的角逐,终于以代表门荫势力的李德裕失败而告终。
陈寅恪先生谓:牛李两党之对立,其根本在两晋南北朝以来山东士族与唐高宗、武则天之后由进士词科进用之新兴阶级,两者互不相容。
此后历代王朝的士大夫官僚集团,均由寒门庶族组成。
而进士考试制度的推行与延续,即为庶族地主进入仕途提供了可靠的保障。
实质:寒门和士族之间的利益冲突。
宋党争之“新旧党争”: 北宋新旧党争最为显著的特征即在于它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庶族士人官僚集团的政见之争。
正是在这一点上,它与东汉、唐、明的党争划清了界线。
北宋新旧党争乃北宋士人官僚集团的内部之争,已如前述。
而由此所引发的便是北宋新旧党争的第二个特征,即北宋士人官僚集团乃处于不断分化与重新组合之中。
这也是北宋新旧党争显而易见者。
北宋新旧党争不仅纯为士大夫之党争,而且还有不断分化与重新组合的特征。
在这二者的背后,却还有一个更为深层的因素,即地域的因素。
换言之,北宋纯士人官僚阶层的党派交争,不啻因其政见不同而然,若以地域析之,则知其与南人、北人之观念紧密相联;北宋士大夫官僚阶层的分化和组合,亦不仅仅因其政见各不相同,它仍然染上了浓郁的地域色彩。
惟其如此,便形成了北宋新旧党争的地域特性。
实质:北宋新旧党争纯属北宋庶族士人官僚集团本身的政见之争,自熙宁迄崇宁,它一直处于不断分化与重新组合之中,而其分化与组合又带有浓郁的地域性。
明党争:“东林党与非东林党之争” 明代党争亦出现于宦官专权之后。
洪武初年,朱元璋为限制宦官专权而令寺人不过侍奉洒扫,不许干与政事。
”然制此法者,首坏此法也。
明太祖朱元璋为独揽朝政大权,废除了宰相一职,使明代的政权结构与前代迥然相异。
罢废宰相后的历朝帝王,已将自己和朝廷大臣隔离开来,二者之间的联系与传递不是由宰相承担,而是由宦官出入殿廷,传播国命。
宦官势力的膨胀及其干预政治的能力遂得以滋长。
而作为统治利益链中重要一环的文官,自然会反抗。
东林党争尤为激烈。
以魏忠贤为代表的熹宗朝宦官集团不仅大兴东林党狱,而且肆意编造东林党籍。
宦官顾秉谦受魏忠贤指使而编定《缙绅便览》,罗列东林党人名单;宦官卢承钦也编制了《东林党人榜》,上列东林党人三百零九人,而在榜之人,生者削籍,死者追夺,已经削夺者禁锢(《明熹宗实录》)。
其做法与北宋之奸党碑如出一辄,不同之处在于,北宋奸党碑出自文人之手,而东林党人榜则由宦官所制。
前者为士林中人的政见不同而引起的党争,后者则为宦官集团与士人官僚集团之间的抗争。
实质:君权与臣权的冲突。
连续两句带“月”字的诗句
卓越的讽刺作家斯威夫特在他的这部小说里描述了小人国里的政党纷争。
亏得他有那样的想象力,说在这个叫做利立普特的国家里,两党激烈的争议居然来自于对于鞋跟高度的选择。
内务大臣向格列佛描述说:七十多个月来,国内两个政党一直相互争斗。
一个党叫特雷姆克森,另一个党叫斯莱姆克森。
区别就在于,一个党的鞋跟高,一个党的鞋跟低。
事实上,据说高跟党更合古法,而国王却决意一切政府管理部门只启用低跟党人。
你不可能不觉察,国王的鞋跟就特别来得低,至少比朝廷中的其他官员低一都尔(约合十四分之一英寸)。
这两个政党的积怨非常深,他们从来不在一起吃喝谈话。
我们估算,特雷姆克森即高跟党在人数上胜过我们,可政权在我们一边。
我们担心的是,国王陛下的继承人王子殿下有点儿倾向高跟党,至少我们发现他的鞋跟一个高一个低,所以走起路来一拐一拐的。
(白马译,中国戏剧出版社2005,页28)以鞋跟高低区分两党,实在是匪夷所思。
这也许折射出斯威夫特的政党观念,或者是他对于英国当时政党纷争的挖苦。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假如不同政党之间的冲突来自于如此琐碎的习俗,也许会将国民的注意力吸引既有冲突却又不至于导致分裂的那些事项上,而降低那些本来让人不共戴天的事项的重要性,最终将不同阶级和族群整合为一个共同体。
晋朝八王之乱和明朝党争哪一个更激烈
八王之乱时期,国家基本完全处于动乱状态,导致后来的五胡乱华,而五胡乱华是几乎让中华文明覆灭。
衣冠南渡什么意思,衣冠南渡之前华夏文明认为南方就是蛮荒之地,能被逼到这个份上,应该没什么好比的吧。
动漫党争处处有,为什么柯南里兰哀的党争如此尖锐激烈
三角恋之所以苦,主要有三种原因。
1.我喜欢的角色没能修成正果。
2.我讨厌的角色竟然... 大老师啊俺妹啊化物语啊也有党争,不过我最早经历的党争还是丽党和香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