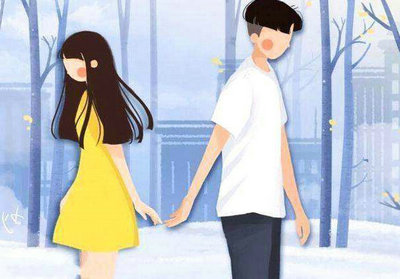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
” 翻译
子曰:“富与是所欲也,不以得之,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君子去仁,恶乎成名
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 译文:孔子说:“富裕和显贵是人人都想要得到的,但不用正当的方法得到它,就不会去享受的;贫穷与低贱是人人都厌恶的,但不用正当的方法去摆脱它,就不会摆脱的。
君子如果离开了仁德,又怎么能叫君子呢
君子没有一顿饭的时间背离仁德的,就是在最紧迫的时刻也必须按照仁德办事,就是在颠沛流离的时候,也一定会按仁德去办事的。
”
曾子杀猪古文全文中“之”的意思
《论语·八佾第三》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
何谓也
” 子曰:“绘事后素。
” 曰:“礼后乎
” 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
《八佾》篇主要涉及“礼”的问题。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出于《诗经·卫风·硕人》,而“素以为绚兮”是逸诗。
此段是子夏问孔子诗经中的这三句作何解。
孔子以“绘事后素”四字作答。
这四个子文简而意丰,给子夏和后人无尽的启发,也带来众多的疑惑和争议。
究其原因,乃是孔子时代距今已二千五百多年,文字句法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当时古人简易的口语对今人而言却是佶屈聱牙;另外文化背景的差异,时代的变迁,使后人难以重现当时的情形,也就很难理解现象背后的文化意义。
所以,“绘事后素”虽然简洁,却并不简单。
后人对其有不同的阐释和理解亦属正常。
综合众多阐释,不外乎三种: 一、“绘事后素”之“绘事”指绘画,“素”指绘画的白底,一说白绢(《说文解字》:“素, 白致缯也。
”是会意字,指没有染色的丝织物。
以古人作画于丝帛上,故曰“后素”)。
宋朱熹认为:“后素”,后于素也。
《考工记》曰:绘画之事后素功。
谓先以粉地为质,而后施五采,犹人有美质,然后可加文饰” (《诸子集成》)。
即素为粉地,人的内在仁德,犹如绘画之素底,是绘画的前提。
有此美好基础,然后学礼,正如将绚烂色彩施于素底,以成其文采。
于是“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在这里“素”可能是指白底,也可能是白绢,但白绢的可能性更大些,因为“素”字本意就是指没有染色、洁白的丝绸 。
如《诗.唐风.扬之水》:“素衣朱绣,从子于鹄。
” ;《怨歌行》:“新裂齐纨素,皎洁如霜雪。
” ;《战国策》:“流血五步,天下缟素”而且更重要的是,先秦绘画多是在木器和丝织物上所作,如商代彩帛绘画及战国楚墓出土,保存先对完整的帛画有《妇女凤鸟图》和《人物御龙图》。
所以,如果对“后”字的理解正确的话,“后于”白绢之上似乎更妥,而朱熹“粉地”之说则显牵强,因为白底作画固为后人习惯,但对先秦而言,没有足够考古证据和历史记录证明那时也是先敷白底,然后才作画。
朱熹以自己时代的事物去揣测春秋时期,所以有此误解。
二、由“绘事后素”启发,引申出深刻的哲学和美学观点。
认为孔子此言,表面上说的是绘画之理,实质却大有深意。
即绘画时施足五彩,在经历过绚烂之后,才体会到素色的可贵。
并由彼及人,表达人生终须由繁华归于平淡,由矫揉回归自然。
无论从对孔子的思想和经历去探究,还是从人生哲学,审美意趣上去分析,这一解释都很有启示意义。
因为从《论语》记载来看,孔子也确实是一个返璞归真的人。
如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
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述而第七》);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学而第一》)。
尤其在《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篇中,当曾皙言其志,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先进第十一》)。
这些生动的记录告诉我们,孔子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为了“天下有道”而奔波改良,但仍保有一颗赤子之心,一份平和淡泊的心境。
后世受其影响,使不慕荣利,淡泊守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独有内涵,并深入到诗歌、绘画乃至为人处世中去,潜移默化,已成为中国人心灵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可以说对“绘事后素”的这一理解,反映了传统知识分子的一种志趣和追求。
也正因为如此,后人只重在对原文的阐发和引申,而忽视了对原意的考据和还原,所以本意虽好,解释虽妙,却不足以令人信服。
因为仅由“绘事后素”四字,便望文生义将“素”简单的认为是白色,更因此得出如此深奥的哲学意义,实在有穿凿之嫌。
实际上,读经典首先应还原其本来面目,然后才可以推演阐发。
而这一过程考据必不可少。
所以应本着胡适先生“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态度去刨根究底,才是对学问真正负责。
否则,即使假设再大胆,观点再完美,离开了实证,也不过是无本之木。
而对于证据不足的假设,不妨阙如,切磋琢磨,总会有新的进展。
三.从古代绘画技巧出发去解释:“后”是然后;“素”指白色,此观点认为,古人作画方式与今人不同,是先施五彩,然后才上白色(一说绘画完毕,然后以白色勾勒出图案。
)所以白色为后,故曰“后素”。
郑玄注曰:绘,画文也,凡绘画,先布众色,然后以素分布其间,以成其文,喻美女虽有倩盼美质,亦须以礼成之(《诸子集成》)。
这样就以绘画之理解决了这个问题,即作画时仅有美丽五彩是不够的,还需要有更重要的一环——上素色的过程,然后才能成为完整的画作。
与朱熹之说相反,这里五彩众色指内在美质,而素色指礼。
引申到修身方面,就是要以仁德为质,以“仁”为本;而后学礼,以成其文采。
最终使自己内外兼修,达到内圣外王的最高理想。
可以说,这种解释虽与朱熹的观点有异,但殊途同归,阐述的道理同样是“仁先礼后”。
所谓差异仅在于对“后”与“素”字的理解上。
但是对“绘事后素”的这种考据并不能令人信服。
首先,古人绘画方式是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因年代久远,又缺乏考古实物,后人很难知晓古人具体的绘画技巧,尤其是先秦时代关于绘画知识的采集记录少之又少,流传下来的作品也是屈指可数。
即使汉末郑玄,距孔子时代也已经数百年,绘画方式之演进极大。
仅此,我们并不能轻易得出素色为后的结论。
所以,以上三种观点,虽各有道理,却都有所不足。
那么能否挖掘其中的合理之处,从而得出切近原意的理解呢,我认为可以。
首先“绘”并非指绘画,后人以今推古,便想当然的将“绘”理解为画画。
考“绘”字的起源:“绘”是一个会意字。
甲骨文“绘”字由两部分构成,左半部分象征丝线,而右半部分则为汇集。
从整体来看,就是将丝线汇集到一起,是对丝的一种加工,有刺绣的意思。
许慎“绘”字从丝,“绘,会五彩绣也”《说文解字》。
也说明“绘”最初与丝织有关。
古人在未染色的白绢上刺绣,于是便有了五彩纹饰。
这一过程称为“绘”。
而“绘”指用笔作画,是后来才有的事。
另外,与孔子时代相近的经书《礼记·杂记下》:“纯以素,钏以五彩”。
我们则可以认为这是对“绘事后素”的解释。
既然人们把“绘”字误解为用笔作画,那么对整句原文的误解也就容易理解。
其实这四个字的关键不在于“后”,也不在于“素”而在于“绘”。
“绘”指五彩绣,自然要绣在丝帛上。
如此,“素”以其原意,是白色丝织物则无疑。
《考工记》之“绘画之事后素功。
”也就有了答案:“素功”就是绣工,即在丝帛上“绘画”。
值得一提的是,“画”的本义与图画无关,作为今义之绘画是汉代之后才有的。
所以就进一步印证了《考工记》这句话是关于手工丝织技术的记载,而不是绘画技巧。
应该说,朱熹对“后”的解释还是很有道理的。
素,既然是彩绣的载体,是“绘”的前提,自然是代表人的内质。
五彩文绘则代表“礼”(先有“素”,然后才能“绘”)。
否则下文子夏所问就难以理解。
“礼后乎
”礼也是在后吗,或者说礼也是后来才有的吗
子夏不仅正确理解了孔子的意思,而且能够举一反三,这着实出乎夫子意料,所以得到了他老人家的赞许。
这里又有了新的问题:子夏问“礼后乎”的潜台词是什么,孔子的原意又是什么,他们师徒二人到底达成了什么默契,使夫子欣然赞许呢
在后人的理解中,最有影响的莫过于“仁先礼后”,即先有“仁”作为修养的基石,而后学“礼,两者顺序有先后,并缺一不可(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
这种观点虽有道理,却只对了一半。
我认为:“礼”固然为后,但“仁”未必为先。
“素”并非指人的内在美质,而是指本质;显然本质为先,而“仁质”是“礼”作用于“本质”的结果。
因为“素”是白色的,是未染成的。
指人的初始未萌阶段,所以墨子见染丝者而叹曰:“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故染不可不慎也”。
既然是本质,就有好有坏,因为并不是每个人天生都具备“仁”。
要想脱胎换骨,成为礼义君子,需要后天不断的培养,与不懈的修身,如《诗·卫风·淇奥》:“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而如何才能约束自己的本性,塑造完美的人格,使自己从本不完善的“本我”跃升至“超我”呢
孔子在《论语》中给出了答案——“礼” 但如果是“仁先礼后”,那么真正符合“仁”的君子少之又少。
例如,子曰: 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
吾闻其语矣,未见其人也。
又如子曰:何事于仁
必也圣乎
尧舜其犹病
连夫子自己都不敢说自己近乎“仁”,可见修身之难,而拥有“仁”质则更难。
礼以修身,“礼”是有助于仁质的形成的。
“礼”首先作用于人的初始内质,然后才美化熏陶,形成仁质。
子夏所悟,不但联想到“礼”,而且理解了“礼”对于人的后天培养,对“仁”的重要作用。
就绘画而言,素,是未经雕琢的底子(内质),最终形成的佳作(仁质)才是最终目的。
所以说人的“内质”为先,“礼”为后。
这也符合绘事后素的本意。
“君子发乎情而止于礼”什么意思,出在哪里
有教无类”从根本上决定了的本质。
“有教无类”的涵义不是某些特定阶层、特定集团、特定群体的人可教,而是人人可教。
人人可教即人人可学,人人可学即大众之学。
…… “有教无类”不是某部分人的问题,而是所有人的问题。
教导人的,不是如何挣大钱、发大财、当大官,而是人如何才称得上是人,怎样才能算作人,如何才能成为一个完全的人。
告诉我们做人比发财更根本、更基础、更富有根源性。
要做人,就要修己。
……儒学的意义就在于将礼乐教化不分族类、不分老少向所有人敞开,实践“有教无类”。
“有教无类”虽说是讲人人可教,然而,在这里“教”毕竟是主动的,而“类”是被动的,此语告诉我们,教者需有愿教爱教之心。
……。
”()人不能与鸟兽同群共处,人不与人打交道,解决人的问题,而逃避现实,回避问题,这样的人生还有什么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