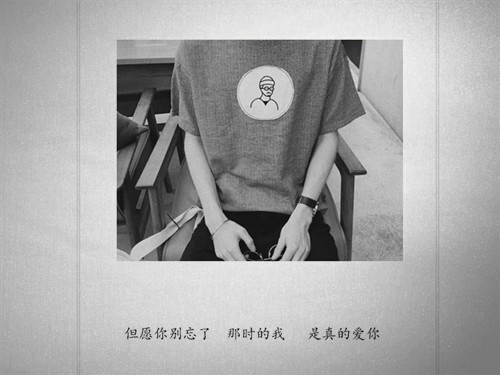描写死人的句子
雨还在不停的下,森林里显得阴森森的冷清。
雨水顺着树干往下流,然后汇集在树脚。
大概是因为长期的浸泡,树脚下发出了腐木的恶臭。
顺着树脚往前看是一具腐败的尸体,浑身散发着恶臭,皮肤早已腐烂不堪。
似乎旁边还有几种不知名的动物在撕咬死尸的肉浓浓的蝇蛆闻开始慢慢散发,许多白色的蝇蛆在尸体上揉动,好像几万只交汇在一起。
死尸睁着充满血丝的双眼,嘴巴张的很大,似乎死前受过巨大的痛苦,凌乱的头发夹杂着鲜血的泥土,显得异常的凄凉。
死尸的四肢已经不见了,应该是被动物给吃掉的。
乌鸦在树枝上低叫,令人毛骨悚然。
死尸的肚子正被乌鸦给剖开,几只乌鸦飞下来食用,一条条鲜血淋淋的肠子被扯了出来。
乌鸦欢快的毫无顾忌的享用着美食,嘴角边似乎还挂着点点血迹。
没有人知道这具不知名的死尸是怎么死的,不过在死尸的身边却有一支猎枪。
。
。
。
。
。
。
如何描写杀人场景 语句
噗”的一声轻响,利刃已经没入了他的体内。
他无意识地发出一声叫喊,眼睛不可思议地睁大了,静静地,静静地望着手中紧紧攥着匕首,正在不住发抖的我。
“为什么……”他轻问。
“我恨你。
”竭力稳住自己正在发抖的手,用力地拔出了匕首,他的血喷涌而出,鲜红的,温湿的血就这么溅了我一身——头上,脸上,身体上,都溅满了他温热的血液……而他,却慢慢地在我身前倒了下去。
“当”的一声,匕首落地,我跪在他的面前,手上还沾着他的血.
描写战争场面的句子
最初的一刹那可怕的。
没有什么群惊惶失措的群众更可怜的了着去拿武器。
他们叫喊着,奔跑着,有许多倒了下来。
这些被袭击的坚强汉子不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他们自己互相枪击。
有些吓昏了的人从屋子里跑出来,又跑进屋子,又跑出来,不知所措地在战斗中乱窜。
一家人在互相呼喊。
这是一场悲渗的战斗,连妇女和小孩也卷在里面。
呼啸着的炮弹拖着长长的光芒划破黑暗。
枪弹从每个黑暗的角落里放射出来。
到处都是浓烟和纷乱。
辎重车和炮车纠缠在一起,更加重了纷乱的程度。
马儿也惊跳起来。
人们践踏在受伤的人身上。
地下到处是呻吟声。
这些人惊惶,那些人吓昏了。
兵土和军官互相找寻。
在这一切中,有些人还抱着阴沉的冷漠态度。
一个女的靠着一垛墙坐着,给她的婴孩哺乳,她的丈夫一条腿断了,也背靠着墙,一面流血,一面镇静地给马枪装上子弹,向前面黑暗中放枪。
有些人卧倒在地上,把枪放在马车的车轮中间开放。
不时爆发出一阵喧闹的喊声。
大炮的巨响淹没了一切。
这是非常可怕的。
([法]雨果:《九三年》第 247—248页) 炮火耀眼,后来阻断了我们的视线。
天空全是铁片的乱哄哄的声音。
在我们头顶上的空间里,许许多多巨大的铁块崩裂开来,纷纷跌下。
在天空下,象暴雨即来时那样漆黑一片,炮弹向四面八方投射出青。
灰色的光芒。
在那可以看得见的世界里,从这一头到那一头,田野在摇晃,下沉,融解,无限广大的空间跟大海一样在抖动。
东方,是极其剧烈的爆炸,南方,是子弹横飞,在天顶,则是一排排开花弹,好象没有底脚的火山一样。
……在那广大无边的地面上,尽是雨和夜色,别的什么也没有,天 ,上的云和地底出来的云,在地面上散落布开,混在一块儿。
([法]巴 比塞;《光明》第175页) 我们用步枪和炮弹来回答向我们疯狂打过来的炮火。
所有防哨和路角房屋的窗口,我们的人都塞上了草褥子,可是里面却因为有子弹打进来都冒着烟。
街垒上不时有一个木偶似的脑袋露出来。
弹无虚发! 我们有一尊大炮,开炮的是几个不大说话的英勇的小伙子。
有一个还不满二十岁,麦黄色的头发,矢车菊蓝的眼珠,遇到有人夸奖他发炮准确,他便象一个小姑娘似的马上红脸。
忽然,窗口上的障碍物一下子落下来了,防御工事在崩溃。
那个开炮的黄头发小伙子号叫了一声。
一颗子弹正打在他的眉头上,在两只蓝色的眼睛当中,仿佛又开了一只黑眼睛。
([法]儒勒, 瓦莱斯:《起义者》第309—311页) 维克多·亨利从凉台上注视着夜袭开始。
破坏、骚动、壮丽的火烧场面、摇曳不定的蓝白色探照灯光、轰炸机马达密集的轰鸣、刚刚开始的砰砰的高射炮声…… 河岸上蹿起新的火苗,四下蔓延,越烧越旺。
远处一片漆黑的泰晤士河上吐出更多的火舌。
但这座大城市的大部分地区却是一片黑沉沉的寂静。
一架小轰炸机从浓烟弥漫的空中坠落,象一支蜡烛似的燃烧着,两条交叉的探照灯光把它紧紧盯住。
即刻就有两架轰炸机坠落下来,有一架带着一团烈火象一颗殒星似的笔直坠落下来,另一架兜了几个圈子,冒起黑烟盘旋起来,终于在半空中象远处的一串炮竹似的爆炸开来。
([美]沃克;《战争风云》弟 607—608页) 德国人的机枪疯狂地扫射着。
许多爆炸开的黑色烟柱子,在直径有一哩来宽的、已经被打得坑洼不平的沙土地上,象旋风一样向空中卷去,进攻的人浪散开了,翻滚着,象水花一样从弹坑旁边分散刀:去,还是爬啊,爬啊…… 炮弹爆炸的黑色烟火越来越紧地扫荡着大地,榴霰弹的斜着飞出来的、刺耳的尖叫声越来越密地泼在进攻的人的身上,贴在地面上的机枪火力越来越残忍地扫射着。
他们打击进攻的人,不许进攻的人靠近铁丝网。
果然就没有能靠近。
十六道波浪只有最后的三道算是滚到了跟前,但是这三道波浪一滚到破烂不堪的铁丝网(许多用铁丝缠着的烧焦的柱子都朝天空竖立着)前面,就象是被碰得粉碎了似的;变成一条一条的小河、一滴一滴的雨点倒流回来…… ([苏]肖洛霍夫:《静静的 顿河》第524—525页) 1937年8月14日下午,日机轰炸上海。
炸弹落于南京路外滩,华懋饭店及汇中饭店被炸毁。
南京路一带尸骸狼藉,在炸毁的建筑物残迹中,受伤者被压在下面,呻吟惨号。
炸死者血肉模糊,肢体残缺。
几分钟后,虞洽聊路与爱多亚路交叉点,也遭到轰炸。
这一地区也是上海的闹市之一,有不少难民聚集在道路两旁。
炸弹落在这里,附近的房屋大都被炸毁或震坍,停在路边的20多辆汽车全部起火燃烧,电缆被炸断垂落地面,又引起大火,使灾情倍加惨烈。
被炸死者的断肢残躯,四处抛散,鲜血染红了街面。
这次轰炸,共炸死无辜平民1742人,炸伤1873人,炸毁及烧毁的房屋财产难以计算。
1937年8月23日中午,日机轰炸南京路闹市区和浙江路,先施公司被炸,电线折断,多处起火,有215人被炸死,一位年轻的母亲横卧血泊,怀中的孩子只剩下两只血淋淋的脚。
此外,还炸死570余人。
同年8月28日下午2时,日机疯狂轰炸上海南火车站。
上海原有南北两个车站,八·一三以后,北站处于战区,交通完全断绝,南站就成了陆路交通的唯一出口。
当时上海及其附近的难民蜂拥而至,争相出逃、南站拥挤不堪。
第一批四架日机首先向南站投弹炸死难民500多人。
不一会,又有八架日机飞抵南站上空投弹,炸死200多人。
车站天桥、月台、铁轨被炸得稀烂,地上满是焦黑残缺的尸体。
月台上横七竖八躺满尸体,上面还压着铅皮和木板。
广场上很多被炸死的妇女紧抱着无头缺肢的孩子。
日机投掷的燃烧弹使车站及站外的外揭旗和郑家桥燃起大火,一时间烟雾弥蔓,哭声四起,满目疮痍,惨不忍睹。
上海南站远离交火地区,根本没有军事设施,中军对南站的轰炸,完全是有计划的野蛮屠杀。
9月18日,日机对上海东区杨树浦等地轰炸,投下多枚燃烧弹,致使那一带的工厂和居民区大火遮天,损失惨重。
这天上午8时,怡和纱厂厂房中弹,打麻机当即起火。
接着东百老汇路、公平路的公所住宅中弹,大火很快蔓延。
此外,兆丰路仓库、百老汇路东一片住宅、培林洋行蛋厂等工业和居民区大火熊熊,被烧成焦土。
在日机的夜以继日的狂轰滥炸下,上海遭到严重破坏。
仅遭日机袭击的文教机关和学校(其中部分又遭轰炸又遭炮击)就达92个,其中被全毁的占75%。
许多医疗卫生机构亦遭到轰炸。
例如,8月18日、19日,日军先后轰炸高悬巨幅红十字旗的直如东南医学院和南翔红十字会第三救护队。
关于轰炸破坏上海的情况,这里摘引一段1938年3月19日上海《密勒氏评论周报》的报道,即可一目了然:被毁的商店至少有10万家,其中包括店主的住宅和财产。
这些商店或被焚毁,或被炸毁,或被轰毁,或被抢掠一空。
我们倘驱车经过虹口、杨树浦、闸北和南市等处,但见两旁街道,尽成废墟,往往延长几里。
在1932年'淞沪战争'后,约一里宽二里长的面积内损害颇重。
这一次,三公里以上的面积内,往往片瓦无存,不足为奇。
在许多地方,破坏的情况,简直难以形容。
两路管理局附近的无数小店铺以及住宅,均遭不断轰炸,摧毁无遗。
最初的一刹那间是可怕的。
没有什么比一群惊惶失措的群众更可怜的了。
他们抢着去拿武器。
他们叫喊着,奔跑着,有许多倒了下来。
这些被袭击的坚强汉子不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他们自己互相枪击。
有些吓昏了的人从屋子里跑出来,又跑进屋子,又跑出来,不知所措地在战斗中乱窜。
一家人在互相呼喊。
这是一场悲渗的战斗,连妇女和小孩也卷在里面。
呼啸着的炮弹拖着长长的光芒划破黑暗。
枪弹从每个黑暗的角落里放射出来。
到处都是浓烟和纷乱。
辎重车和炮车纠缠在一起,更加重了纷乱的程度。
马儿也惊跳起来。
人们践踏在受伤的人身上。
地下到处是呻吟声。
这些人惊惶,那些人吓昏了。
兵土和军官互相找寻。
在这一切中,有些人还抱着阴沉的冷漠态度。
一个女的靠着一垛墙坐着,给她的婴孩哺乳,她的丈夫一条腿断了,也背靠着墙,一面流血,一面镇静地给马枪装上子弹,向前面黑暗中放枪。
有些人卧倒在地上,把枪放在马车的车轮中间开放。
不时爆发出一阵喧闹的喊声。
大炮的巨响淹没了一切。
这是非常可怕的。
([法]雨果:《九三年》第 247—248页) 炮火耀眼,后来阻断了我们的视线。
天空全是铁片的乱哄哄的声音。
在我们头顶上的空间里,许许多多巨大的铁块崩裂开来,纷纷跌下。
在天空下,象暴雨即来时那样漆黑一片,炮弹向四面八方投射出青。
灰色的光芒。
在那可以看得见的世界里,从这一头到那一头,田野在摇晃,下沉,融解,无限广大的空间跟大海一样在抖动。
东方,是极其剧烈的爆炸,南方,是子弹横飞,在天顶,则是一排排开花弹,好象没有底脚的火山一样。
……在那广大无边的地面上,尽是雨和夜色,别的什么也没有,天 ,上的云和地底出来的云,在地面上散落布开,混在一块儿。
([法]巴 比塞;《光明》第175页) 我们用步枪和炮弹来回答向我们疯狂打过来的炮火。
所有防哨和路角房屋的窗口,我们的人都塞上了草褥子,可是里面却因为有子弹打进来都冒着烟。
街垒上不时有一个木偶似的脑袋露出来。
弹无虚发! 我们有一尊大炮,开炮的是几个不大说话的英勇的小伙子。
有一个还不满二十岁,麦黄色的头发,矢车菊蓝的眼珠,遇到有人夸奖他发炮准确,他便象一个小姑娘似的马上红脸。
忽然,窗口上的障碍物一下子落下来了,防御工事在崩溃。
那个开炮的黄头发小伙子号叫了一声。
一颗子弹正打在他的眉头上,在两只蓝色的眼睛当中,仿佛又开了一只黑眼睛。
([法]儒勒, 瓦莱斯:《起义者》第309—311页) 维克多·亨利从凉台上注视着夜袭开始。
破坏、骚动、壮丽的火烧场面、摇曳不定的蓝白色探照灯光、轰炸机马达密集的轰鸣、刚刚开始的砰砰的高射炮声…… 河岸上蹿起新的火苗,四下蔓延,越烧越旺。
远处一片漆黑的泰晤士河上吐出更多的火舌。
但这座大城市的大部分地区却是一片黑沉沉的寂静。
一架小轰炸机从浓烟弥漫的空中坠落,象一支蜡烛似的燃烧着,两条交叉的探照灯光把它紧紧盯住。
即刻就有两架轰炸机坠落下来,有一架带着一团烈火象一颗殒星似的笔直坠落下来,另一架兜了几个圈子,冒起黑烟盘旋起来,终于在半空中象远处的一串炮竹似的爆炸开来。
([美]沃克;《战争风云》弟 607—608页) 德国人的机枪疯狂地扫射着。
许多爆炸开的黑色烟柱子,在直径有一哩来宽的、已经被打得坑洼不平的沙土地上,象旋风一样向空中卷去,进攻的人浪散开了,翻滚着,象水花一样从弹坑旁边分散刀:去,还是爬啊,爬啊…… 炮弹爆炸的黑色烟火越来越紧地扫荡着大地,榴霰弹的斜着飞出来的、刺耳的尖叫声越来越密地泼在进攻的人的身上,贴在地面上的机枪火力越来越残忍地扫射着。
他们打击进攻的人,不许进攻的人靠近铁丝网。
果然就没有能靠近。
十六道波浪只有最后的三道算是滚到了跟前,但是这三道波浪一滚到破烂不堪的铁丝网(许多用铁丝缠着的烧焦的柱子都朝天空竖立着)前面,就象是被碰得粉碎了似的;变成一条一条的小河、一滴一滴的雨点倒流回来…… ([苏]肖洛霍夫:《静静的 顿河》第524—525页) 词:白骨露野 露:暴露;野:野外。
死人的白骨暴露在野外。
形容战争或灾难所造成的悲惨景象兵戈扰攘 兵戈:武器,指战争;扰攘:纷乱。
形容战争时期社会动荡混乱兵无常势 兵:战争;常:常规、不变;势:形势。
指用兵作战没有一成不变的方式。
指根据敌情采取灵活对策刀枪入库 没有战争,不用武备;和平麻痹,解除武装,不作戒备兵戎相见 兵戎:武器。
以武力相见。
指用战争解决问题。
兵荒马乱 荒、乱:指社会秩序不安定。
形容战争期间社会混乱不安的景象。
兵连祸结 兵:战争;连:接连;结:相联。
战争接连不断,带来了无穷的灾祸。
赤地千里 赤:空。
形容天灾或战争造成大量土地荒凉的景象。
楚界汉河 楚、汉相争中双方控制地区之间的地界与河流。
后常比喻战争的前线。
春秋无义战 春秋时代没有正义的战争。
也泛指非正义战争。
大动干戈 大规模地进行战争。
比喻大张声势地行事。
倒载干戈 倒:把锋刃向里倒插着;载:陈设,放置;干戈:古代的两种兵器,泛指武器。
把武器倒着放起来,比喻没有战争,天下太平。
放牛归马 把作战用的牛马牧放。
比喻战争结束,不再用兵。
风尘之变 风尘:比喻战乱。
指战争的灾乱。
烽火四起 战争的火焰从四面八方燃烧起来。
形容边防不安宁,四处有敌人进犯。
烽火连年 烽火:古时边防报警的烟火。
比喻战火或战争。
指战火连年不断。
归马放牛 把作战用的牛马牧放。
比喻战争结束,不再用兵。
化干戈为玉帛 比喻使战争转变为和平。
祸结兵连 结:相联;兵:战争;连:接连。
战争接连不断,带来了无穷的灾祸。
金戈铁马 戈闪耀着金光,马配备了铁甲。
比喻战争。
也形容战士持枪驰马的雄姿。
龙血玄黄 比喻战争激烈,血流成河。
连天烽火 烽火:古时边防报警的烟火,比喻战火或战争。
形容战火烧遍各地。
穷兵黩武 穷:竭尽;黩:随便,任意。
随意使用武力,不断发动侵略战争。
形容极其好战。
散兵游勇 勇:清代指战争期间临时招募的士兵。
原指没有统帅的逃散士兵。
现有指没有组织的集体队伍里独自行动的人。
休养生息 休养:何处保养;生息:人口繁殖。
指在战争或社会大动荡之后,减轻人民负担,安定生活,恢复元气。
以战去战 用战争消灭战争。
以逸待劳 逸:安闲;劳:疲劳。
指在战争中做好充分准备,养精蓄锐,等疲乏的敌人来犯时给以迎头痛击。
枕戈寝甲 枕着戈、穿着铠甲睡。
形容经常生活在战争之中。
兵慌马乱 形容战争期间社会混乱不安的景象。
伐罪吊民 伐:讨伐。
吊:慰问。
讨伐有罪,拯救百姓。
常用以作为发动战争的口号干戈载戢 干戈:古代的兵器。
指武器。
载:虚词。
戢:聚藏。
把武器收藏起来。
比喻不再进行战争动用武力了。
描写战争环境的句子【要惨烈一些,最好有死人,有秃鹰】
十八层地狱解 地狱(梵语naraka)十八泥犁有十八个地狱,何等为十八呢
就是光就居虚略、桑居都、楼、房卒、草乌卑次、都卢难旦、不卢半呼、乌竟都、泥卢都、乌略、乌满、乌藉、乌呼、须健居、末都干直呼、区通途、陈莫。
这些都是梵音,全部是一些刀兵杀伤,大火大热、大寒大冻、大坑大谷等的刑罚。
以下是详细介绍: 第一层,拔舌地狱: 凡在世之人,挑拨离间,诽谤害人,油嘴滑舌,巧言相辨,说谎骗人。
死后被打入拔舌地狱,小鬼掰开来人的嘴,用铁钳夹住舌头,生生拔下,非一下拔下,而是拉长,慢拽......后入剪刀地狱,铁树地狱。
第二层,剪刀地狱: 在阳间,若妇人的丈夫不幸提前死去,她便守了寡,你若唆使她再嫁,或是为她牵线搭桥,那么你死后就会被打入剪刀地狱,剪断你的十个手指
更不用说她的丈夫还没死,就向《水浒传》中的王婆,潘金莲本无意勾引西门庆,王婆却唆使她讨好西门大官人,并赠予她毒药,毒害武大郎。
且不说潘金莲,西门庆下场如何,单讲王婆,剪刀地狱够她一戗
第三层,铁树地狱: 凡在世时离间骨肉,挑唆父子,兄弟,姐妹夫妻不和之人,死后入铁树地狱。
树上皆利刃,自来后背皮下挑入,吊于铁树之上。
待此过后,还要入拔舌地狱,蒸笼地狱。
第四层,孽镜地狱: 如果在阳世犯了罪,若其不吐真情,或是走通门路,上下打点暪天过海,就算其逃过了惩罚,逃亡一生也终有死那天吧
到地府报道,打入孽镜地狱,照此镜而显现罪状。
然后分别打入不同地狱受罪。
第五层,蒸笼地狱: 有种人,平日里家长里短,以讹传讹,陷害,诽谤他人。
就是人们常说的长舌妇。
这种人死后,则被打入蒸笼地狱,投入蒸笼里蒸。
不但如此,蒸过以后,冷风吹过,重塑人身,带入拔舌地狱。
第六层,铜柱地狱: 恶意纵火或为毁灭罪证,报复,放火害命者,死后打入铜柱地狱。
小鬼们扒光你的衣服,让你裸体抱住一根直径一米,高两米的铜柱筒。
在筒内燃烧炭火,并不停扇扇鼓风,很快铜柱筒通红……看过《封神榜》吗
苏妲己的炮烙,到此你肯定激灵一下。
第七层,刀山地狱: 亵渎神灵者,你不信没关系,但你不能亵渎他;杀牲者,别提杀人,就说你生前杀过牛呀,马呀,猫,狗,因为它们也是生命,也许它们的前生也是人或许还是你的......因为阴司不同于阳间,那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牛,马,猫,狗以及人,来者统称为生灵。
犯以上二罪之一者,死后被打入刀山地狱,脱光衣物,令其赤身裸体爬上刀山......视其罪过轻重,也许“常驻”刀山之上。
第八层,冰山地狱: 凡谋害亲夫,与人通奸,恶意堕胎的恶妇,死后打入冰山地狱。
令其脱光衣服,裸体上冰山。
另外还有赌博成性,不孝敬父母,不仁不义之人,令其裸体上冰山。
潘金莲定在
第九层,油锅地狱: 卖淫嫖*,盗贼抢劫,欺善凌弱,拐骗妇女儿童,诬告诽谤他人,谋占他人财产,妻室之人,死后打入油锅地狱,剥光衣服投入热油锅内翻炸,啪,啪直响
依据情节轻重,判炸N遍......有时罪孽深重之人,刚从冰山里出来,又被小鬼押送到油锅地狱里暖和暖和…… 平常人们所说的十八层地狱,数目是对了,但从意义上却却不见得理解。
《十八泥犁经》中讲到这十八层的差别,最主要不在于空间的上下,而在于时间和刑法上的不同,尤其时间上。
若与阳世的时间比教,第一层地狱是以人间的三千七百五十年为一年,在这里的众生必须此生活一万年,想要早死一天都不行,而这一万岁就相当于阴间的一百三十五忆年。
而由于地狱的时间和寿命都是依次倍增的,所以,到了第十八层地狱,便以忆忆忆年为单位,如此长期的受刑时间,可说是名符其实的万劫不复,痛苦和残酷的景象,是世人所难以想像和理解的。
第十层,牛坑地狱: 这是一层为畜生申冤的地狱。
凡在世之人随意诸杀牲畜,把你的快乐建立在它们的痛苦上。
那么好,死后打入牛坑地狱。
投入坑中,数只野牛袭来,牛角顶,牛蹄踩......(本人认为是最舒服的一层了。
) 另据记载,与之相反的还有名为“刀船地狱”的,未在此十八层地狱之列,后面将补充。
第十一层,石压地狱: 若在世之人,产下一婴儿,无论是何原因,如婴儿天生呆傻,残疾;或是因重男轻女等原因,将婴儿溺死,抛弃。
这种人死后打入石压地狱。
为一方形大石池(槽),上用绳索吊一与之大小相同的巨石,将人放入池中,用斧砍断绳索...... 第十二层,舂臼地狱: 此狱颇为稀奇,就是人在世时,如果你浪费粮食,糟踏五谷,比如说吃剩的酒席随意倒掉,或是不喜欢吃的东西吃两口就扔掉。
死后将打入舂臼地狱,放入臼内舂杀。
稀奇的是如果你吃饭的时候说话,特别是脏话,秽语,骂街,死后同样打入舂臼地狱受罪。
所以提醒大家,吃饭的时候最好不要说话,特别是骂街。
第十三层,血池地狱: 凡不尊敬他人,不孝敬父母,不正直,歪门邪道之人,死后将打入血池地狱。
投入血池中受苦。
我也不大明白,这里说凡难产,吐血,流血而死之人,死后也投入血池中受苦
第十四层,枉死地狱: 要知道,作为人身来到这个世界是非常不容易的,是阎王爷给你的机会。
如果你不珍惜,去自杀,如割脉死,服毒死,上吊死等人,激怒阎王爷,死后打入枉死牢狱。
就再也别想为人了。
我劝戒在世的人,遇到多大的困难,也要顽强的活下去,自杀是懦弱的表现。
特别是那些殉情的傻小子们。
第十五层,磔刑地狱: 现在不多见了,不过此罪过很大。
即挖坟掘墓之人,死后将打入磔刑地狱,处磔刑。
第十六层,火山地狱: 这一层比较广泛,损公肥私,行贿受贿,偷鸡摸狗,抢劫钱财,放火之人,死后将打入火山地狱。
被赶入火山之中活烧而不死。
另外还有犯戒的和尚,道士。
也被赶入火山之中。
(这层应该人满为患了。
) 第十七层,石磨地狱: 糟踏五谷,贼人小偷,贪官污吏,欺压百姓之人死后将打入石磨地狱。
磨成肉酱。
后重塑人身再磨
另外还有吃荤的和尚,道士皆如此。
第十八层,刀锯地狱: 偷工减料,欺上瞒下,拐诱妇女儿童,买卖不公之人,死后将打入刀锯地狱。
把来人衣服脱光,呈“大”字形捆绑于四根木桩之上,由裆部开始至头部,用锯锯毙。
更恐惧被关押的时间: 十八地狱是以受罪时间的长短,与罪行等级轻重而排列,若随最短时间的光就居地狱之寿命而言,其一日等于人间三千七百五十岁,三十日为一月,十二月为一年,经一万岁,也就是人间一百三十五忆年,才命终出狱,逐次往后推,每一地狱各各比前一地狱,增苦二十倍,增寿一倍,到了十八地狱时,简直苦得无法形容,并也无法计算出狱的日期了。
求描写死人的片段
雨还在不停的下,森林里显得阴森森的冷清。
雨水顺着树干往下流,然后汇集在树脚。
大概是因为长期的浸泡,树脚下发出了腐木的恶臭。
顺着树脚往前看是一具腐败的尸体,浑身散发着恶臭,皮肤早已腐烂不堪。
似乎旁边还有几种不知名的动物在撕咬死尸的肉浓浓的蝇蛆闻开始慢慢散发,许多白色的蝇蛆在尸体上揉动,好像几万只交汇在一起。
死尸睁着充满血丝的双眼,嘴巴张的很大,似乎死前受过巨大的痛苦,凌乱的头发夹杂着鲜血的泥土,显得异常的凄凉。
死尸的四肢已经不见了,应该是被动物给吃掉的。
乌鸦在树枝上低叫,令人毛骨悚然。
死尸的肚子正被乌鸦给剖开,几只乌鸦飞下来食用,一条条鲜血淋淋的肠子被扯了出来。
乌鸦欢快的毫无顾忌的享用着美食,嘴角边似乎还挂着点点血迹。
没有人知道这具不知名的死尸是怎么死的,不过在死尸的身边却有一支猎枪。
。
。
。
。
。
。
写小说 描写人要死亡的句子 长一点 急急急急急
漫无边际是一丝一丝拼命往里钻的冷,仿佛冷到里去。
每一块骨头都好像得脆了。
每动一下都好似骨头碎掉的疼,疼的钻心。
阴寒的冷,冷得入骨。
不一会儿,却又变成一阵突如其来的剧烈疼痛,更可怕的是自己的手脚都不能动,剧烈的疼痛好像是要把她碾断拉碎,无论什么地方都痛。
每一分钟,每一秒都无比漫长。
她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疼痛,只愿赶快死去,也不要承受这样的疼痛。
---------------------------------------------------------------------------------------------------------------------刀片闪出冷冷的寒光,往苍白的手腕处狠狠划下
手腕裂开了一道狭长的口子,煞白煞白,慢慢地,鲜血从伤口里沁出,然后,鲜血突然湍急了起来,喷涌而出,如迸裂一般
一滴…… 一滴…… 一滴…… 顺着手腕…… 血珠滴落在温热的水面…… 如同一朵朵在黑色的梦魇中绽开的……血红色的花朵…… ---------------------- 原来…… 这就叫做皮开肉绽啊…… 苍白的唇角勾出一抹轻柔的笑容,迸裂的肌肤,翻卷的血肉伤口,原来,即使皮开肉绽也是不会痛的,原来,鲜血流逝的感觉是平静而麻木的。
慢慢地,他闭上眼睛,流血的手腕慢慢滑进水面之下。
在温热的水中…… 伤口就永远不会凝结了吧…… 透明的水波。
一丝殷红的血线缓缓地从割裂的手腕处轻轻荡荡飘涌上来,源源不断地,鲜血如同一条细细长长的线在水中妖艳地摇曳,然后荡开,袅袅的白色雾气中,透明的水渐渐变成透明的红…… ------------------------ 白色的雾气从温热的水面轻柔地升腾而起。
血液将浴缸里的水染得暗红暗红。
身体越来越冷。
心脏仿佛被重重地压着喘不过气。
洛熙的眼前渐渐发黑,世界眩晕而狂乱,苍白的嘴唇微微干裂,呼吸也变得急促了起来。
水波将他全身包围着,湿透的白衬衣在水面下轻轻飘起衣角,他的身体濡湿而冰凉,从水龙头源源流下温水也无法让他感受到丝毫温度。
-------------------------- 温热的水涌出黑色大理石的浴缸…… 漫出在白瓷的地面…… 血红的…… 仿佛仍旧带着体温般的温度…… 唇片上最后的血色已经褪尽,眼前漆黑得什么都不再能够看得见,湿透的白色衬衣如脆弱的白色花瓣在水下轻轻飘荡,生命一丝一丝地流淌,只有那只滴着血的手,固执地,紧紧地抓着浴室中的电话,仿佛抓紧着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 鲜血…… 一滴一滴从手腕滴淌而下…… 漆黑的眩晕中…… ----------------------- 临死前就是想再看你一眼…… 温热的水流从水龙头源源不断地流淌…… 浴室里充满了白色的雾气…… 地面满是鲜红的血水…… 苍白淌血的手腕再也无法握住电话话筒,重重地跌进浴缸的水面之下,溅起一朵被血染红的水花…… --------------------------- 话筒在水面下轻飘飘地摇荡着。
“嘟——” “嘟——” 鲜血已经将浴缸里的水染成暗红色,不断地漫出去,温热的水不断地注入,那浸泡在水中的手腕伤口永远无法凝固,汩汩地,流着新鲜的血液…… 漆黑的眩晕中…… 心脏渐渐窒息无力…… 彻骨的寒冷…… 嘴唇惨白失血,洛熙苍白地躺在黑色浴缸里,水波将透明的衣角轻轻飘起,缓缓地,他如纸般雪白的脸,无力地,垂向一侧,任由死亡将他最后的清明带走…… ----------------------- 会不会…… “嘟、嘟、嘟、嘟……” 水面下的话筒沉闷地传来被挂断的声音,就像最后一根丝线也断开了,再无任何牵挂,安安静静地离去…… ------------------ 来到我身边呢…… 她们迟疑地走到浴室门口,半开的门,从里面淌出来的水如被鲜血染红了般刺目惊心,隐约可以看到黑色的大理石浴缸里,有人影苍白得仿佛…… 仿佛…… 早已死去……
描写古代被人追杀的句子
黑起来了,天上挂着的缺月愈发晻曀,上和官道的衔接处有两个灯笼高高挂着照明。
从散发光可以看到小镇的牌坊--桃源镇。
此时离更夫刚打完五更的鸣锣声不久,忽然,北面镇外官道上的传来了一阵急促马蹄声。
只见,一名男子疾驰至镇门口时,抬眼看了一眼牌坊,翻身下马便以轻功跃向镇旁的树林里,任由马儿冲进小镇上。
因为他知道,如果再跑下去的话,他一定逃不过身后那群黑衣人的追杀。
在该男子进入竹林几个弹指间,一群黑衣人便蜂拥而至,以三人为一组亦跟着跃进树林里。
虽然江湖上一直有着“逢林勿入”的说法,可是这时已然顾不上了,只要能杀了该男子,不管付出什么代价。
冲进竹林的这名男子越跑越踉跄,却有着止不住的疑问,之前便被偷袭,又被这群黑衣人追杀,现在的自己根本就无法敌对这二十几个黑衣人,只是可恨啊,竟不知道是谁所派来了。
不过幸好天公作美,这昏暗的天色,对自己很有利,而眼下只有先找个地方藏起来,应付眼前的难关,不然即便没被他们杀死,自己也会被这伤势拖累而死。
扑的一声,这名男子忽然倒地,却也非常郁闷,若是不曾受伤,也不会被这树藤绊倒了,不过要是没受伤也不会被追的这么赶了。
咦,树洞。
在起来之时,忽然发现旁边的树底有个口子,这名男子果断过去,试着躲进树洞里,若是再不找个地儿躲躲,跑也跑不了了。
这树洞说大不大,说小却也不小了,足够一个小少年蹲着了,自己缩缩还是能躲躲的,要是这还躲不过去,只能说天要灭我了。
唉,跑也不能跑,先就地疗伤吧。
极盗者死人了么
死了几个
在哪个场景中死的
楼上的好傻 人家问的是真实的死亡 替身在拍电影极限运动中死了三个 真的死了 在拍摄过程中
描写葬礼的句子
拿着“引”字白纸帖的吴府执事人们,身上是黑大布的长褂,腰间扣 着老大厚重又长又阔整段白布做成的一根腰带,在烈日底下穿梭似的 刚从大门口走到作为灵堂的大客厅前,便又赶回到犬门口再“引”进新 的吊客——一个个都累得满头大汗了。
十点半钟以前,这一班的八个 人有时还能在大门口那班“鼓乐手”旁边的木长凳上尖着屁股坐这么一二分钟,撩起腰间的白布带来擦脸上的汗,又用那“引”字的白纸帖代替 扇子,透一口气,抱怨吴三老爷不肯多用几个人,可是一到了毒太阳直 射头顶的时候,吊客象潮水一般涌到,大门口以及灵堂前的两班鼓乐手 不换气似的吹着打着,这班“引”路的执事人们便简直成为来来往往跑 着的机器,连抱怨吴三老爷的念头也没工夫去想了,至多是偶然望一望 灵堂前伺候的六个执事人,暗暗羡慕他们的运气好。
汽车的喇叭叫,笛子,唢呐,小班锣,混合着的“哀乐”,当差们挤来 挤去高呼着“某处倒茶,某处开汽水”的叫声,发车饭钱处的争吵,大门 口巡捕暗探赶走闲杂人们的吆喝;烟卷的辣味,人身上的汗臭;都结成一片,弥漫了吴公馆的各厅各室以及那个占地八九亩的园子。
(茅盾: 《子夜》第31页) 举行仪式时,我感到一种恐慌,一种对将来的预感,我站不住了。
最后尸首装入棺材钉起来。
然后助葬的人把棺材放在柩车上,就出发 了。
我只伴送着走完了一条街。
走到那儿,赶车的突然把车赶得飞跑 起来,老人跟着柩车跑——大声啼哭,可是跑的动作时时使哭声变得颤 抖,而且。
忽断忽续的。
后来他的帽子掉了,可怜的老人并不停下来拾, 虽然雨打在他头上,又刮起风来,雪雨不住地刺痛,击打他的脸。
他从 柩车这边跑到那边,好象他不了解这件残忍的事一样——他的旧大衣 的两边给风吹起来象一对翅膀似的。
衣服的每一个口袋里都装着书凸起来,他的胳膊底下挟着一本特别大的书,他紧紧的抱在胸前。
送葬的 行列经过时,过路人脱下帽子,在胸前划·十字,有些过路人站住惊愕的 凝视着那司·怜的老人。
不时有书从他的口袋里滑出来,掉到污泥里,因 此,有人叫住他,叫他注意他的书掉了,他就站住,把书拾起来,还是跑 去尾随着柩车。
在街的一个角,一个褴褛的老太婆紧跟着他,最后一直 到柩车拐弯,我的眼睛看不见了。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穷人>>笫 64—65页) 卡拉特特的妻子决不能就把丈夫一人丢在坟墓里。
而且那不幸的女人自己也不愿意独自一人活下去。
这是风俗,同时也是职责,这种殉夫的事例在新西兰的历史里是常见的。
卡拉特特的妻子出场了。
她还很年轻。
她的头发乱披在肩膀上, 又号啕,又哽咽,哀声震天。
她一面啼哭,一面声诉,模模糊湖的活音, 缠缠绵绵的悼念、断断续续的语句都颂扬着死者的品德,哀痛到极点 时,她躺到土墩脚下,把头在地上直擂。
这时,啃骨魔走到了她的跟前。
忽然那可怜的牺牲者又想爬起来, 但是那酋长手里舞动“木擂”——一种可怕的大木槌——一下子又把地 打倒下去。
她气绝了。
([法]凡尔纳:《格兰特船长的儿女》第664页) 他向围立在墓穴四周的人群扫了一眼,全是警察,全都穿着便服, 同样的雨衣,同样的笔挺的黑帽子,雨伞象佩剑一般握在手里,这些奇 异的守灵人,不知风从哪儿把他们刮来的,他们的忠实显得不真实。
在他们后边,排列成梯队的市政府乐队,穿着黑红二色的制服,是匆匆召集来的,都拚命设法把自己金色的乐器在外套下保护起来。
他们就这 样围在棺材周围,它平放在那边,一只木制的匣子,没有花圈,没有鲜 花,但却是唯一的温暖所在,正在这一无休止的雨滴之中安葬,雨水单调地拍溅着地面,始终如一,永无尽止。
牧师早巳读完了。
没有人注意 到。
这里只有雨水,人们只听到雨声。
牧师咳嗽起来,先是一声,接着好几声。
于是低音喇叭、长喇叭、号角、短号,低音笛一齐奏鸣,傲慢而雄壮,乐器在雨帘中闪着金光,但是它们也沉没了,消散了,停止了。
一切全退缩在雨伞之下,雨衣之下了。
雨始终不断地下着。
鞋子陷在泥泞之中,雨水汇成小河流入空的墓穴。
([瑞士]杜仑马特:《法官和他 的刽子手》第45页) 举行葬礼的一切早已准备好了。
元老们把灵轿在火葬的柴堆旁边 放了下来。
范莱丽雅走了上去,阖上了死者的眼皮,又按照当时的风 俗,把一个铜币塞到死人的嘴里,以便他付给兴隆,充作渡过波浪汹涌 的阿凯伦河的船钱。
接着,这位寡妇在死者的嘴唇上吻了一下,按照风俗大声说:“再会了!按照老天安排的次序,我们会跟着你来的。
”乐工开 始演奏哀乐,那些奉献人就在乐声中把好些指定作为牺牲的动物牵过 来杀死,把它们的鲜血与牛奶、蜜和葡萄酒掺和在一起,然后拿来洒在 火葬的柴堆周围。
这一切完毕以后,送葬的人就开始向柴堆上面浇香油,抛掷种种香料,堆上不计其数的桂冠和花圈。
花圈多极了,不但盖满了整个柴堆, 而且在柴堆四周厚厚地叠了起来。
一阵轰雷一般的鼓掌声滚过马尔斯广场,回答这位年轻的凯旋者 和征服阿非利加的元帅对死者所表示的敬意。
一阵火焰突然进发出 来,随即迅速地蔓延开去。
终于,整个柴堆发出无数蜿蜒飘动的火舌, 而且被一阵阵云雾一般的芳香的浓烟所笼罩了。
([意]乔万尼奥里, 《斯巴达克思》第246页) 泰戈尔达斯·穆克吉的年老妻子在连续发了七天高烧之后死了。
老穆克吉先生经营粮食生意发了大财。
他的四个儿子、三个女儿、孙男 孙女、女婿和亲戚朋友以及仆人们全都赶来了,乱哄哄地象是在过大节 日。
村子里的人们也成群结队地赶来参观这一隆重而体面的丧仪。
女儿们哭泣着在母亲的脚跖上浓浓地涂上了一层胭脂,在她的中 分的发缝里抹上了一道朱砂。
儿媳妇们在婆婆的前额上敷上了檀香膏 沫,替婆婆裹上了贵重的纱丽之后,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服,把披在头 上的纱巾拉得低低的,向婆婆行了最后的摸足礼。
五彩缤纷的鲜花,绿色的嫩叶,浓郁的檀香,各色的花环,一片‘喧哗 声里使人嗅不出悲哀的气息——这似乎是豪门的主妇在五十年后又一 次扮作新嫁娘起程到丈夫家里去。
老穆克吉先生平静地向自己老伴做了最后的告别,暗暗地抹去了两滴泪水,开始劝慰起悲哀地哭泣着的女儿和儿媳妇来。
“诃利!诃利!”闷雷般的颂赞声震撼着清展的天空,整个村子的人们眼随着丧仪的行列出发了…… 火葬场在村外河边沙滩上。
在那里焚烧尸体需用的木柴、檀香屑, 酥油、蜂蜜、松香、娑罗树脂……早巳准备妥当。
……当尸体被安置在宽大、堂皇的焚尸的柴堆上的时侯……大家齐声呼唤着“诃利”的圣名,儿子拿着被婆罗门祭师的经咒净化了的火把,点起了葬火……儿子手里的火I这真是谈何容易啊J把丈夫、儿子、 女儿、孙男孙女、亲戚朋友、仆人——尘世间的一切,整个留在熊熊的火焰里,婆罗门老太太升天去了。
([印]查特吉:《奥帕吉的天堂》 《外 国短篇小说》中册第462—4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