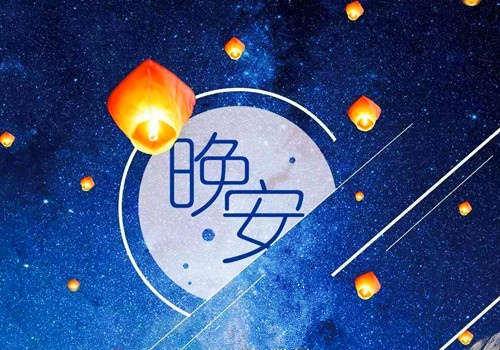荀慧生的资料
荀慧生(1900~1968) 男,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
原名词,又名秉彝、秉超,字慧生,号留香,艺名白牡丹。
出生于河北省东光县(现为阜成县)一个捻售线香的手工业之家。
幼年家贫无以生计。
1907年随父母到天津谋生,父亲将他与兄慧荣卖予小桃红梆子戏班学戏。
不久其兄不堪忍受打骂私自逃走,只剩慧生,后被卖给花旦为私房徒弟,自此,荀慧生沦为家奴,吃尽苦头,但他仍以巨大的耐力与毅力坚持每天练功。
夏天穿棉袄,冬天穿单衣,头顶大碗,足履冰水,点香火头练转眼珠,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苦功练出了硬本领,唱、念、做、打无一不精。
1909年,荀慧生以“白牡丹”艺名随师常在冀中、冀东一带农村市镇唱庙会和野台子戏。
1910年荀慧生随师进京,先后搭庆寿和、义顺和、鸿顺和、天庆和等梆子班。
辛亥革命前期他去天津曾同革命戏剧家王钟声,同台演出《革命家庭》、《黑奴恨》等戏,后向陈桐云、李寿山、程继先学习京昆艺术,直到十七岁才独立成班。
1918年与刘鸿升、侯喜瑞、梅兰芳、程继先开始合作,演出《胭脂虎》、《霓虹关》等戏,又同杨小楼、余叔岩、王凤卿、高庆奎、朱桂芳等合作,并拜王瑶卿门下学习正工青衣。
同年杨小楼应上海天蟾舞台之邀和尚小云、谭小培合作演出,请荀慧生担任“刀马旦”,公演引起轰动,人称“三小一白”(即小楼、小云、小培和牡丹)。
荀慧生的表演生动活泼,扮相俊俏,使上海观众耳目一新,被赞为“誉满春申”,后又与周信芳、冯子和、盖叫天、小达子等人合作,演出《赵五娘》、《劈山救母》、《九曲桥》、《杨乃武与小白菜》等戏,名震沪上。
上海国画大师吴昌硕同知名人士严独鹤、舒舍予也为宣传和扩大荀慧生的艺术影响到处奔走。
荀慧生喜欢作画,1924年正式拜吴昌硕为师,他又向齐白石、陈半丁、傅抱石、李苦禅、王雪涛等名师求教,丰富了他的艺术生活,提高了他的艺术素养。
1927年北京报界举办京剧旦行评选,他与梅、尚、程一起被誉为“四大名旦”,这也标志着他艺术走向成熟,得到社会肯定,赢得了观众的赞赏。
他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在剧本、唱腔、表演、念白、到服饰等方面都进行了创新的实践与探索。
他演出的剧目有三百多出,主要包括《红娘》、《红楼二尤》、《杜十娘》、《荀灌娘》、《钗头凤》、《十三妹》、《玉堂春》、《金玉奴》、《得意缘》、《卓文君》等。
在唱腔艺术方面荀慧生大胆破除传统局限,发挥个人嗓音特长,吸取昆、梆、汉、川等曲调旋律,大胆创新。
这不是简单的一曲多用,而是从生活出发,从人物感情与心境出发,字正腔圆,腔随情出,令人着迷。
他善于使用上滑下滑的装饰音,听来俏丽、轻盈、谐趣具有特殊的韵味。
他还十分注重道白艺术,吐字清晰,声情并貌,他创造出融韵白、京白为一体的念白,韵调别致,具有特殊的表现力。
表演方面他强调“演人不演行”,不受行当限制,根据需要进行必要的突破,他塑造的许多少女、少妇的艺术形象,具有大众化、生活化的特点。
娇雅妩媚、清秀俊美、风格各异。
建国后,荀慧生遵照周总理签署的戏曲改革指示,为京剧艺术改革做出了大量工作。
1952年获第一届戏曲观摩大会老艺术家表演奖。
他历任中国戏曲家协会艺委会副主任,北京市戏曲研究所所长,河北省梆子剧院院长,河北省政协委员,北京市文联常务理事,北京市戏曲编导委员会主任等职。
荀慧生一生收徒之众,不计其数,他指导和亲自传授的后人、学生、徒弟有:吴纪敏、金淑华、李薇华、荀令莱、宋德珠、毛世来、童芷苓、李玉茹、李玉芝、吴素秋、赵燕侠、小王玉蓉、张正芳、尚明珠、厉慧敏、陆正梅、宋长荣、李妙春等等,还有许多人虽未拜师,但多得其亲授。
诞辰:1900年1月5日,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十二月初五日 逝世:1968年12月26日,农历戊申年十一月初七日
老舍先生为什么要跳湖
因为老舍惨遭毒打被家人冷言冷语对待,受到的不仅仅是身体上的伤害,更是心灵上的伤害
老舍诗集
正文 白云寺 北戴河赠四友诗 北行小诗 春游小诗 登太白楼 登岳阳楼 登岳阳楼题-三秋图 观豫剧《花打朝》 贺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 黄山奇 黄山小诗之一 黄山云 哭王礼锡先生 内蒙东部纪游 内蒙即景 汕头行 诗十五首 诗五首 诗三律 诗谢郭老秋雨中来访 蜀村小景 题全家福 题关良“凤姐图”诗 题静庐写秃松小品 向日本话剧团献诗 春节与北京曲艺团诸友欢聚得句 咏黄山 游海门-莲花峰 游秦皇岛 游日十七首 再集马派名剧-赠马连良 赠白土吾夫 赠北京晋阳饭庄 赠陈叔通 赠涤非词人 赠广州部队战士话剧团 赠湖南博物馆 赠梅阡 赠木下顺二 赠山月 赠汕头工艺美术陈列馆 赠申凤梅 赠沈柔坚 赠土歧善 赠王莹 赠荀慧生 赠友人归广州 致郭老 致章老 保民杀寇 保我河山 壁报诗 长期抵抗 成渝路上 慈母 打(游击队歌) 打刀曲 附录 致友人函 歌唱伟大的党 歌声(散文诗) 鬼曲 国葬 海外新声 红叶 教授 她记得 抗战民歌二首 空城计 礼物 恋歌 流离 蒙古青年进行曲 谜 怒 青年 青年突击队员 清明 日本撤兵了 山高挡不住太阳 蜀江船歌 痰迷新格 童谣二则 微笑 为和平而战 为小朋友们作歌 新春之歌 新青年 新诗(1) 新诗(2) 新诗(3) 新诗(4) 新诗(5) 雪中行军 音乐的生活 元旦铭 札兰屯的夏天 战 丈夫去当兵 致富神咒 祝贺北京解放十年 祝贺儿童节 咳咳,这算不算
请问,著名作家老舍先生为什么投湖自尽了?谢谢!
1966年7月,老舍病重,大口吐血,住进了北京。
8月23日,他挣扎着,像往常一样去北京市文联上班。
刚踏院,一位负责指挥的女红卫兵就发现了他,马上大叫起来:这是老舍
他们的主席
大反动权威
揪他上车
来不及作任何的申辩,老舍就和肖军、骆宾基、荀慧生等人一起,被拉到一个焚烧文化局戏曲道具的现场,接受批斗。
他们被挂上各样的牌子,跪在火堆周围,要他们接受“革命之火”的洗礼, 67岁的老舍支持不住,晕倒在地……没有同情,没有怜悯,反而认为他态度不老实——苏醒后的老舍,遭受的是新一轮折磨。
因为怕出人命,市文联设法将老舍接回,不料,文联大院早就有数百名红卫兵守在门口,迎接他的又是新一轮的皮带,拳头,凉鞋,唾沫……士可杀而不可辱。
他决定不再低头忍受,不再为自己辩护,他抬起血迹斑斑的头,愤怒地扔掉手中的牌子。
当然是新一轮的批判,当然是审问到深夜,当然是勒令他明早必须带着“现行反革命”的牌子到市文联接受新的批斗。
回到家中,当他夫人帮他清洗伤口时,老舍冷静地说:人民是理解我的。
这个时候的老舍,内心已经作出了抉择。
他一夜没睡。
让时光倒流。
1949年7月,曹禺、楼适夷遵党组织的嘱托,写信请他回国;1951年12月,北京市人民政府授予他“人民艺术家”的光荣称号;1959年的一个下午,周恩来总理突然出现在他的小院子里,亲切地询问老舍的健康情况,临走前,他严肃地对老舍的家人说,以后,不管老舍得了什么病,你都要马上向我汇报。
——俱往矣,新时代的仁慈与梦想。
现实已没有什么光荣可言,公理和人性已经退场,“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
”第二天,老舍没有举着“现行反革命”的牌子去文联,而是带着他亲自抄写的毛主席诗词去了北郊的太平湖,他在那里坐了整整一天。
晚上,他望着映满星光的湖水,终于向着湖心纵身一跃——堪恨秋肃夺英魂,秋水无情也吞声
赞美“青衣”的句子有哪些
原文: “这群有很的,也有五六十岁的。
虽然年纪不可一律雪花膏与香粉,寿数越高的越把粉擦得厚。
他们之中有贫也有富,不拘贫富,服装可都很讲究……还能在颜色上着想,衬上什么雪青的或深紫的。
他们一律都卷着袖口,为是好显显小褂的洁白。
大概是因为忌妒吧,他们才说小陈是“兔子”;其实据我看呢,这群人们倒更象“那个”呢。
” “那个”指的就是“兔子” 那时封建的社会思想是不容许同性XX的(会被认为是侮辱门第),所以也是一种隐讳作用性:雄的兔子可以和雄兔交配,也可以和雌兔交配,只是和雄兔交配不会受精。
每一个兔子都是这样。
说白了一点,就是只要是雄兔看到另一只或几只兔,不管是公母,都会去做就是了。
所以在古代,人们不知道同性恋这个词,就用兔子来代替。
《木兰辞》中便有“双兔傍地走,安能辩我是雌雄?”之说 显然老舍作品《兔》里所描写的那些个黑汉组织来的票友多是具有同性恋者的倾向,只是他们的表现在于将同性英俊男子做了示爱对象,因为小陈的唱几乎无一可取,而他的作派却非常了得。
只是要注意的是,同性恋者的美学标准在此是以异性之美来作为表征的。
比如小陈的“脸上还白净”、“他腼腆”,以及他的“嗓子就和根毛儿似的那么细,坐在最前面的人们也听不见一个字”这又一次说明了同性恋者的“爱慕”对方是以多元因素体现的。
有时候倏忽以为那些票友们爱恋的是小陈的女性一面,为异性之爱,却不然,那正是另外一种变化了的爱——男性中隐含着的女性因素,是为“中性”,或者通常被叫做“第三性”的那种。
染上恶习的票友正是指那的这些同性恋者. 老舍的女儿舍济提起《兔》,舍济的解释就只一句:他写的就是同性恋。
但小陈倒未必就有同性恋的心理或行为(至少小说里没有直接描写)仅是一众同性恋者贬损小陈而谣传他是“兔子”....... 关于男旦: 但明朝和清朝还有一点区别。
明朝乃至清初,富贵人家家里 养的戏班子较多,主人家根据爱好可以选择养男班还是女班。
比 如李渔家里、阮大铖家里、大观园里就是女班,杜少(慎
)卿 家里就养过男班。
(这里引用的有的是文学作品中人物,但也能 说明问题。
)清朝以后,府里头养的班子少了,许多戏班子开始 社会化,开始走江湖,艺人也职业化了。
这时候女班明显就不好 生存,由清一色妇女组成的戏班,远涉江湖不容易,同时成年的 妇女都要嫁人,嫁了人就不好再唱戏,所以女班肯定要衰落。
到 了京剧的繁荣时期,几乎全是男班了,所以男旦也就成了风气。
即使是到了民国,有许多坤角开始走红,但戏饭仍然不好吃。
女演员红了,愿意不愿意都要被人娶回家里。
梅夫人福芝芳以前就是坤角,嫁到梅家以后,也不唱戏了就是一例。
孟小冬要不和梅兰芳离婚,她以后的拜余,也不可能。
后嫁杜府以后,杜老板 也没有允许她再登台。
其他的女演员遭遇各不相同,但都十分地 难。
只有到了解放后,这个问题才彻底解决,女演员不但可以和 男演员同台,而且结婚后也可以光明正大地以唱戏为职业。
那么长一段时期,男旦在旦角领域占统治地位,他们取得的 成就肯定也是不凡的,这就不用说了。
现在很多人听戏时能够接 受老一辈的男旦,在现实生活中却厌恶这种以男做女的人物。
这 和男旦历史上一些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有关。
清朝时候,皇帝不许在京的官员嫖娼,却允许他们听戏。
一 些王公贵族大官之类的还则罢了,看戏就是看戏,自己没什么饥 渴可言。
而很多下层下吏,类似书办之流,上任不带家眷,客中难免寂寞,看戏时就有些不三不四的想法。
艺人爱财,也难免迎合,形成一时风气,在社会各阶层漫延。
在北京就有了许多江青同志津津乐道的相公堂子,相公(古代的民间对同性恋的不俚俗之称)主要就是学旦的幼伶。
这段历史直到民国才算结束。
人一提起男旦,就会想起这个,你说能不厌恶吗
但男旦的相公历史,也是受压迫受毒害的象征,这些被卖去学艺的苦孩子们有什么错
最近在网上为电视剧《荀慧生》的热播,网友对其中的猥亵男孩儿的情节展开了针锋相对的口水大战。
在中国极度开放的今天,人们的思想空前活跃,当局也给予人们一定的自由空间;所以说出现在电视剧中的情节是无可厚非的。
男女之间的激情戏,火辣辣的场面都能有立足之地,关于中性人的讨论甚至变性人的讨论都堂而皇之的登堂入室,难道电视剧中出现一些鲜为人知的情节就不可以吗
有些人是从事京剧男旦的演员工作,更为担心因此会引起社会上对于他们工作的误解
就更没必要了。
旧社会曾经把戏子位列妓女之后;也就是因为那时富豪和军阀们,玩女人已经腻歪了,就打起玩男人(小旦,也就是男扮女装的演员)的主意,再加上那时的艺人本身为了利益的驱使,不自重,也给人造成了很坏的影响;所以才有下九流的说法——戏子(也就是把演员)排在妓女的后边。
比妓女稍逊一筹,相差一等。
当然现在就不同了,都是大腕儿了,明星了,艺术家了;是众人追捧的super star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