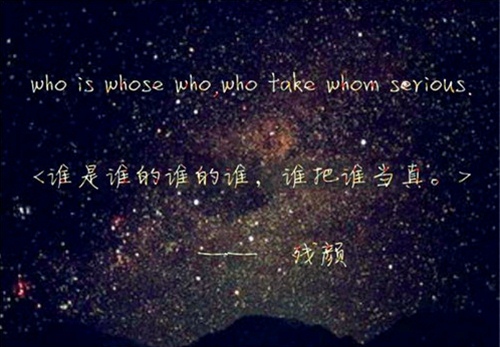
陈道明,1955年4月26日出生于天津,国家一级演员。1985年,凭借电视剧《末代皇帝》被观众熟知,获得第7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男演员和第9届中国电视飞天奖优秀男主角。1990年,凭借《围城》获得全国制片厂第二届优秀电视剧评选最佳男主角奖,第十一届“飞天奖”最佳男主角奖。1999年,凭借《我的1919》获得第9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男演员、第20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男主角;2001年,陈道明凭借在《康熙王朝》中的演技获得了“美菱杯”观众最喜爱的男演员评选银奖和第二届阳光健康电视明星;[1]2010年,出演《唐山大地震》,凭借该片获得第4届亚太电影大奖最佳男演员;2012年,主演电视剧《楚汉传奇》;2014年,与巩俐主演张艺谋执导的电影《归来》。
陈道明的戏看了不少,他写的文字还是头一回读到。
在陈道明准备步入花甲之年的时候,他写的一篇人生感慨:做点无用的事儿。
以下是原文:
一晃都年近六旬了,说不注意身心健康那是假的,但上升到正经八百的“养生”高度,又似乎不那么对味儿,因为我做的,用冯小刚的话说都是“奇技淫巧以悦妇孺”,不为无益之事,又何以遣有涯之生?
这观念打远了说,可能与我早年的经历有关。我生在天津一个中医世家,父亲是燕京大学毕业生,后在天津医科大学教英文。受家庭影响,我少年时期的理想是当律师、外交官、医生,人生规划里完全没有“演员”。但高中时为了躲避上山下乡,有个正经的城里饭碗,不得已报考了天津人艺话剧团。进剧团后也没有一鸣惊人,多数时间都在舞台上跑龙套,一跑就是六七年。
那时候演艺界都是吃大锅饭,主角和配角的收入相差不大,加上自我感觉“入错了行”,对出人头地没有什么奢望。人生起步阶段没有经历什么急功近利的熏陶,很自然地便学会了将很多东西看淡。不像现在的演员,接受了太多以竞争为主、甚至强调“你死我活”的教育,心理整个就跟着急功近利了。
其实不光演员,现在整个社会都得了“有用强迫症”,崇尚一切都以“有用”为标尺,有用学之,无用弃之……许多技能和它们原本提升自我、怡情悦性的初衷越行越远,于是社会变得越来越功利,人心变得越来越浮躁。
但这世界上许多美妙都是由无用之物带来的,一场猝不及防的春雨或许无用,却给人沁人心脾之感;刺绣和手工或许无用,却带给我们美感和惊喜;诗词歌赋或许无用,但它可以说中你的心声,抚慰你的哀伤……老子在《道德经》里也讲“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人的生命包含肉体和精神,前者是基础,后者是升华。与其一味追求有用之物,不如静下心来,细细品味无用之物带来的静谧和美好。心安,则身安。
我从小弹得一手好钢琴,喜欢到钟爱。只要在家,我每天要弹上两三个小时,兴致高时会弹四五个小时。我有一台珍藏版电子钢琴,无论去哪儿都会带着,在外拍戏间隙就会用它来代替钢琴,有时碰巧剧组有设备,也会弹弹手风琴、吹吹萨克斯。钢琴对我来说是绝对私密的朋友,混迹于社会,难免有郁结之事,无用的钢琴练习便成了我排解心中不平的利器。
进入中年后,我迷上了画画,没有门派,不讲章法。磨好墨汁,铺好宣纸,手握画笔,然后打开地图,回想多年来拍戏到过的地方,然后挥笔泼墨画山水。画好后贴在书房的墙上,一遍遍观赏、对比,直到自觉不错了,这幅方才作罢。又有言书画不分家,后来我又觉得书法很精妙,慢慢也迷上了,我现在最喜欢用毛笔抄写《道德经》之类的古籍,一边抄写,一边默读,入脑入心,很有意思。
我也相当钟情棋艺。从围棋、象棋、国际象棋到军棋、跳棋、斗兽棋、飞行棋、五子棋、华容道棋……算得上无所不会吧。不过我只喜欢与自己下棋,人生如棋,下好下坏全在自己。借下棋,观天地之深广,思人生之浅狭。棋中有棋,棋里养生,抛却胜负,无心则胜,无心则乐,无心则寿。
偶尔,我也会做点手工。我家里有一个很大的房间专门用来放置糖人、面人,木工、裁缝所用的工具,这几项手工活我都还算拿手。女儿常年在国外,想她的时候就会浇个糖人,捏个面人,或者干脆穿针引线给她裁剪一身衣裳,聊解相思之苦,也算自我宽慰吧。当然,我更乐意干的是为妻子缝制各种皮质包包。我妻子4年前退休了,喜欢弄点十字绣之类的,有时我们夫妻俩就同坐窗下,她绣她的.花草,我裁我的皮包,窗外落叶无声,屋内时光静好,很有一种让人心动的美感。
其实我最大的梦想是写杂文。在现当代作家里我最喜欢鲁迅的杂文,《鲁迅全集》我全部读过。在阴雨天,我愿意一个人写东西。但写杂文一直没有尝试过,觉得很难,要有一个环境和心境,先要把心洗干净,无杂念,看着窗外的飘雪,身上披着棉袄,身后一盏纸糊灯罩的灯,一支烟燃着,但不吸,手里一支沉甸甸的笔,写一句,思三思,踱五步,方可出杂文。
有人说工作那么忙,时间那么紧,去哪儿找闲情逸致?其实还是鲁迅的那句话:“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只要挤总是有的。”我这个人不沾烟、酒、牌,不喜欢应酬,从不光顾酒吧、歌舞厅之类的娱乐场所,很少参加饭局,即使参加,一般也不超过半小时。工作之外,剩下的便只是读书、练字、弹琴、下棋,为女儿做衣服,为妻子裁皮包了。
这些或许都是“奇技淫巧以悦妇孺”的事儿,远不如一场饭局来得更有用,但人活着,需要给自己的心灵安一个家,让自己保持自我、本我、真我。无用方得从容,洁净如初的心灵及丰富多彩的精神世界才能成就百毒不侵的自己,心没病,身体自然安康。如果要说养生的秘密,这就是我越活越年轻的“奥秘”。
陈道明拍戏有不少“怪癖”。怪僻之一是不脱戏服。一旦进入剧组,换上角色的衣服,陈道明就不会轻易脱下来。在《归来》的整个拍摄期,他一直穿着陆焉识的破棉袄,下了戏也不例外,回酒店时常常引来侧目。这个习惯并不是在拍《归来》时才养成的,从《康熙大帝》到《楚汉传奇》,无不如此。拍《楚汉传奇》是在冬天,陈道明就穿一条单裤,因为他觉得戏中的场景是在秋天,多穿一条裤子会影响视觉效果。就为这,拍完戏就得了重感冒。在片场他总是穿着刘邦那套戏服,永远是整装待发的样子。之所以如此。陈道明的理由是:“进入剧组后,演员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把戏服穿成自己的衣服,把道具变成自己的手持物,只有这样,这些东西才能‘贴神’,而不像借来或租来的.。”
陈道明演戏的另一个怪癖是爱站着。在片场,稍微大牌点的演员都有专属的椅子,供休息用,陈道明却总是站着。《楚汉传奇》导演高希希透露,陈道明在片场一站就是一天。陈道明的“站神”精神,让剧组上下都肃然起敬。“你说陈道明站着,我们谁敢坐下?剧组就集体陪站呗!”高希希笑着表示,这算是一部“站着拍完的戏”。排练话剧《喜剧的忧伤》也一样,第一天排了7个小时,陈道明就没坐下过。
这些别人眼中的“怪癖”,在陈道明看来,只是演员的职业特性。他说:“演员这个职业是有职业性的,职业性有时候要付出代价。不都是光环,不都是掌声和鲜花。演员不能只带脸进现场,一定要带着脑袋进现场,因为演员不是演脸的,而是演心的。”
近日曾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品《平凡的世界》被搬上了荧屏,虽然因旁白、角色造型等问题该剧口碑毁誉参半,但剧中主演王雷以一口纯正的陕北腔、逼真的农民形象赢得了一片赞扬。而王雷的妻子李小萌也在剧中扮演了一位“村妇”,只是这个村妇是王雷的弟
【谈剧集】 从演弟弟变成演哥哥
导演让我来演男一号
在电视剧《平凡的世界》中,王雷饰演的孙少安,成为剧中唯一一位将陕北方言贯穿始终的角色,且不只是口音,无论是服装造型还是神态,都符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形象。谈起角色,王雷表示最初中意的是演孙少平,但看完原著后改了主意:“孙少安这个人物是中国式的经典,甚至不输任何一个莎士比亚剧中的角色。”
新京报:第一次接触《平凡的世界》是什么时候?
王雷:当时我在上艺校,中专二年级,表演课老师给我们布置作业,把小说改成片段来演,我就看到了《平凡的世界》。当时一看,哎哟,书那么厚,要改可太费劲了,就粗略
新京报:当时你选择演弟弟孙少平?
王雷:对,当时改小说主要以改爱情戏为主,因为别的不懂啊,就看谁和谁爱得死去活来就改谁的呗。因为年龄原因,我看书时对孙少平这个人物感觉偏多一些,我看孙少平谈谈恋爱、谈谈理想,蛮有意思。但对孙少安没什么兴趣,因为他的故事都是关于农村的。
新京报:那要拍电视剧版时,导演毛卫宁说哥哥弟弟随你挑?
王雷:对。让我挑肯定得演男一号啊,导演就跟我聊,觉得我更适合演少安。然后我又赶紧
我说那我演少平吧,少平多讨巧啊,然后毛导说讨巧还找你干吗,你得接受挑战。
新京报:然后导演怎么说服你演哥哥孙少安的?
王雷:少安有传统农民身上背负的隐忍,包括农民的改革、农民的立志,在今天看来这个角色更有现实意义。再就是毛导说你要是演少平,只能他去演少安了(笑)。
现学陕北话融入角色
新京报:听说你一开始进组是说普通话?
王雷:对,演了两三天普通话,后面开窍了,决定说陕北方言。当我用普通话演的时候,实在找不到感觉,然后我就开始学陕北话,当我用陕北话演的时候,一下子这个人就立起来了。你看剧中晓
新京报:怎么开窍?
王雷:可能我是北京人艺的演员,作为话剧演员在语言上我有一定的优势,所以我学起来会快一些。就像宋丹丹,她是北京人,但她可以用东北话演小品,演得比东北人还东北。像徐帆和陈小艺她们是四川人,但是现在很多方言都会说。
新京报:听说尤勇表扬过你的口音?
王雷:有一次,我穿着戏里的衣服和当地农民聊天,那些农民把我当成了当地人,还问我“后生,他们剧组这帮怂人到底要在我们这里拍多久?”,哈哈哈。
【谈感情】 当起妻子的免费老师
娱乐圈明星夫妻不少,但像王雷和李小萌这样,两人都是演员,且还经常一块演戏的少之又少。说到两人之所以能走到一起,王雷认为这主要取决于两人在表演上的审美观一致。面对未来,两人也都认可男主外女主内的模式,李小萌就坚定地表示:“为了家庭,我肯定会放弃一些东西。”
支持李小萌去上学
新京报:你们俩一起演戏,是你演戏的强制要求吗?
王雷:真不是,我们之前和毛导合作过,这次是毛导主动提出来的。
新京报:李小萌怎么不演田润叶(剧中与王雷有感情戏)呢?
李小萌:是我坚持选择田晓
新京报:所以对手戏并不多?
李小萌:也就三场正面接触的戏。
新京报:似乎你最近几部戏都是和王雷在一个组?
李小萌:对啊,因为我上大学偏晚,这几年拍的戏很少,新戏就和王雷在一起。
新京报:你是2013年毕业的吧?但其实你很早就出道了。
李小萌:我虽然很早就接触影视圈,但一直都是在演自己,比如一个任性的女儿,或者是叛逆的小孩,都是在重复自己。上学是我一直的决心。在23岁的时候,我想去读书、要出国,王雷就说你别出国,你在中国考大学。于是我就去考中戏,他就像我的老师一样,每天给我辅导,也顺利考进去了。
新京报:这么晚毕业,觉得耽误了事业发展吗?
李小萌:我一点都不后悔,虽然那时候我放弃了很多片约,也不去挣钱,也无法继续出名了,但我扎扎实实地学了我想学的东西,面对镜头,面对舞台我更自信了,我可以说自己是一个专业演员了,这是我觉得上学对于一个演员的意义。
新京报:你没上学之前觉得自己不是专业演员?
李小萌:我一直都说我是业余演员,但这几年,通过戏剧学院的锻炼,我可以自豪地说我是个专业演员了。
新京报:但入学时你已经小有名气,会不会和同学相处起来不一样?
李小萌:一点都没有。
王雷:大家都是同学,我还经常给他们排练。她同学都管我叫姐夫,我一去就管我叫姐夫。连戏剧学院的老师都说,王雷好几年没见着你了,小萌一来就老看着你呀。
演起戏一直在PK
新京报:你觉得你老公演技怎么样?
李小萌:王雷跟少安之间的差距太大了,以至于我看到他牵着一头牛出来时,我就哭了。
新京报:哭什么?
李小萌:因为王雷塑造了一个人物,不再是他自己了,举手投足,从脑袋到脚,我觉得都是一个实实在在、踏踏实实的农民,他弓着背,在那个飘雪的夜里面走,那种孤独感我一下子就能感受得到,这可能就是一个演员对一个演员的感受。
王雷:她说传神了(笑)。其实我觉得现在真的需要演这样的作品,给观众奉献一些经典的人物形象。咱们不能光说六七十年代的陈道明、陈宝国、李保田……
新京报:你们两个在演戏价值观上挺相似的?
李小萌:对。
王雷:对,我们俩比较一致。
李小萌:我学生气比较重。(好像你剧中也不怎么化妆)基本妆很淡很淡,因为我觉得在那样一个戏里面,如果还涂睫毛膏,画眼线,太可怕了,女人这个时是要放弃美丽的。我也和灯光师说过,不要打得太亮太美。
新京报:那你们自己会PK演技吗?
王雷:一直在比。
李小萌:我口服心服啊。我觉得这个东西不需要比,自己跟自己比就好了,我进步很慢,但是只要我不退步就行。
王雷:哦?你能这么说就已经进步得很快了。
新京报:你挺像点评老师。
王雷:哈哈哈,我觉得男强女弱也挺好的。不过在拍《十送红军》的时候,我已经甘拜下风了,那个戏我下了不少工夫在她身上,确实得到了回报。戏出来以后很多老演员一见到我就说,“哎哟,我是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