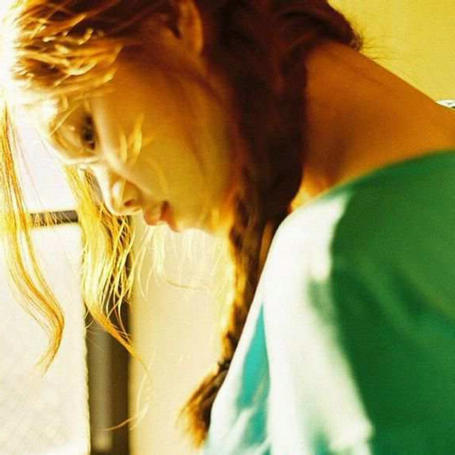描述杜娟花的现代诗
一种美学的高度 我从酷热的南方,来至遥远的北国边境。
逶迤的江河,伸出修长粗壮的胳膊;北国的原野,敞开无比宽广的胸膛;那些高飞的鸟,是好客的主人,融入云里的样子楚楚动人。
季节瞬间更替。
燃烧的夏天消失得无影无踪。
明亮的七月,静谧而严肃。
铁质和石质的高速路,因为蜿蜒起伏而柔若无骨。
原野上的路是对生命的沉思,它的形成,也就是生命的形成,是让人欣喜和热爱的生命完美的迹象。
那些在时间中消逝的人们为我们踏出了生命之路。
我们将记住他们的步履,让他们永远存留在我们心上,以免让心灵之路荒芜。
我是如此地喜爱北国的原野。
它有着天生的阳刚的禀赋。
广袤和辽阔,本身就是一种美学的高度。
逃逸出被雾霾淹没的城市,这里的空气干净得近乎奢侈。
波澜壮阔的绿色,一直向比天边还要遥远的远处汹涌。
曾经血泪斑斑的战场,被深深地埋葬。
坚硬而爽利的风,无边地鼓动生长的欲望。
与春天不断地交合后的原野,仿佛从来就没有过忧郁的冬天:荒芜的坡地,颓废的花影,风霜如利剑切割,大树们悲伤的手指上缠满了凛冽的冰雪。
沧桑,是一段需要唤醒的记忆。
美人松的集群,笔直地站在坡地的背脊,高扬着男性的头颅。
白桦林自信而散漫,闪着诱惑的光。
蓝皮和红皮的屋顶,在树丛中跳动。
裸露的村头,棕色的马匹安详一如既往,偶尔扬起发亮的黑色长尾。
蓝天和绿野之间,云悬浮飘动。
阳光一会儿在它前面,照出凹凸的曲线;一会儿在它后面,勾出金色的边缘。
而它,兀自经营着明暗和色彩,酝酿暴雨。
雨一旦降落,便是直立的柱体,顶天立地,气势磅礴地在原野上移动。
它刚刚离开的地方,立刻就被阳光充满。
野花落英缤纷,希望托付给种子,返回原野,接受季节的所有邀请,在春天来临之前,弥漫成又一度响彻云霄的灿烂。
一坡坡怀孕的玉米,凝聚在耀眼的阳光下面,傍晚的雷声隆隆滚过,在即将来临的诱惑之夜,陷入夏天的感情陷阱。
流水一样的狗尾草,摇落细致的露珠。
摒弃了多余的杂质,成为大地上一种蓬勃的力量。
将会有镀金的巨型收割机,把秋天装上。
夕阳让老人们眯缝眼睛,细数着一颗豆荚、一棒玉米、一穗高粱走过的漫长路程,以及自己一生的收获。
很多年前,他们曾经肩着绑绳,匍匐在原野的路上。
世界此时格外安详。
大野肃穆,彩虹丈量着原野的两极。
一只大手,抚摸着我们,如唤醒孩提懵懂的话语。
我想我应该放弃词不达意的表达,蜷缩在那只手掌的温情里,一边看风景,一边咀嚼岁月的苦涩与芳香。
风一阵一阵地拉扯我的衣衫,我漫无目的地站在原野上,听任绿色进入我的身体,以及庄稼的芬芳渗入我的思考。
空间与时间无限扩大与延长。
四十六亿年的演化,地球馈赠给人类无数的珍宝。
第四纪。
新生代最新的一个纪。
其下限年代距今二百六十万年。
那时,灵长目完成了从猿到人的进化,生物界进化到现代面貌。
一声巨响,无数巨岩伴着灰黑色的浓烟,翻卷着冲天而起;各个火山口,时而轮流喷发,时而静止,时而同时发作,绚烂无比的礼花在空中怒放。
大地在颤抖,整个天穹被照得通亮,岩浆肆意奔流,为一个不可克制的欲望鼓舞,在烈焰迸溅的一瞬间,领会到生命的开端和终结的全部欢乐和痛苦。
北起大兴安岭北部的鄂伦春诺敏河火山群,经阿尔山——柴河、锡林浩特——阿巴嘎火山群,南抵察右后旗乌兰哈达火山群,断续延伸一千公里,三百九十多座形态各异的火山,构成了内蒙东部壮观的第四纪火山喷发带。
一座座拔地而起的火山锥,千姿百态。
喷发年代由史前的两百多万年到近代的两百八十多年前,是世界顶级资源。
这里拥有保存着世界上最完整、分布最集中、品类最齐全、状貌最典型的新老期火山地质地貌。
最新期火山岩浆填塞了浩瀚的远古凹陷盆地,一个个湖泊串起欧亚大陆桥上璀璨的明珠。
人类无法洞穿地壳,但地壳自身千疮百孔。
火山遍布全球,有的孕育和爆发的条件伴随着整个造山运动;有的孕育和爆发的过程伴随着整个山体的坍塌;有的形成上下翻滚的火湖,熔岩从火湖的边沿流出,形成恐怖的熔岩瀑布、熔岩河流、熔岩喷泉。
炽烈的岩浆汹涌,烧毁了森林,淹没了耕地,埋葬了整座城市。
火山是一种残酷无情的美丽:向上飞扬是一种毁灭,向下伸延也是一种毁灭。
如同早逝的耶夫诺夫的诗:我不是活着,是在燃烧。
但北国原野上的火山,却写出了另样的诗篇,寻找到又一度烂漫的生命。
谁能想象沉寂了千万年的火山,会有如此的芳草萋萋,林木葳蕤。
葱绿充盈的树叶和草叶,在黑色的熔铸金属上铺展。
积雪融化、树木泛青之前,初春的达子香早已含苞欲放。
原始石塘上粉色的云团,浩浩渺渺,香气远远地飘浮。
关于烈火迸溅的记忆,早已在梦中消失;火山为自己狂热经历的辩解,早已坠落在深深的草莽。
万物皆神圣 踏着枯枝、落叶、青苔,走进谷地深深的树林。
这里是满族、鄂伦春族、达斡尔族、鄂温克族的故乡。
一个多情的季节,早已开始。
顺着被年深月久的腐烂落叶弄得软绵绵的路走着。
鱼鳞松、油松、杉松、柞树,色树、洋槐、刺槐、青桐、榛材棵子,满山遍坡都是。
所有的树都被灌木丛紧紧地包围。
在茂密的灌木棵子里,熙熙攘攘地挤满了霸王鞭、野丁香、狗尾花、山芍药、野玫瑰、扫帚梅。
穿过茂密的、散发着浓郁的树脂和草莓香味的树林,衣服被弄得湿漉漉的,带给人一种清凉的、甜丝丝的快感。
一个个被野火烧过的土墩子上,长满了草莓子。
这儿的浆果和草莓子,都熟透了,发黑了,甜得要命。
风在沙沙地响,杜鹃、沙斑鸡和不甘寂寞的蝉在合唱。
在这样的树林里走路,就像在彩色的、水声悦耳的溪水里游来游去的鱼。
这是沉思默想的最好时刻。
你会不由自主地回想起遥远的已经忘却的童年,脑子里充满了种种孩提的甜蜜和喜悦。
头顶树桠上,这儿那儿站着野百灵、沙斑鸡、鹪鹩和山鸡。
它们大大方方、满不在乎地站着。
即使被你惊动,也不过稍稍地、懒洋洋地一跳。
有时候,铁雀和斑鸠会落到离你很近的地方,然后又扑扑地飞起,它们拨起的风,直朝你脸上吹过来。
长尾巴的松鼠在明明灭灭的树枝上无忧无虑地跳来跳去,毫不在意树林里出现的不速之客。
如果是夜晚,从林子里跑出的狍子会傻傻地站在路中间,对迎面而来的灯光视而不见。
黄昏,潮湿的凉意从四面八方袭来。
鸟悄悄地离开被太阳晒得温暖的树梢,振起翅膀,依恋地、默默地飞进树林深处。
雾在林中飘荡。
雾是半透明的,并不妨碍仰望树缝中的天空。
被树枝分割的天空特别明亮。
心轻轻颤栗。
北方无垠的原野,是美与善的象征。
一切浮躁都被洗净,仿佛远离尘世,心灵恢复了本来面目,所有的恶念在与原野接触时消失。
弥漫在原野上的沉寂与神秘,滋润着诗心,成为艺术深沉、宁静的心理背景。
森林中站着部族的图腾:太阳,月亮,男人,女人,飞禽,走兽,十二个杜瓦兰神,栖息在十二种植物上的十二种动物……萨满的根基是万物有灵,可见的世界到处是不可见的力量,所有的生命和非生命、有机物和无机物都有着灵魂。
没有创始者,没有寺庙,没有成文的经典,也没有规范的礼仪,萨满是超越时空的文化,用不着既定的分类逻辑。
人们崇奉的是氏族或部落的祖灵和图腾,乃至一切动植物以及无生命的自然物和自然现象。
世界最早的宗教,几乎与现代人类出现的历史一样长久,文明诞生之前,人们用石器打猎时就已经存在。
各种外来宗教传入之前,萨满独占了北方的古老祭坛。
拜火。
拜山。
拜日月星辰、风雨雷电。
祖神的偶像挂于树梢,两侧是日、月和大雁、布谷。
树间皮绳上悬挂着兽头和兽尾、脏器和四肢,兽头朝向祖神。
凭借祖神的力量,同鬼神交战。
猛烈地击打神鼓,疯狂地摆动腰铃。
“乌麦”(为婴儿抓回灵魂的仪式),送魂,祈求猎物,求雨和止雨,咒术与法术,占卜与跳神。
神鼓和腰铃是萨满语言的载体。
宏大而嘈杂的鼓铃之声是萨满音乐的全部。
变幻莫测、简朴粗犷的野性音响,充满慑人魂魄的威力。
萨满音乐不是生活之外的“艺术”,它就是生活本身,是与神沟通的语言。
萨满是“知者”,循着萨满旅程从另一个实在获得力量和知识,然后回到原本的世界,以其所得的力量和知识帮助自己或他人。
由人到神,又由神还原为人。
自然是灵性和拯救的源泉,赋予人们改变境遇的能力。
萨满相信万物皆活,万物相系,万物皆神圣。
狩猎部族搬进了新居,古老的灵性修行并不曾消失。
延续着大地灵性和个体意识转换与成长的主题,神秘的萨满依旧萦回在现代生活。
萨满只为与自然为友,并不追求彼岸世界。
萨满的生命观基于人类自我实现的欲望。
那便是寻觅自己的梦境,发现自己内在的神话。
萨满的力量不是权力,而是能量,是人类与自然的整体生命力。
在人类中心主义狂热肆虐造成的人类与自然的疏离乃至生态危机中,萨满强调自然与个体的能力,让所有的人都体验到与万物一体和万物之神圣,回归大地之母的怀抱,回归生命本身。
萨满经验实现了深层原初的出神需要,这种出神是人类存在的意义
守望心灵的高地 时间在不知不觉中推移,岁月像水一样流逝,而山川依旧。
北国原野是怎样的一个所在
仅仅是清新、古老与富饶吗
抑或只是遥远
原野上有两种声音: 一个欢快,吟唱着尘世的演变,对生命充满感激。
人类的生息和繁衍,朝代的兴衰和更迭,全球化与城市化:雾凇和冰雕,古禅寺和旅游岛,滑雪场和度假村,火山温泉和森林浴,啤酒节和音乐会,俄罗斯风情舞和庄稼院二人转,人参、鹿茸和杀猪菜,红肠、列巴和苏波汤…… 一个严肃,沉思着神性的里程,对生命有更深沉的敬畏。
北国原野,远离繁华激荡的中心,在世纪的神经末梢舞蹈。
略带伤感的节拍流露出舒缓和飘逸。
原野上的心灵只渴望飞翔。
诗人们以草原、寂寞、候鸟、江水和波涛命名。
饮下整夜的黑,一条河流的疼痛和曲折,像母亲一样的味道纠结成盐,抵达诗人们的内心并且变得深刻。
上升或下沉,周而复始。
从屈原开始的艺术高贵,至少在这里没有失落。
岸边簇生的芦苇,细长的苇叶剪碎了天空的深蓝,新月是刚出鞘的银刀。
江河是诗人们的黑美人,在诗歌的怀中静静酣睡。
爱和坚守都与山河有关。
精神探求者们足踏在哲人向往的自由而新鲜的土地,在北国原野守望着心灵的高地: 他们或者静静地收拾了自己的行囊,避开了城市的喧嚣,蹲在祖居场院的石碾上,重新呼吸左邻右舍弥漫到屋院的柴烟,看着远处庞然连绵的楼群和熙熙攘攘的人流,那里各种欲望膨胀成一股强大的浊流,冲击所有大门窗户和每一个心扉。
而他们整颗心没入父辈爷辈老老老爷辈生活过的这方原野的沉重的历史烟云,负了写出民族秘史的沉重使命,穿越一条幽深漫长得似乎看不到尽头的时空隧道。
纷繁的世界和纷繁的文坛似乎远不可及,得意与失意,激昂与颓废,新旗与旧帜,红脸与白脸,似乎都是另一个世界的属于昨天的故事而沉寂为化石了。
除了思想,他们完全地封闭了自己,领着笔下的人物穿行过世纪的风霜雨雪,让他们带着各自的生的欢乐和死的悲凉进入最后的归宿。
他们或者反感现代文明表面光鲜之下的种种卑琐,在一个争名逐利、以权贵自炫的时态中,坚持绝对的平民立场,着力状写北方硬汉的生存困境、荣辱沉浮,以及深深扎根于内心的孤独史和痛苦史。
这些硬汉们往往不仅不是世俗的成功者,甚至差不多是失败者。
然而他们正直,有力气,有色彩,有故事;敢打敢拼,说话声音高,骂人花样多,干什么事都不拐弯抹角,在社会转型的风吹雨打和涛翻浪涌中与命运抗争,希望,追寻,失落,抗拒,欢笑,悲号,扭曲与升华。
这个世界是如此杂乱、浑浊、穷困、粗野,又是如此强悍、生气勃勃,是张扬生命力的舞台。
他们有血有肉地活着,自主自立地站着。
健全的生命和人格令他们天然地摆脱了颓废与堕落,绝不堕入人性变质的深渊,独立地在自己的本质内成就自己,与时尚保持距离,拒绝卷入狂飙突进的时代游戏。
作为永不屈服于生存困境的草根意志的体现者,他们矗立在富丽堂皇、光怪陆离、物欲横流、信义沦丧的滚滚红尘中。
他们或者以特有的沉静和从容,义无反顾地追随着河流行走。
岸边的村庄,迤逦于自然的河流形态,曾经的风情气韵激荡,拖拽着明明灭灭的故事。
水流声里一条条生命游动。
性急的孩子不等伏天早已光溜溜跳进了河水。
岸上的女子,手臂如凝脂,脖颈如玉兰。
老人坐在廊棚下听雨,猫啊狗啊的。
一巷子蛙鸣浮起来落下去,不知名小鸟的啁啾遥远了一切,透明了一切……他们就这样走过无数的村庄,有过无数的无奈和迷惘:欲望把日子翻得断了线,人在诱惑、在生存原则的逼迫中现代化。
一座村庄的经脉曲折起伏,难道只能是靠记忆了吗
他们于是写村庄,写那里的人们和土地的是非,写他们与土地目不斜视的狂欢,写他们在物事面前丝毫不敢清浊不分的秉性,写他们铺陈在万物之上的张扬;写他们对信仰的执着守诚;写一杆长鞭在月亮即将退去的黎明前甩得激扬,写一个女人想那长眉浓烈似墨,张开的大嘴吼出威震山川的期待,不屑去爱一个白面书生。
爱到老,依然扯着皱褶重叠的脖颈仰望那一声撕裂的鞭声。
质朴而博大的文学于是在北方原野的泥土、水和空气里,在众生云集真情裸露的地方成长起来。
一个以“产业化”为文化政策导向的时代;一个指望莺歌燕舞、插科打诨安抚社会神经的时代;一个用“富豪榜”评判作家优劣的时代;一个无需学问只需嘴皮子,甚至代笔、抄袭即可风靡天下的时代;一个连阅读也功利化的时代;一个连语文教学都边缘化的时代,丝毫没有影响他们执拗的守望。
北国原野上的文学是刚性的文学,像北国原野一样大气,总是带给我们一次又一次震撼。
离别北国原野的那个早晨,我在江边徘徊。
迷蒙的亮光缓缓地从地平线升起,渐渐点燃了丝丝缕缕的柔软的云,投向淡紫色的江面。
笼罩在紫丁香般晨曦中的江水,带着无言的欢欣,奔流在静谧中。
大江用千里长线,携带着广袤北国的豪放和夏天的纯净,追逐地平线。
地平线不断呈露出一处处闪耀在灰蓝色远方的诱人的、神秘的天地。
随意而潇洒,风无声地掠过大地,像琴弦低声细语的倾诉。
江水应着风的节拍,为无形的精灵所牵制着驾驭着呼唤着。
风,是江河自由的侣伴。
这样的静谧让我觉得什么地方有一个人像我一样,在聚精会神地倾听我所听不见的一些声音。
他凝神屏息,睁大眼睛。
有一种东西在激动他,让他马上就要打开自己的胸怀,对着一种巨大的、无边无际的、我所看不见的东西。
他倾听着七月的黎明的音响,吮吸正在消失的夏夜的气息。
沉默使他感到沉重。
在这样的早晨不应该沉默,在这样的早晨要唱歌
这冲动不仅仅是来自歌喉,而且是来自一种心的深处发出的东西,一种最能唤起别人同样的激情,最能使人吐露最隐秘的心曲的东西。
那个人不是别人,就是我自己。
我喜欢在这样的早晨眺望原野。
独自一人,面对着一片无声的闪亮的流水,一片无声的闪亮的绿色,听着一个想象中动听的声音讲述一个温柔的故事。
在水凝滞在宁静的沉思中的地方,一切都像天空一样灿然。
朝霞燃烧起来,远处最高的山峰最先射出金色的光芒,一只不知名的鸟像个圆点悬在空中,仿佛一颗心脏似的颤动不已。
一阵细雨般的、馥郁而温馨的花粉,不知从什么地方袭来,悄悄飘扬。
凭这股香味可以闻到有无数的花儿在忽然之间盛开。
一切都极其真实,就像朋友陪伴在我身边。
我想象着我已经蜕变,像蝴蝶脱掉丑陋的衣衫,轻盈穿过原野,为漫长的河流吹起绸缎的涟漪,为所有热恋的人弹起竖琴。
不必费心地杜撰任何神话。
再没有什么能比一会儿以温情,一会儿以力量,一会儿以安静,一会儿以快乐来触动人的心弦的北方原野更庄严神圣的了。
(陈世旭 新时期代表作家,中国作协主席团成员)
南方能养鹿吗?
鹿鹿体型大小不一般雄性有一对角,雌性没有大多生活在中,以树芽叶为食。
鹿角为随年龄的增长而长大。
鹿分布在美洲及亚欧大陆的大部分地区。
【汉字释义】ㄌㄨˋ汉语拼音:lu汉字笔划:11书写笔顺:拉横撇折竖竖横横折撇折偏旁部首:鹿部首笔划:11五笔输入:ynj(86版) ox(98版)汉字解释:〈名〉(1) (象形。
甲骨文字形,象鹿的头角四足之形。
本义:鹿科动物的总称。
种类很多,通常雄鹿有角)(2) 同本义 [deer] 鹿,山兽也。
――《说文》即鹿无虞。
――《易·屯》呦呦鹿鸣。
――《诗·小雅·鹿鸣》鹿中容八算。
――《仪礼·乡射礼记》(3) 又如:鹿中(刻成鹿形的木器);鹿伏鹤行(形容小心警惕的样子)(4) 比喻政权,爵位 [political power] 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
――《史记·淮阴侯列传》(5) 又如:鹿台(古台名。
故址在今河南汤阴朝歌镇南,相传为殷纣王所造。
武王伐纣,纣兵败,登台自焚而死)(6) 方形粮仓 [granary;barn] 市无赤米,而囷鹿空虚。
――《国语·吴语》(7) 通“麓”。
山脚 [foot of a hill or mountain]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谷梁传·僖公十四年》(8) 通“簏”。
竹箱 [bamboo vessel] 而囷鹿空虚。
――《国语·吴语》(9) 姓鹿 lù〈形〉粗,陋 [coarse]。
如:鹿布(粗布);鹿车(用人力推拉的窄小车子)〈通“禄”〉鹿、禄 ----《汉书·蒯通传》:“且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
”张晏注:“鹿喻帝位。
”即鹿作“禄”解。
(摘自黄现璠著《古书解读入门》(油印本),广西师范学院教材部,1962年2月;黄现璠著《古书解读初探——黄现璠学术论文选》第475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词组:鹿角 lùjiǎo [antler;deer horn] 雄鹿的角。
亦指为阻止敌军前进而设置的树枝、荆棘之类的障碍物鹿卢剑 lùlújiàn [handle of sword wound with silk thread] 剑把用丝绦缠绕起来,像鹿卢的样子。
鹿卢,即辘轳,井上汲水的用具鹿茸 lùróng [pilose antler of a young stag] 雄鹿的幼角鹿死谁手 lùsǐshuíshǒu [at whose hand will the deer die――who will win the prize]鹿:谓猎取的对象。
喻指政权。
比喻最后胜利属于谁脱遇光武,当并驱于中原,未知鹿死谁手。
――《晋书·石勒载记下》鹿砦 lùzhài [abatis] 用树木设置的形似鹿角的障碍物。
分为树枝类与树干类两种。
前者主要用于防步兵。
后者主要用于防坦克。
设置时可用有刺铁丝、手榴弹和地雷予以加强【鹿科动物】【拉丁文】学名:Cervus axis【英文名】:Erxleben【分类】: 哺乳纲、偶蹄目、鹿科【体长】: 0.75~2.90米【肩高】:0.3~2.20米【体重】:9~800公斤【形态】:鹿是偶蹄目的1科,共16属约52种,大多数种类普遍具有的特点是:四肢细长、尾巴较短,雄性体性,大于雌性。
通常雄的有角,有的种类雌雄都有角或都无角。
【毛色】:大多数种类毛色深暗,从黑色、棕色、黄色、深红色至淡黄色不等。
但驯鹿会出现白色的个体。
【寿命】:8~45年不等【保护级别】:梅花鹿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地理种群差异】:鹿的种类繁多,形态各异,共16属约52种,从最大的驼鹿到最小的鼷鹿之间品种丰富。
【分布情况】:鹿的种类繁多,共16属约52种,全世界除南极洲外均有分布。
【物种状况】:大部分种类地方常见,少数种类为濒危物种。
其中梅花鹿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生活习性】:除驼鹿外大多数种类群居生活。
【生活环境】: 山地、草原、森林均有分布。
【食物种类】:树叶、草、果实、种子、地衣、苔藓、灌木、花朵、水草、树皮、嫩枝、树苗。
【生理特征】:一般春季3~4月发情交配,怀孕期4~10个月,每胎1~3崽。
2~3岁性成熟。
【经济价值】:所有种类的肉可吃,皮可制革。
其中梅花鹿的鹿茸是名贵的药材。
国内已大量进行人工饲养,并进行活鹿取茸(对鹿不会造成伤害)。
角是鹿科动物中雄鹿的第二性征(个别属无角,如獐属),同时也是雄鹿之间争夺配偶的武器。
角的生长与脱落受脑下垂体和睾丸激素的影响。
北方的鹿过了繁殖季节,角便自下面毛口处脱落,第2年又从额骨上面的1对梗节上面的毛口处生出。
刚长出来的角叫茸(我们通常叫鹿茸),外面包着皮肤,有毛,有血管大量供血,分杈。
随着角的长大,供血即逐渐减少,外皮遂干枯脱落。
1~2岁时生出的初角几乎是直的,以后角的分杈逐年增多,到成年后定型。
梅花鹿是鹿科鹿属的1种。
因为身上有一些明显的白斑在背脊两旁和体侧下缘排列成行而得名。
也叫花鹿。
梅花鹿分7个亚种,中国有5个亚种。
鼻端裸出而呈裂缝状;雄鹿有角,每年约4月脱盘长茸,其角一般到4杈为止,眉杈斜向下伸,第2杈与眉杈相距甚远;冬天毛的颜色为栗棕色,白色斑点不显,尾下部为白色,腹毛淡棕;夏天毛红棕色,有的为暗灰褐色,背部中线地方为黑色,有的至尾部黑色线变细,尾上部黑色,下部白色。
分布于西伯利亚东南方,日本,中国的东北、华北、东南和台湾。
现今野生梅花鹿数量非常稀少;中国列为一类保护动物。
栖于混交林,山地草原和森林边缘,一般不进入密林。
冬季多在阳坡低凹背风处,春秋则在空旷少树地区活动。
夏季喜荫凉,多在阴坡开阔透风的地方,有时为了避免蚊蝇叮咬也到高山草原活动。
性机警,晨昏时结群。
主要以青草、嫩芽、树叶、沙参等为食。
每年8~11月交配,怀孕期7~8个月,4~6月为产仔盛期,每胎1~2仔。
【我国现存的鹿】:麝(Moschus moschiferus),体型较小,体重约10公斤。
雌雄性皆无角。
雄性上犬齿獠牙状,突出口外。
后肢比前肢长。
具胆囊。
雄麝有麝香腺,分泌具有浓郁香气的麝香,是极名贵的药材和高级香料。
我国麝香的产量与质量均居世界之首位。
在分类上有人主张麝应单独立科。
麂(Muntiacus muntjak),是华南地区常见中型鹿类。
麂皮细韧,是服装制革和精密仪器用革的良好材料,为我国传统出口商品。
梅花鹿(Cervus nippon),夏毛红棕色,有显著的白色斑点,冬毛棕褐色,白色斑点不显。
臀部具明显的白斑。
雄性角有四叉。
眶下腺发达。
在我国历史上曾有过广泛分布,但目前仅存于安徽少数地区和四川最北部。
我国很多地区都建立了养鹿场,进行人工繁殖,作为割取鹿茸的主要来源。
鹿胎、鹿血、鹿鞭和鹿内脏等均是贵重的药材。
马鹿(Cervus elaphus),是大型鹿类,体重可达200余公斤,鹿茸也是名贵药材,品质仅次于梅花鹿,但产量较高。
鹿曾经广泛分布于每个大陆,澳大利亚有6种在19世纪引进的鹿,它们是:黇鹿、马鹿、水鹿、豚鹿、蒂汶黑鹿和花鹿。
但由于环境的限制,只分布在有限的范围。
通常只有公鹿长角,驯鹿是唯一一种公鹿和母鹿都长角的鹿,但母鹿的角要小得多。
在每年冬天,公鹿的角都会脱落,到春天开始长出新的角,那时鹿角会覆盖者一层皮,叫做鹿茸。
当鹿角成型时,鹿茸就会脱落。
母驯鹿的角是在春天脱落的。
另外,麝和獐无论公的还是母的,都没有角,它们用长长的獠牙去自卫。
公麂既有獠牙也有角,而母麂既没有獠牙也没有角。
雪是鹿最大的敌人之一。
如果雪并不是很大,那到没什么的。
但当雪变得非常厚时,它们就很难找到食物,因为雪都把食物盖住了。
另外,虽然鹿跑得很快,但由于有些鹿的体重可达300公斤,当它们跑时,它们就会陷到雪中,减慢它们的速度。
仅50公斤的狼便很容易地追上了它们。
不像大多数动物,鹿没有固定的家。
对鹿来说,所谓的家就是地盘。
夜晚它们就睡在灌木丛中。
在冬天时,当鹿的地盘覆盖着厚雪时,它们就会再找一个雪相对较浅的地盘。
当很多鹿都选这个地盘时,它们就会分地盘。
总的来说,鹿科动物是哺乳类动物中最富有价值的种类。
它的价值是多方面的。
自古以来,由帝王、贵族到一般老百姓,不论中外,都把“狩鹿”作为一种兼具体育性、社交性、娱乐性以及实用性的重要活动。
在古代的记事中,“狩鹿”总是占有重要地位。
连孔子所订六艺之一的“射”,也和“射鹿”有关。
中国古代射猎的,主要是麋鹿,即四不象,到清代康熙、乾隆时是马鹿和驼鹿。
对一般人说来,猎鹿主要是着眼于经济价值。
鹿全身都是宝,鹿茸、鹿胎、鹿鞭、鹿尾、鹿筋、鹿肉、鹿脯等等,无一不是药材或补品,另外有几种鹿的毛皮,可制为高级衣物或皮革。
驯鹿更具有广泛的用途,例如拉雪橇、驮东西、挤奶,等等。
近年来驼鹿和梅花鹿还有家畜化的倾向。
正是由干鹿的经济价值这样高,所以人们猎得出多。
麋鹿作为一种野生动物,几乎在一两千年前就已打绝了。
梅花鹿由于鹿茸质量最优,所以在几十年前已将山西、河北两个亚种的野生种打绝,另外华南、东北、台湾三个亚种也所剩无几。
其他鹿种也有类似情况。
现在国家固然已将绝大部分鹿种列入保护动物名单,但在野外尚未受到严格的保护。
有些稀有种,例如海南岛的坡鹿、华南的梅花鹿、西双版纳的豚鹿等,仍然处在濒危的边缘,值得严重注意。
中国是世界上产鹿种类最多的国家。
属于鹿科的动物,全世界共有17属,38种,其中有10属、18种在中国曾经产或现在仍产。
这就是说,中国产的鹿,占世界鹿属的一半以上,占世界鹿种的将近一半。
相形之下,前苏联的国土比中国大1倍多,但只有5属、6种;美国和加拿大面积和中国大小相近,各只有4属、5种;印度的面积固然没有中国大,但印度素以鸟兽种类“最丰富”著称,却只有鹿属4个、鹿种8个,仍远不及我国。
更应指出,这四个国家,谁都没有一个特有属或特有种的鹿科动物,可是在中国产的鹿科动物中,至少有一个麋鹿属是特有属,有麋鹿、白唇鹿、毛额黄麂、小黄麂或再加上林麝等四五个种是特有种。
另外还有黑麂(毛冠鹿)和河麂(獐子)2属2种,除缅甸和朝鲜各产少数外,中国分布既广,数量又多,所以基本上上可视为我国的特产动物。
四不象就是麋鹿。
麋鹿是古书上的名称,四不象则是民间的俗名。
《封神演义》里讲到过四不象,说这是武王伐纣大军主帅姜子牙的乘骑。
小说把四不象描述成“麟头豸(Zhi)尾体如龙”,这当然与真实形象相去十万八千里。
但这书中所说并不是纯粹出自想象。
从化石资料可以知道,武王伐纣的时代,正是麋鹿最为繁盛的时代,长江南北出土的麋鹿化石,以商末周初为最丰富,之后逐渐稀少,周朝以后更急剧减少,到秦汉时代已变得极少了。
有人认为,麋鹿作为一种野生动物,可能在汉朝时就已经灭亡了。
但也有人考证说,直到明朝,甚至清初,在长江以北的苏北地区,还有残余的麋鹿生存,只是数目已微不足道了。
在动物学史上,关于麋鹿的现代叙述是从1865年开始的。
一个住在北京城里的法国神甫通过种种渠道,结识了皇家猎苑北京南海子的守卫人员,干了一桩盗买盗卖麋鹿标本的勾当,在1866年1月弄走了两张鹿皮和两个鹿头。
鹿头和鹿皮被送到巴黎,很快便引起欧洲各国动物学界和自然爱好者的巨大兴趣。
各国动物园纷纷找路子,都想得到它。
由1866年到1876年的10年间,英、法、德、比等国驻清使节和教会人士,通过明索暗购种种手段,陆续从南海子猎苑搞到几十只麋鹿,运回国展览。
从此中国的“四不象”遂名扬四海。
我国特产动物中,最闻名于世的,人们都说是大熊猫,殊不知麋鹿扬名海外,还远在大熊猫之前。
从上个世纪70年代到本世纪初,这二三十年间,麋鹿的遭遇是悲惨的。
作为当时世界上唯一种群的北京南苑的南海子种群,连遭打击与浩劫。
1894年永定河决口,洪水冲破了猎苑的围墙,逃出来的麋鹿和其他动物,被灾民吃去不少。
接着在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猎苑里的兽群全部被杀光。
据说还剩下一对,养在一处王府里,以后转送“万牲园”,也死掉了。
至此,中国特产动物四不象,在国内完全灭绝。
这时欧洲各家动物园里还剩下18只麋鹿。
英国有一位贝福特公爵,素爱豢养动物,他花大价钱,把这18只全部买回,养在他的庄园里。
麋鹿在里面繁殖顺利。
结果,本来是中国的特产动物,中国却一只也没有了,中国人想要看它一眼,却不得不到国外去看。
可见即使是一种动物,它的命运也是同祖国的兴衰荣辱息息相关的。
在英国的那群麋鹿,历经两次世界大战,幸运地保存下来,而且逐渐增多,到1948年已增至255头。
1956年春,伦敦动物学会派人将两对年轻的麋鹿送到北京。
于是,时隔50余年,中国人民重新见到久闻其名但无缘相见的“四不象”。
由于饲养环境不适合它们的特殊要求,未能顺利繁殖后代。
1973年底,英国朋友又送来两对年轻的麋鹿。
1984年春,国内的麋鹿总数是12头,其中雌雄各6头,有9头在北京动物园,其余3头分别在上海、广州和保定的动物园。
而外国动物园中所饲养的麋鹿总数,据1982年的调查,已超过1100头了。
所有这些麋鹿,全部是百余年前弄出国去的那几十只的后代。
除了麋鹿是货真价实的四不象之外,我国民间还把另外几种动物也叫“四不象”。
这些姑且称之为“假四不象”。
这包括大兴安岭鄂温克人畜养的驯鹿;大兴安岭南部的驼鹿,又名麋;湖南南部产的黑鹿或水鹿;安徽黄山一带产的苏门羚,又名鬣羚。
也许还有其他。
没有学过动物分类学的人,往往把形态较怪的动物都叫四不象,这是误会。
驯鹿: 在这么多“假四不象”当中,以驯鹿最容易引人误会,因为不仅在大兴安岭产地群众叫它四不象,而且许多种古书,例如《清文汇书》、《黑龙江外记》、《异域录》、《曹廷裘日记》等,都将它传得很广很久,使得人们相信这就是真的四不象。
记得1950年春北京动物园重新开园之际,报纸上和动物说明牌上都有“四不象”一名,人们兴冲冲跑去一看,原来就是驯鹿。
驯鹿和麋鹿在外形上的区别较大,即使外行人也不难一眼看清。
麋鹿是尾巴最长的鹿,驯鹿的尾却极短。
麋鹿的角好似没有眉杈,各杈皆向后发展,驯鹿却有非常复杂的向前生长的角杈,而且它是唯一雌雄皆长角的鹿种。
在体形毛色上也有不少差别。
二者唯一相同之处,就是蹄子扁平宽大,间距较宽,悬蹄发达。
这是因为麋鹿原来生活在沼泽和湿地,而驯鹿则长期活动在冰天雪地,二者都需要这种类型的蹄子。
中国没有真正野生的驯鹿。
鄂温克族人所豢养的驯鹿,估计现有1000多头,不知当初是从哪儿得来的。
它们与西伯利亚及北欧各少数民族养的驯鹿,习性上基本相同,都是属于半饲养、半野生的状态。
日间大都任其跑到山野间自由觅食闲逛,晚上跑回村里过夜。
有需要时,就把它套上拖雪橇,驮东西,挤鹿奶,甚至宰杀剥皮、割肉、炼油。
寒带少数民族需要驯鹿,正好比青藏高原上的人需要牦牛一样。
驼鹿 :驼鹿的情况却不同。
它是真正的野生动物。
它的分布区不象驯鹿那样靠北,在我国可以分布到大小兴安岭的北纬四十七八度一带。
《动物学大辞典》给它起了个名字叫“麋”。
这就更容易使之同“麋鹿”相混淆。
在大兴安岭有人口叫它“四不象”,但是在小兴安岭就没有人这样叫了。
看来还是叫它“驼鹿”最为相宜,因为它身体高大如骆驼,四条长腿也有一点像骆驼,肩部特别高耸,略似驼峰。
驼鹿是世界上所有鹿中个体最大,角也最大的鹿。
头很大,脸特别长,脖子非常短,鼻子肥大而下垂,喉下有肉柱,上有许多垂毛,躯体十分雄壮短粗,四条腿却又细长得不成比例。
雄鹿的角与别的各种鹿的角形状都不同,不是枝杈形,而是扁平的铲状,中间宽阔似仙人掌,四周生出大量的尖杈,最多可达三四十个。
每支角的长度可超过一米,最长的竟达1.8米,宽度能达40厘米。
两支角的重量就达三四十公斤。
那支撑着如此巨大的角的身体,不用说也是大得可观了。
在阿拉斯加曾经发现过肩高超过2米,体长将近3米,体重达到650公斤的大驼鹿。
在兴安岭猎获的驼鹿,没有超过500公斤重的,毛色也较淡,角出较小,不十分宽扁。
驼鹿生活在亚寒带多湖沼的森林地区,不爱吃草,喜欢吃嫩枝叶和树皮,春夏秋三季常下水浸泡,摄取水草和莲花、莲茎,冬季则在雪地上觅食各种苔藓。
很少集合成群。
牡鹿平时更喜欢独居,但在冬季缺食时,却有过混人牛群里觅食的情况。
在内蒙古阿尔山的牛群中,就曾有两只驼鹿被人捉住,其中一只雌的被送到北京动物园展览。
驼鹿和驯鹿也有鹿茸,论尺寸和重量都比梅花鹿茸大得多,但据说质量次,药用效能低。
其原因还不清楚。
驼鹿如此巨大,肉量自然很可观,可是味道如何,似乎没有多少人称道。
但据说古代著名美味“八珍”之一的“猩唇”,就是它那肥大下垂的鼻唇。
驼鹿在外国是一种最重要的狩猎兽。
人们猎它,是为了要它的巨角做纪念品。
在我国,鄂伦春等少数民族猎它,是为了吃肉取皮。
现在,它属于国家第二类保护动物。
至于麋鹿和驯鹿,因为都没有野生种,所以都不用列入国家保护动物的行列。
黑鹿: 在湖南南部多水的山林里,还有一种“假四不象”,就是黑鹿。
越过湘粤边境,到了广东北部的山区,人们叫它水鹿。
在四川产地,它的名字是黑鹿。
到了云南,人们又叫它马鹿。
听说海南岛上的人还叫它水牛鹿。
总之,除了湖南人叫它四不象之外,所有各地都承认它是鹿。
这是一种热带、亚热带的鹿种,向南一直分布到马来西亚、苏门答腊,最北的产区是在我国四川西北部和青海南部一带。
台湾岛上上有一个亚种。
黑鹿是一种大型鹿,身体粗壮,比驯鹿更为高大,和麋鹿差不多。
我国产的黑鹿,雄的肩高可达1.25米到1.3米,体重可达200多公斤。
雌鹿较小,重约130到140公斤。
毛色一般黑褐,颈和尾的颜色更深。
毛十分粗杂。
尾巴虽比不上真正的四不象长,但比起其他各种鹿也算是长的。
雄鹿有粗大的角,一般长达七八十厘米,粗达十七八厘米,最长纪录是1.25米。
这种鹿的茸角,虽不如梅花鹿和马鹿的鹿茸价值高,但较优于驼鹿、驯鹿,过去为我国西南各省的主要土特产,每年收购数量相当大。
现在它已被列入第二类保护动物名单。
其他珍稀鹿种 :前面曾提到过,在我国所产的18种鹿中,有四五种是中国的特有种。
其中除了麋鹿举世闻名之外,还有两种也很著名,就是白唇鹿和毛额黄麂。
另外有几种,虽不是中国的特有种,但确属珍贵稀有,比如海南岛的坡鹿,西藏昌都地区的白鹿,西藏的寿鹿和新疆西部的天山马鹿等。
白唇鹿: 除70年代初,我国送给斯里兰卡一对(现存一只)和80年代初送给尼泊尔一对外,其他任何国家都没有见过这种中国特产的鹿。
它的产地只限于青藏高原,包括西藏和青海的大部地区,甘肃中部和东南部,四川西部和北部。
它是高山区的动物,一般生活在海拔三四千米以上的山地,夏季甚至能上升到5000米,活动于高山灌丛或高山草甸区。
身上有厚密的长毛,不畏风雪严寒,以山草和灌木嫩枝叶为食,是非常顽强耐苦的鹿种。
白唇鹿的主要特征,正如其名所示,就是有一个纯白色的下唇,白色且延续到喉上部和吻的两端,所以亦可称为白吻鹿。
在甘肃、青海等地,俗名叫做黄鹿或草鹿。
白唇鹿夏毛棕黄色,与当地俗名叫做青鹿的马鹿有显著区别。
这两种鹿的鹿角也有明显的差异。
马鹿角的眉杈与次杈相距很近,白唇鹿角则相距较远,且次杈特别长,主枝略呈侧扁。
这些都不难辨别。
在白唇鹿和马鹿的产区互相重叠的地方,例如四川西北部和甘肃祁连山北麓,都曾发现过白唇鹿和马鹿自然杂交,并产生杂种后代的情况。
近年来,在青海、甘肃、四川,已有几处养鹿场开始驯养白唇鹿,其中以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治多县养鹿场养的最多,达到数百头。
据统计,该场从1958年到1979年,共捕获幼白唇鹿710只,驯养成活363只,成活率为51.13%。
另外,集体和个人也有分散饲养的。
据报道,现已能实行放牧饲养,这不仅可以减少饲料费,节约劳动力,而且也有助于改变它的野生习性,增加繁殖率。
在国家保护动物名单中,只有3种鹿属于第一类,即白唇鹿、梅花鹿和海南坡鹿。
梅花鹿: 梅花鹿,总的说来还算不上是稀有珍奇动物,因为这种鹿不但在公园、动物园里容易看到,而且在国内有很多养鹿场大批地饲养着。
但是仍可以把它归入珍稀动物的行列。
首先说“珍”。
这种鹿的鹿茸是各种鹿茸中价格最高的,在药材中被称为“黄茸”。
另外,鹿皮、鹿肉、鹿鞭、鹿尾、鹿筋,等等,也都有较高的价值。
所以说它是一种珍贵动物。
其次是“稀”。
家养的梅花鹿虽多,但野生的却特别稀少,不仅河北亚种和山西亚种野生的早已绝灭多年,连从前分布最广、数量最多的华南亚种和从前数量也很多的东北亚种,现在也都所剩无几,前途岌岌可危。
至于台湾亚种,野外究竟还有没有,很成问题,恐怕只有到动物园里还能找到一些。
所幸在60年代中期和70年代初,先后又在四川最北部的若尔盖和甘肃南部靠近四川边界的迭部,发现了一个梅花鹿新亚种,数量估计约有一二百头。
它们经常活动于混交林边缘或林间草地,有时与牛群同在一片草地吃草,有时与苏门羚、黑麂一起休息。
至今世界上任何一处动物园还未展出过这个新亚种,因此也可以认为是世上最稀有的动物之一。
对残余野生梅花鹿的保护工作,应作为重点看待。
江西彭泽县桃红岭是江西省唯一产梅花鹿的地方,估计这里还残留有100头左右的华南亚种,现在这里已被划为梅花鹿自然保护区。
梅花鹿亚种虽多,在形态上差别不大,只是在个体大小毛色深浅、斑点的多少和大小、背中线的长短和明显程度等方面,有不同程度的区别。
台湾亚种最小,肩高只有八九十厘米;东北亚种最大,肩高可超过110厘米,体重超过120公斤。
坡鹿: “坡鹿”是海南岛上的俗名,分类学上的名称叫艾氏鹿,也叫眉杈鹿。
共有三四个亚种。
在我国唯一的产地是海南岛。
这里的鹿究竟是不是单独的一个亚种,至今还有意见分歧。
坡鹿的大小和梅花鹿差不多,属于中型鹿。
肩高在105到110厘米之间,体重在60到100公斤之间,身上也有白斑,背部也有黑色中线。
它的最主要特征是角形特殊,不同于梅花鹿乃至其他各种鹿。
坡鹿的角有一个大而弯的眉杈,和后面的弯曲主枝接连起来,形成一个大角度的弧形。
主校下面不分杈,看来好像没有次杈、三杈,其实是分杈位置较高,长到主枝上端来了。
由于眉杈特别发达,所以外国著作中大都叫它眉杈鹿。
解放前,坡鹿在海南岛上的分布比较广,似乎除了北部以外,岛上至少有9或10个县的山地上,有相当多的坡鹿生存。
据估计,在解放初期还有300多只。
由于滥猎,到1979年,岛上只有东方县的大田和白沙县的帮溪二地,残余不过30多只。
经过最近几年的大力宣传和保护,情况有了明显的好转。
1983年5月间的调查表明,东方县的总数已增到80只以上。
生活在东方县大田珍贵动物保护区内的坡鹿,只经过一年多的人工保护,就已逐渐习惯跟人接近,有的走近村旁休息,有的对过往汽车、牛车也不逃避。
国际自然保护组织现在已将眉杈鹿,包括海南岛的坡鹿在内的各个亚种都划为第一级濒危动物,希望给予最严格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