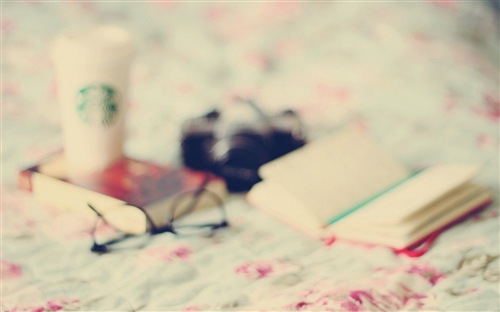保险公司擂台赛串词
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周六17:15、23:30首播,翌日中午11:20回放。
解说词:周秉建是周恩来的小侄女,许多人知道周秉建的名字是因为她曾经作为知识青年,在内蒙古草原当过一回牧民。
主持人:见到周秉建,她的年轻真的让我吃惊,她的样子完全不像是五十岁的人,可能是在内蒙待了二十多年的时间,她说普通话的时候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很特别的口音,偶尔还会夹杂进一两个蒙语单词,周秉建的性格也很豪爽,我说话的时候很喜欢说,为什么没有,她说,如果你要是说怎么不的话,可能更口语化一点,我说你的性格已经完全是蒙族人的性格了,她笑了,说她是牧民的性格。
下乡放羊 解说词:1968年给每一个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中国人都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
那一年,周秉建的父亲被人以与刘少奇专案有关的罪名关押起来了。
还不到16岁的周秉建也由于学校停课,待在家里。
面对社会和家庭的动荡,周秉建选择了当时被认为是青年学生应该选择的一条理想之路:上山下乡,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周秉建:我谁都没商量。
我已经年到半百吧,可能一辈子我自己真是,自己决定的只有几件事情,这恐怕是第一件吧。
我跟我的伯父(周恩来)说了一下,打电话报告了一下,写封信去说明我报名上山下乡已经得到批准,然后8月7号要离开北京,想到中南海去看一下伯伯(周恩来) 七妈(邓颖超)。
解说词:在中南海西花厅的那个傍晚,周秉建的选择得到了伯伯和七妈的支持。
被文革中众多国家大事困扰的伯伯周恩来破例地陪周秉建吃了晚饭,并把周秉建领到西花厅那满是国家大事的中国地图前议了一回家事。
而七妈邓颖超则送给了周秉建一份当时十分珍贵的礼物——《选集》。
第二天一早,周秉建就和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一起,汇集天安门广场。
随后踏上了前往内蒙古草原的人生之旅。
主持人:像你这么小的小孩,到了牧区你们能做些什么工作
周秉建:主要就是放牧,我们当时是四个人一组,都是女孩子,也都是一个学校的。
然后就白天出去放羊,一开始放羊不会的,一开始就怕羊跑,脑子里,尤其到冬天是不是出现龙梅、玉荣那样的暴风雪什么的,要为保护集体财产,这些思想我们都是有的,但是还好,然后也不敢,成天不敢让羊群撒开,刚撒开一点就把羊拢到一块。
实际这样非常不好,它吃不到草的话,肯定待不住,而且我们放的羊群也比较大,一千五六百只吧。
主持人:你当时做这些工作对你来说是特别快乐的,还是不行,我已经愁得不行了。
周秉建:当然快乐了,喜欢的就是这个嘛,所以我一直在牧业队工作,从来没有搞过农业活,不行,农业一无所知。
一封家书 解说词:周秉建初到牧区,正赶上内蒙古自治区搞与所谓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有关的内人党的冤案。
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原本是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支持指导下,早在 1925年就组建的一个带有统一战线性质的组织。
1928年,乌兰夫等人受中央指派负责内人党工作。
1947年,内人党完成使命,停止了工作。
这个组织的大多数人都转为受共产党组织的领导。
1968 年2月,康生指示在内蒙古抓内人党 ,搞得整个自治区人心惶惶。
周秉建:我刚才讲的写家信,当然是自然的了,除了生产生活以外,你肯定还要谈到,我们这个当地的运动是怎么怎么搞的,是如何如何进行的,跟伯伯七妈写信的时候就讲,我们大队有多少多少,三十几户人家,然后只有三户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百分之九十七的人家都是乌兰夫黑线上的人,然后怎么着,就觉得好象,也不太明白。
当然伯伯作为国家的领导人,他还是这么丰富的革命经历,他一下子就看出来这边在搞冤案。
主持人:等于他从你的信里里面知道内蒙很多真实的情况。
周秉建:对对对,后来中央做了调查了解,然后又召开会议,最后中央下了一个“5 .22”(5月22日)决定,就是在内蒙古自治区要停止扩大化这个运动。
解说词:内人党冤案导致了内蒙古36万4千多人受牵连,其中1万6千多人被整死,8万多人被批斗致残。
十多年后,周秉建才从邓颖超的一次谈话中了解到,周恩来确实是根据侄女来信得知了内蒙的情况,然后敦促中央派人调查此事,制止了冤案继续。
参军受阻 解说词:当时无数青年都向往着当一名军人,周秉建也不例外。
她做一辈子牧民的决心第一次有了改变。
在有关部门的照顾下,周秉建顺利地办妥了入伍的手续。
她所在部队的新兵连就驻扎在北京郊区。
于是,周秉建也再次回到了北京。
周秉建:然后来了以后,新兵连的领导还是很关心这几个知青的,说你们也挺不容易的,在牧区那么长时间,你们都回家看看,但是你必须是只能住一晚上,明天晚上就返回来,我们都挺高兴,当时领章帽徽没发。
是元旦那天,还是元月二号那天,反正是过新年嘛,就到西花厅了,自己还挺美呢,颠颠地跑进去了。
然后伯伯跟我一见面,说你能不能脱下你这身军装回内蒙古继续当牧民,第一句话,我真的没有想到,当时我一下脑袋“哗”一下大了,就觉得怎么问这个问题啊。
既然,我想我们家家教就别说了,老爷子问这个话不就是让你回去吗,我说可以啊,特小的声音,可能我自己听见,我不知道老爷子听着没听着,然后蔫蔫的,一点都不高兴了嘛。
然后吃饭,一边吃饭伯伯就问我,你这个过程怎么回事,我就一 二 三 四,从最开始怎么回事,一直到怎么出来的,整个应该说是汇报了,我想,讲得特详细,怎么怎么回事,伯伯说,但是我想,在内蒙古这么多青年人里面,能够挑选你来当兵参军,而不是让其他牧民的子女来当兵,是不是还是看在我的面子上。
说你看你爸爸现在还是被关押,在牛棚里没有被解放,按照我们国家的征兵有关的条例,规章制度是不允许的,那还用说吗,这一句话我还不明白,我也太傻了吧,我就不说话了。
然后我说那我知道了,然后说这样吧,就说你呢,既然来了,也不是说明天就回去,你就明天还回你的部队,还参加你的新兵连训练,至于什么时候走,有关部队领导会通知你的,这是我第一次哭。
主持人:因为是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建获得了参军的机会,但也因为是周恩来的侄女,她又不得不脱下军装再回到内蒙,如今回忆起那一段参军的波折,周秉建的声音很平淡,但我想这件事情,是她人生当中不小的一次挫折,因为自己特殊的身份,周秉建的确获得了一些机会,但因为这样一个特殊的身份,周秉建也失去了不少的机会。
顺利入学 周秉建:我也得提高学习,后来我一想那我就上学吧,挺逗的。
我说,我这文化水平也不行,老初中的底子太薄,要不然上学,不上学的话,老是小伙子们追的也挺麻烦的。
主持人:当时推荐你去哪儿去上学呢
周秉建:当时我报了一个中专,是我们内蒙古的蒙文专科学校。
但是后来录取通知书下来还是内蒙古大学,那我也没有办法了。
解说词:周恩来年谱中,有这样一段记载,1975年内蒙古自治区团委调周秉建担任共青团的宣传干部,被周恩来制止。
所以,这次能不能顺利入学,周秉建心中很不踏实。
周秉建:1975年春天,伯伯已经住院了,后来我就跟伯伯讲,当时内蒙古自治区团委,调我到自治区团委任宣传部的干部,我还是不愿意走,想当干部,我觉得还是在基层干得挺好的,挺适合我的,我想还是上学吧,伯伯说就是啊,让你去搞宣传工作,你不上学不学蒙古文字,语言文字不通的话,你怎么做宣传工作。
当时这样说的,后来我说我想到内蒙古上学,他说好啊,既然是在内蒙古工作生活,一定要学习掌握好蒙古族的语言和文字,这样才有利于你的工作和发展,后来反正怎么说呢,也是因为伯伯讲了,我心里比较有底了。
解说词:病床上的周恩来没有阻拦小侄女上学的事情,但这也是周秉建最后一次听到伯伯的声音。
周秉建在内蒙古大学蒙古语言文学系学习的第一个学期,周恩来逝世了。
嫁作蒙古妇 解说词:伯伯在周秉建心中有着极高的威望。
她和她的哥哥姐姐们遇到大事都要征得伯伯的同意。
和周恩来的一次谈话,对周秉建后来与蒙古族青年歌手拉苏荣之间的婚事,应该说是有影响的。
周秉建:从大寨回来的时候,我就路过一次北京,顺便回家看了看,那次伯伯又提新问题了,然后说,你今年多大了,我说十九了,这以后就问我找对象时候特逗。
然后又想了一会儿,伯伯说你以后能不能在内蒙古找一个蒙古族青年,我说可以吧,行啊,声音没这么痛快,不是,怎么说呢,反正也是声音没这么大,其实我心里,当时这个事,好象也还没有。
解说词:周秉建在内蒙古大学读书期间,曾经参加过访问朝鲜的青年代表团。
出访前的集训中,她认识了拉苏荣。
当时拉苏荣是内蒙古著名的乌兰牧骑演出团的青年歌手,而他的歌声是周秉建早已熟悉的。
周秉建:他当时有女朋友,我干吗要插足,我绝对不能干这事,很理智的,后来听说吹了,吹了就吹了。
主持人:他是经历过一次不太成功的婚姻,还是说…… 周秉建:你说不成功吧,有他这个第一次婚姻有一点,应该说有包办的因素,特别逗,他从内蒙古艺校毕业的时候,他们家一张电文,回来结婚,然后就回去结婚去了特别逗。
主持人:他们家肯定也会有顾虑吧
周秉建:他们家有什么顾虑,人家就是牧民,他妈妈就是牧民,有什么顾虑,不会的。
他自己有一点点负担,他就说这事万一不成,压力对我无所谓了,我解脱了,但是对他压力会很大,我说这事肯定成,我说我要成哪还有不行的,又不是跟别人结婚什么之类的。
解说词:1979年周秉建嫁给了拉苏荣,成了这个蒙古族家庭中的一员。
拉苏荣前妻留下的儿子已到了上学的年龄,婆婆有病在身需要照顾,两个妹妹也都没有成年。
但这些都没能阻止周秉建的爱情。
经过哥哥姐姐安排,她还把拉苏荣带到北京办了一次婚礼。
主持人:你七妈还送你一个礼物,也算是一个结婚礼物。
周秉建:当时她也刚从日本出访回来不久,她本来想送我一个日本小的傻瓜照相机,后来有人建议说,你还是给他留一个有纪念意义的,后来把伯伯那个,参加亚非会议的时候,日本的一个朋友送给他的一个照相机,把那个给小六做纪念吧,我想这更好,这个比那个应该更好。
后来因为当时家里很穷,欠了别人的债有七百多元。
主持人:谁欠的
周秉建:就我们家,应该说是我们家了,因为我已经嫁给他了,就是我们家了,原来拉苏荣欠的,因为他妈妈需要看病,妹妹们,工作上学,上学什么的,有一些开销。
然后七妈就说再补助你三百元,然后写了个收条,说你欠的这个钱我都可以帮你还上,但是我们觉得这样不好,对你会有一种依赖思想,应该靠自己的劳动来解决这个问题,解决困难什么的。
解说词:从1968年到1994年,周秉建在内蒙古生活二十六年,度过了她人生中最美好的一段时光。
在周秉建的家中,能够深深感受到她和丈夫对草原的眷恋。
主持人:你觉得你这一生谁对你的影响比较大
周秉建:谁对我影响大,牧民吧。
※※※※※※在网络仅限于网络的时代,渴望着一个没有月亮,没有星星,但有两双期待的瞳孔的夜晚。
因为这晚我可以不带面具,可以让思维穿过沉寂来到你身边,轻轻地敲着:一起聊聊好吗
本帖地址:[复制地址]
和上海姑娘有关的
上海姑娘有“嗲”的魅力,上海姑娘有“嗲”的风情,上海姑娘有“嗲”的文化,上海姑娘有“嗲”的智慧。
这也许是举世公认的。
这也许是您嗤之以鼻的。
这并非我是上海人,这也并非我听从几位上海网友的的忠告,要把汤本论坛办得有“上海味”。
而是因为,堂堂美国前副总统,共和党总统竞选人,丹.奎尔娶了上海姑娘为儿媳,刚刚受完三大拜,在上海参加完婚礼,回到美国,在脱口秀节目上,公开大赞儿媳。
我并不是要袒护上海女孩,我实际上在东北多年,性格中更多的是北方人的爽快和实在(再一次自吹自擂)。
也不是因为我的姐姐们青年时有姿色,中年时犹有风韵...,我便偏要替上海姑娘讲好话。
上海姑娘确实是好,好到我们美国总统柯林顿,在上海时,眼睛都转不过来了。
据随行人员讲,柯林顿总统对上海印象最为深刻。
他还许诺将来退休后,要到上海来开律师事务所。
柯林顿如果能成愿,不仅能够赚进大把绿色,还可饱览上海春色。
还是丹.奎尔的儿子先行一步,在上海学习、工作,喜交上海女孩,喜结上海良缘。
当新婚小夫妻双双向奎尔行大礼时,喜得这对前副总统夫妇闭不拢嘴。
上海姑娘真是很嗲,嗲字就是娇美,柔顺。
就是会撒娇。
丹.奎尔的儿子痴迷上的上海姑娘,想必一定有这些素质和气质。
可惜,前副总统奎尔本来就是连土豆也要拼错字的人,单词量太少,对“嗲”更是无法体味,只有一个劲地向节目主持人雷诺和现场观众,讲自己的儿媳妇是“Beautiful”、“Beautiful”以外,再也找不到别的词来了。
当然,英文永远翻译不出上海姑娘的嗲来。
事实上,自上海开埠以来,从小渔村变成东方的巴黎和纽约,全中国的美女,向黄浦江边倾流。
当然,绝姿绝色的,更是来自江浙一带的美女,她们眼睛亮丽娇媚,皮肤白晰,体型修长苗条.....端的是典型的江南美。
当然,上海姑娘的嗲,结了婚,有不少也是有变化的。
正象台湾名作家龙应台,写文章讽刺“啊,上海男人”。
上海男人的妻管严,做家务,伺候上海“嗲”小姐变成的凶太太,也是出了名的。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上海男人都这样,而且,还是有很多曾经是上海“嗲”小姐,现在也是上海“嗲”太太的女士。
不管如何,进入九十年代,上海姑娘的“嗲”更增添了现代女都市女郎的风情。
西方文明和东方文明在上海交汇,上海姑娘不仅濡染上西方流行服饰和化妆的美和西方文明的气质,还保留了东方女孩质朴的美,使得许多中国人欣赏上海姑娘的洋气的美,又使得许多西方人在欣赏上海姑娘的洋气,有一种同质感之外,又痴迷于她们内在的东方美。
尽管西风东浸,上海姑娘在感情性爱方面比以往的几代的上海姑娘开放很多,但相比西方女孩,还是东方。
上海姑娘之所以最受到西方尤其是美国男士的亲睐,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七十年代以来,上海的英语教育和社会学习英语的风气,始终是在全中国大陆首屈一指。
这又使得最聪明的上海姑娘们能以一口流利的英语来传递自己的“嗲”的天生丽质,“嗲”的性格,“嗲”的气质,“嗲”的风情。
当然,过去和现在,总是有一些“九斤老太”们在对开放的、现代化的姑娘们(不管是上海的还是北京的)说三道四,大加鞭挞,进行侮辱性的批评。
有的甚至不惜大谈自己在革命时期或者五十年代六十年代拥有如何纯洁的爱情,她们往往忘了,在革命口号下,她们潜意识地将革命政治利益背后所含有的经济利益,也在作某种权衡、估量、交换,只是不说出来,只是更虚伪罢了。
王实味所批评的革命根据地的“食分五等,车分四等”,并不是捏造的,更何况革命胜利之后。
既然如此,她们还有什么理由来指责相当于她们的女儿、或者孙女或者重孙女的女孩子们
人们应该观察到一个极为重要的现象,在中国大陆尤其是在上海的现代化进程中,人们的“个性化追求”日益强烈,这是一个重大的社会变化。
这是极为良性的社会变迁,体现在上海姑娘身上,是她们的强烈的个性追求,她们懂得自己事业追求和自己的情感追求,可以超越地区,可以超越国界。
对此,没有任何偏见,没有任何拘束。
只要自己爱的,只要自己喜欢的,只要是文明向上(当然包括物质上的享受)的,就要追求。
更何况具有“嗲”的魅力的上海姑娘们,尚未去追求别人,就有被中外间精英男士们所痴迷,所追求了。
也许是自然,也许是潮流,在主动和被动中,上海姑娘们被卷进潮流。
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的上层社会的政界、媒体、商界的单身或不单身的贵族们,正在向有“嗲”的魅力的上海姑娘们进攻,幽默一点讲,上海姑娘们,也正在向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的上层社会的政界、媒体、商界,大举“进攻”。
上海的,也是江南的“嗲嗲”的枕边风,温馨而甜美,柔和而飘逸,无微不至,直透人心... 上海春风,将会拂遍美国
上海春风,将会拂遍全世界
于是,国会议员考科斯从梦中醒来,出一身虚汗,大声惊叫:这里有没有间谍? 。
要弄清前面提出的问题,首先就得弄清什么是上海人。
但这并不容易。
余秋雨说:“上海人始终是中国近代史开始以来最尴尬的一群”(《上海人》)。
其尴尬之一,就是身份不明。
什么人是上海人
或者说,什么人是最正宗、最地道,亦即最有资格看不起外地人的上海人
谁也说不清。
因为认真说来,倘若追根寻源、寻宗问祖,则几乎大家都是外地人,而真正正宗的上海人,则又是几乎所有上海人都看不起的“乡下人”。
这实在是一件十分令人尴尬的事。
如果说,上海是一个“出身暧昧的混血儿”,那么,上海人便是一群“来历不明的尴尬人”。
然而,恰恰是这些“来历不明”的“尴尬人”,却几乎比其他任何地方的人,都更具有自己的特征,而且这些特征还十分鲜明。
的确,上海人和非上海人,几乎是一眼就可以区分开来的。
一个外地人一进上海,立即就会被辨认出来,哪怕他一身的海货包装。
同样,几个上海人到了外地,也会为众所瞩目,哪怕他们穿当地服装,也不说上海话。
当然,其他地方人,也有容易辨认的,比如北京人和广东人。
但北京人几乎总也改不掉他们说话的那种“京味儿”,而广东人除了一说话就“露馅”外,长相的特征往往也很明显。
只有上海人,才既不靠长相,也主要不靠口音,而能够卓然超群地区别于外地人。
说得白一点,上海人区别于外地人的,就是他们身上特有的那种“上海味”。
这种味道,几乎所有外地人都能感受得到,敏感的人更是一下就“闻”到了。
显然,上海人的特征,是一种文化特征。
或者用文化人类学的术语说,是一种“社区性的文化特征”。
它表现为一整套心照不宣和根深蒂固的生活秩序、内心规范和文化方式,而且这一整套东西是和中国其他地方其他城市大相径庭甚至格格不入的。
事实上,不管人们如何描述上海或上海人的社区特征,至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这些特征十分鲜明,而且与全国其他地区相去甚远。
也就是说,与其他社区相比,上海社区的异质程度很高(另一个异质程度很高的城市是广州)。
唯其如此,上海人才无论走到哪里都十分地“扎眼”,与其他人格格不入,并且到处招人物议。
坦率地说,我并不完全赞同对上海人的种种批评。
我认为,这些非议和闲话,其实至少有一半左右是出于一种文化上的偏见,而且未见得有多么准确和高明。
说得难听一点,有的甚至可能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即以一种相对落后的文化观念去抨击上海人,或者对上海的先进与文明(比如上海人特有的“经济理性”、“个体意识”甚至“卫生习惯”等等)“看不惯”或“看不起”。
比方说,看不惯上海人的衣冠整洁、处处讲究,就不一定有道理;看不起上海人喜欢把账算得很清,也大可不必。
但是,无论外地人对上海人的抨击和批判有理也好(上海人确有毛病),无理也好(外地人观念相对落后),上海与全国其他社区之间差异极大,总归是一个事实。
上海固然完全不同于农村(因此上海人特别看不起“乡下人”),也总体上基本上不同于国内其他城市(上海人所谓“外地人”,便主要指国内其他城市人)。
这也是上海与北京、广州的最大区别之一。
北京模式是“天下之通则”,省会、州府、县城,无非是缩小了和降格了的北京。
它们当然很容易和北京认同,不会格格不入。
广州则介乎北京与香港之间,既可以与北京认同,又可以与香港认同,更何况广州在岭南地区,还有那么多的“小兄弟”,何愁不能“呼朋引类”
上海却显得特别孤立。
它甚至和它的临近城市、周边城市如南京、杭州、苏州、无锡也“不搭界”,尽管上海曾被称为“小苏州”,而无锡则被称为“小上海”。
但上海固然早已不是苏州的缩影,无锡也决非上海的赝品。
更何况,别的城市或许会仿效上海,上海却决不会追随他人。
上海就是上海。
上海既然如此地与众不同,则上海人当然也就有理由同其他地方人划清界限,并把后者不加区别和一视同仁地都称之为“外地人”。
事实上,外地人如此地喜欢议论上海人,无非说明了两点,一是上海文化特别,二是上海文化优越。
北京优越但不特别,所以不议论北京人;云南的摩梭人特别但不优越,所以也没有人议论摩梭人。
只有上海,既优越又特别,所以对上海人的议论也就最多。
当然,也正是这些优越性和独异性,使上海人在说到“外地人”时,会发自内心、不由自主甚至不加掩饰地表现出一种优越感。
也许,这便正是让外地人受不了的地方。
人都有自尊心。
每个民族有每个民族的自尊,每个地区也有每个地区的自尊;当然也有每个地区相对其他地区的优越性(尽管可能会有点“自以为是”)和由此而生的优越感。
但是,优越感不等于优越性。
比方说,一个陕西的农民也会坚持说他们的文化最优秀,因为他们的油泼辣子夹馍是世界上最好吃的饭食,秦腔则是“世界戏剧之祖”,而信天游又特别好听等等。
但是,恐怕不会有谁认为陕西农村就是最先进和最优秀的社区。
要之,优越感是属于自己的,优越性则必须要别人承认。
上海文化的优越性恰恰是被人承认的。
尽管有那么多外地人同仇敌汽地声讨、讥讽和笑话上海人,但决没有人敢小看上海,也没有人会鄙夷上海,更没有人能够否定上海。
要言之,他们往往是肯定(尽管并不一定喜欢)上海,否定上海人。
但上海人是上海文化的创造者和承载者,没有上海人,哪来的上海文化
所以,上海人对外地人的讥讽和笑话根本就无所谓,当然也无意反驳。
你们要讥讽就讥讽,要笑话就笑话,要声讨就声讨吧
“阿拉上海人”就是这种活法,“关侬啥事体”
况且,你们说完了,笑完了,还得到南京路上来买东西。
上海人如此自信,不是没有道理的。
我们知道,真正的自信心只能来源于优越性。
没有优越性做背景,自信就不过是自大;而区别自信与自大的一个标志,就是看他敢不敢自己“揭短”。
没有自信心的人是不敢自己揭短的。
他只会喋喋不休地摆显自己或自己那里如何如何好,一切一切都是天下第一、无与伦比。
其实,他越是说得多,就越是没有自信心。
因为他必须靠这种不断地摆显来给自己打气。
再说,这种深怕别人不知道自己或自己那里有多好的心态,岂非恰好证明了自己和自己那里的“好”,并不怎么靠得住,别人信不过,自己也底气不足
否则,没完没了地说它干什么
上海人就不这么说。
当然,上海人当中也有在外地和外地人面前大吹法螺者。
但对上海文化多少有些了解的人一眼就能看出,那多半是“下只角”的小市民。
他们平常在上海不大摆得起谱,便只好到外地人那里去找平衡。
真正具有自信心的上海人并不这样做,至少他们的优越感并不需要通过吹嘘来显示。
相反,他们还会经常私下地或公开地对上海表示不满。
上海曾经深入持久地展开关于上海文化的讨论,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在那场讨论中,向来爱面子的上海人,居然纷纷投书撰稿,历数上海和上海人的种种不是,在上海的报刊上让上海人的种种丑陋纷纷亮相,揭露得淋漓尽致,而从学者到市民也都踊跃参加议论和批判(当然也有认为上海人可爱者)。
显然,这种讨论,在别的地方就不大开展得起来,比如在厦门就开展不了(厦门人懒得参加),在北京似乎也不大行(北京人不以为然),然而在上海,却讨论得轰轰烈烈。
上海人自己都敢揭自己的短,当然也不怕别人说三道四。
我这本书就是在上海出版的,我关于城市文化的一些文章也都在上海出版的《人民日报》(华东版)、《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发表。
上海人看了也许会有不同意见,但没有人认为不该发表,更没有人像当年扬州人对付我的同宗前辈易君左那样,要和我对簿公堂。
这无疑是一种有自信心的表现。
那些没有自信心的人,是不敢让“丑媳妇”公开亮相的,也是容不得别人提一点点意见的。
看来,除自称“大上海”这一点较北京为“掉价”外,上海人从总体上看,应该说显然是自信心十足。
的确,上海人对自己社区的优越性,似乎确信无疑。
除在北京人面前略显底气不足外,上海人对自己社区文化的优越性,几乎从未产生过怀疑。
一个可以证明这一点的众所周知的事实是,上海人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充满自信地把上海文化传播到哪里,而且往往能够成功。
建国以来,由于种种原因(支援边疆、支援三线、上山下乡等),上海人大批地走出了上海,来到北大荒、云贵川、新疆、内蒙,撒遍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他们在当地人那里引起的,首先是新奇感,然后是羡慕和模仿。
尽管他们当中不少人,是带着“自我改造”的任务去那里的,但他们在改造自己的同时,也在悄悄地改造着那里,在普及小裤脚、茄克衫和奶油蛋糕的同时,也在普及着上海文化。
改造的结果也是众所周知的:上海人还是上海人,而一个个边题小镇、内陆山城、乡村社区却变成了“小上海”。
无疑,这不是因为某几个上海人特别能干,而是上海文化的特质所致。
上海文化这种特别能够同化、消解异质文化的特质和功能,几乎像遗传基因一样存在于每个上海人的身上,使他们甚至能够“人自为战,村自为战”。
结果自然是总有收获:如果有足够多的上海人,他们就能把他们所在的地方改造成“小上海”。
如果人数不够,则至少能把自己身边的人(比如非上海籍的配偶)改造成半个上海人。
比如,在云南、新疆、黑龙江军垦农场,无论是其他城市的知青,还是农场的老职工及其子弟,只要和上海知青结了婚,用不了多久,都会里里外外变得像个上海人,除了他们的口音以外。
上海人(尤其是上海姑娘)就是有这种本事:如果上帝不能给他(她)一个上海人做配偶,他(她)就会自己创造一个。
似乎可以这么说,上海文化很像某些科幻影片中的外星生命体,碰到什么,就把什么变得和自己一样。
我们还可以这么说,北京文化的特点是有凝聚力,上海文化的特点则是有扩散力。
北京的能耐是能把全国各地人吸引到北京,在北京把他们同化为北京人;上海的能耐则是能把上海文化辐射出去,在外地把外地人改造为上海人。
显然,这种同化、消解异质文化的特质和功能,是属于上海社区的。
上海社区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上海人与非上海人之间的区别和差异,要远远大于上海人与上海人之间在身份、地位、职业和教养等等方面的区别和差异。
在北京或其他城市,你多半可以很容易地大体上看出一个人是什么身份,干什么的,或处于什么阶层,而在南京路上,你首先分辨出的,则是上海人和外地人。
至于上海人,除了身着制服者外,你就很难再看出什么名堂来他们几乎都一样地皮肤白皙、衣冠整洁、坐站得体、彬彬有礼,甚至连先前的人力车夫,也能说几句英语(尽管是“洋泾浜的)。
总之,他们都有明显区别于外地人的某些特征,即仅仅属于上海社区的特征,当然都“一样咯统统阿拉上海人”。
可见,“上海人”这个概念,已经涵盖和压倒了身份、地位、职业的差异和区别,社区的认同比阶级的认同更为重要。
因为上海文化强大的同化力已经差不多把那些差异都消解结果,在外地人眼里,上海就似乎没有好人和坏人、穷人和富人、大人物和小人物、土包子和洋鬼子,而只有一种人——上海人。
当然,上海人并不这么看。
在上海人看来,“上只角”和“下只角”、“上等人”和“下等人”,还是有明显区别的,只是外地人看不出。
况且,上海的舆论导向,似乎也倾向于社区的认同,或致力于营造上海社区的情调和氛围。
最能体现上述倾向的是那份《新民晚报》。
在国内众多的晚报中,它是名气最大风格也最为卓异的(另一份曾经差不多具有同等水平的是《羊城晚报》,不过现在《南方周末》似乎已后来居上)。
外地人几乎一眼就能看出它是上海的报纸,有着明显的上海风格。
但对上海人,它却是真正地“有读无类”,小市民爱看,大名流也爱读。
总之,它对于上海的读者,也是“一样咯”统统看作“阿拉上海人”的。
它的“个性”,只是上海文化的个性。
或者说,只是上海的社区性。
上海的社区性无疑是具有优越性的。
我们知道,文化的传播有一个规律,就是“水往低处流”,亦即从相对比较先进文明的地区向比较落后的地区传播,而同化的规律亦然。
当年,清军铁马金戈,挥师南下,强迫汉人易服,试图同化汉文化,结果却被汉文化所同化,就是证明。
上海文化有这么强的传播力和同化力,应该说足以证明其优越性。
然而,这样一种文化,却只有短暂得可怜的历史。
尽管上海人有时也会陶醉于春申君开黄浦江之类的传说(上海的别号“申城”即源于此),但正如世代繁衍于此的“正宗上海人”其实是“乡下人”,上海作为现代都市的真正历史,当始于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之后、1843年11月7日的正式开埠。
在此之前,直至明末清初,上海不过“蕞尔小邑”,是个只有10条巷子的小县城。
到清嘉庆年间,亦不过60条街巷,并以通行苏州话为荣。
可是,开埠不到二十年工夫,上海的外贸出口便超过了中国最早的通商口岸广州。
1861年,上海的出口份额占据了全国出口贸易总额的半壁江山;九年后,广州已不敢望上海之项背(上海63%,广州13%)。
难怪作为“后起之秀”的香港也被称为“小上海”,而不是“小广州”,尽管广州在地理上要近得多,文化上也近得多。
正如1876年葛元煦《游沪杂记》所言:“向称天下繁华有四大镇,日朱仙,曰佛山,曰汉口,曰景德。
自香港兴而四镇逊焉,自上海兴而香港又逊焉。
” 以后的故事则是人所共知的:上海像巨星一样冉冉升起,像云团一样迅速膨胀。
1852年,上海人口仅54.4万,到1949年,则已增至545.5万。
增长之快,虽比不上今天的“深圳速度”,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却已十分惊人。
与此同时,上海的地位也在急遽上升。
1927年7月,即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三个月后,上海因其“绾毂南北”、“屏蔽首都”的特殊地位而被定为“特别市”,从此与县城省治告别,成为完全意义上的城市型社区。
它甚至被称为“东亚第一特别市”,成为当时国民政府的国脉所系。
与北京从政治中心退隐为文化本位城市相反,作为世界瞩目的国际大都会和新兴市民的文化大本营,上海开始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越来越多地发挥着举足轻重和无可替代的作用。
资产阶级大财团在这里崛起,无产阶级先锋队也在这里诞生;西方思想文化从这里输入,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在这里传播。
一切具有现代意义、与传统文化截然不同的新东西,包括新阶级、新职业、新技术、新生活、新思想、新观念,甚至新名词,差不多都最先发初于上海,然后才推行于全国。
一时间,上海几乎成了“新生活”或“现代化”的代名词,成了那些不安分于传统社会、决心选择新人生道路的人的“希望之邦”。
在上海迅速崛起为全国最大的工业、商贸、金融、航运中心,崛起为远东首屈一指的现代化大城市的同时,它在文学艺术方面的成就也堪称亚洲第一。
事实上,从某种意义上说,上海也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
在这方面,它至少是可以和五四运动的策源地北京共享声誉的。
当北京大学、燕京大学的图书馆还不屑于收藏新小说时,上海却已有了22种以小说命名的报刊(全国29种)。
更不要说它还为中国贡献了鲁迅、胡适、陈独秀、茅盾、巴金、郭沫若、瞿秋白、叶圣陶、郁达夫、徐志摩、戴望舒、林语堂、刘半农、陶行知、胡风、周扬、夏衍、田汉、洪深、聂耳、傅雷、周信芳、盖叫天等(这个名单是开不完的)一大批文化精英和艺术大师。
至于它所创造的“海派文化”,更是当时不同凡响,至今余响未绝。
这真是令人叹为观止。
哲人有云“人类是擅长制造城市的动物”,但上海的崛起似乎也太快 事实上,上海文化在这么短暂的时间内就成了“气候”,而且是“大气候”,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
上海社区文化性格的秘密,当从这一奇迹中去找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