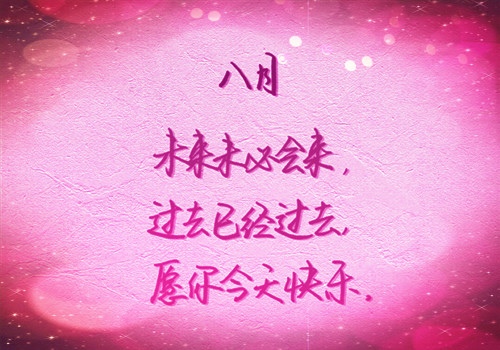前苏联有什么著名小说
(要作者)
帕斯捷尔纳克写的[日瓦戈医生》是部经典,是20世纪俄罗斯文学留给世人的一部经典。
就其诞生的年代而言,它无疑是苏联文学的经典之一,而且是一部真正的、严格意义上的经典,是无须添加任何定语的经典。
不知谁是始作俑者,苏联文学(包括当代中国文学)中的许多所谓主旋律作品被冠以红色经典的称谓。
恕笔者直言,当今常挂在人们嘴边的所谓红色经典(无论是苏联的还是中国的),就其实质而言,乃是在高度政治化、高度意识形态化的社会-文化生态环境中衍生出的一种文学怪胎,不知率先发明出红色经典这一称谓的人究竟是出于赞赏,还是出于讥讽。
其实,真正的文学经典是不能添加任何色素的。
那些所谓红色经典,那些够不上经典的红色经典,也许恰恰是因为无法承受经典二字沉重的分量,才无奈地躲进了红色二字的保护伞下。
经典要求作家有一种宏大的历史视野,人们要求经典具有史诗的风采。
记得帕斯捷尔纳克曾说过,《日瓦戈医生》是我第一部真正的作品,我想在其中刻画出俄罗斯近45年的历史。
不错,1905年革命、一次世界大战、二月革命、十月革命、新经济政策……《日瓦戈医生》里所涵盖的这一切历史事件似乎都可以满足企图领略历史沧桑的人们的渴求。
难怪美国人埃德蒙·威尔逊会喜不自禁地把它同《战争与和平》这部巨作相提并论。
不过,对于在历史震荡与变迁中滋养出艺术创作灵感的苏联作家们,这种宏大的叙事眼光是共同的,在苏联文学中,几乎每一部卷帙浩繁的长篇巨著都包含了广阔的历史与现实的画卷。
然而,远非每一部这样的巨作都可被视为传世之经典。
经典毕竟是寥若星辰的。
能够踏入经典之殿堂的,恐怕只有那些对现实与历史充满了强烈的批判意识,实现了对现实生活的超越的作品。
文学的本质就是对现实的审美化的否定与超越。
如果没有了对现实生活的否定与超越精神,艺术的生命也就不复存在。
这是艺术的基本价值所在,艺术的天性使然。
品读《日瓦戈医生》,可以发现,在其字里行间浸透着强烈的批判意识。
记得在十多年前的那场《日瓦戈医生》热中,许多人都在饶有兴趣地反复琢磨:这部小说究竟是否反对十月革命
帕斯捷尔纳克对苏联近30年的历史变迁到底持何种态度
一时间,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似乎也就决定了对该小说的不同的价值判断。
于是,一种颇滑稽的局面形成了:那些实在难以割舍对《日瓦戈医生》这部杰作的青睐的人,只好千方百计地竭力否认作家心中存有哪怕半点儿对历史与现实的否定性。
当年评论家沃兹德维任斯基说:无论日瓦戈,还是帕斯捷尔纳克本人,都谈不上是反对革命的人,谈不上对抗革命。
他的说法恐怕体现了大多数喜爱这部作品的人的心态。
但是,笔者以为,在这个问题上,似乎45年以前反对刊登这部小说的《新世界》杂志那五名编委的感受更实在些。
他们确确实实觉察出了蕴涵在小说中的对历史和现实的批判。
的确,《日瓦戈医生》充满了批判的锋芒,正如一切我们时常津津乐道的那些西欧19世纪的名著、20世纪西方现代主义杰作乃至后现代主义之作都充满了对新兴资本主义社会、工业化社会乃至后工业化社会的尖锐而深刻的批判与否定一样,《日瓦戈医生》也同样闪烁着批判的锋芒。
倘若现在还把批判与否定的精神只赋予伟大的19世纪俄罗斯文学;倘若现在还以为新生的苏联文学只能为新生的苏维埃社会献上甜美的赞歌,那就未免太滑稽了。
但是,虽然当年那五个编委嗅出了小说的批判味儿,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对小说的否定精神有正确的理解。
今天,我们似乎不必再去纠缠这部小说是不是否定了十月革命。
毋庸置疑,帕斯捷尔纳克当然是以否定的眼光来看待他所描述的那段历史的。
但倘若以此就断言他对十月革命有着天生的反感,那就错了。
他并不是带着一种与生俱来的仇恨去批判历史与现实的,他丝毫没有存心要与十月革命过不去。
他批判的锋芒只是源自他身上那种天然的艺术家的本性,即对现实的批判眼光。
诚如美国学者罗伯特·佩恩所言,有些西方评论家把日瓦戈医生看成是对抗苏维埃政权的人物。
这种看法并不正确,因为他们没能够发现,这部作品其实是对一切存在着的政权的反抗。
这说到了点子上。
虽然我们很难驳倒英国人海伍德的说法,即帕斯捷尔纳克1946年开始写的《日瓦戈医生》,是存心构思出来针对斯大林及其政体所维护的一切的一种挑战,但我们必须把这种挑战理解为对既定现实的一种形而上的否定。
多么出色的手术啊
拿过来就巧妙地一下子把发臭的多年的溃疡切掉了
既简单又开门见山,对习惯于让人们顶礼膜拜的几百年来的非正义作出了判决。
出自小说主人公日瓦戈之口的这句名言不知多少次被人们引用,想以此作为主人公日瓦戈对降临到俄国大地上的革命风暴的向往。
其实,这句话与其说是表现了日瓦戈对革命风暴的赞赏,倒不如说是对他所生活过的俄国社会的批判。
这句名言同主人公后来对十月革命的种种使我们心中颇存不安的反思在实质上是相通的,即都体现了小说主人公日瓦戈作为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所理应具有的精神独立的气质和批判意识。
帕斯捷尔纳克赋予小说主人公乃至整部作品的这种对现实与历史的批判和超越意识,使这部作品具有了成为经典的可能。
毕竟,真正的艺术怎么能没有对现实的批判与超越呢
波兰作家贡布罗维奇说得好:我觉得任何一个尊重自己的艺术家都应当是,而且在每一种意义上都必然是名副其实的流亡者。
这所谓流亡者,在笔者看来,更多是指精神上的流亡者,而且是自我流亡者。
这样的艺术家才会真正不为历史所遗忘,因为只有这样的自我流亡者才会真正获得当年陈寅恪先生所云的摆脱了俗谛的独立之精神;才会超越当下的社会主流意识赋予作家的,并非为他自身所拥有的所谓政治思想而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之思想。
回望近70年的苏联文学,在这个曾自封为最有光辉的思想的文学里,那些跟在时代后面放声歌唱,在时代吹奏的笛子下跳着优美舞步的带色素的所谓经典,也能算是真正的经典吗
经典之所以为经典,往往在于它能站在思考人的存在意义、生命价值的精神高度对历史进程予以文化的批判。
40多年前,当《日瓦戈医生》被封杀在《新世界》杂志编辑部里时,包括帕斯捷尔纳克及其妻子季纳依达在内的许多人都纳闷,为什么杜金采夫的《不是单靠面包》尽管遭到部分人的围攻,却可以出版问世。
在他们眼里,似乎这部小说才是真正揭露了社会的阴暗面。
倘若帕斯捷尔纳克本人果真是这么想的话,那么显然,这位伟大的诗人倒是由于自己天真单纯的诗人气质而没能意识到,自己的小说虽不象杜金采夫的成名作那样直接地针砭时弊,却在另一个更高的意义上触及了当权者脆弱的神经。
日瓦戈医生身上的叛逆性,是洛巴特金所无法比拟的。
这种叛逆性不是指向具体的某种官僚习气,不是指向显在的体制问题,而是以文化批判的高度指向了人的精神的内在层面。
对于文学来说,只有这种意义上的文化批判才会真正超越时代的局限。
能否站在文化批判的高度审视现实,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讲是至关重要的。
当年高尔基就俄国革命所阐发的种种不合时宜的思想,这位革命文豪对俄国革命的深刻反思,充分显示了一个坚持文化操守的文化人在激烈的政治动荡岁月中冷静与深远的头脑。
对俄国革命中滋生的俄罗斯人蛮性与奴性,无论是革命文豪高尔基,还是旧俄式知识分子帕斯捷尔纳克,都做出了深刻的反省。
虽然帕斯捷尔纳克头上永远也不会有革命二字的光环,但这种站在人类文化精神立场对历史与现实的审视和批判,是两位艺术家的共通之处。
在政治动荡的年代里,对文化操守的坚持是最可贵的,它对人类一切功利的思维与行动都具有一种透彻的批判意识。
这种坚持文化操守的批判意识往往会被人扣上保守的高帽。
狄更斯在《双城记》里对法国大革命的表现可谓是充满了感伤的保守主义情绪,高尔基这只呼唤暴风雨的海燕也在暴风雨真正到来之际又突然变得顾虑重重,还有我们的鲁迅,亦曾被年轻一代斥为封建余孽。
然而,当我们后辈人经历了历史的荒诞性的洗礼之后,难道没有理由钦佩这些文化先哲们深远的目光吗
对鲁迅,甚至对高尔基的那些指责如今似乎都成为我们的笑谈了,难道40多年前对帕斯捷尔纳克的非难就不是荒唐的吗
这种对历史与现实的超越了普通政治层面的思考,这种克服了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和政治功利主义情绪,以人类最广泛的永恒的、共同的情感为旨归的批判与超越意识,是文学经典的重要特质。
美国人威尔逊把《日瓦戈医生》概括提炼为革命-历史-生命哲学-文化恋母情结这十四个字,颇为精当。
人们常说这部小说浸透了对基督教教义的评论、关于生命和死亡的思考、关于自由与真理的思考、关于历史与自然和艺术的联系的思考;人们常说帕斯捷尔纳克是以某种不朽的人性,以某种先验的善和正义等宗教人本主义观念作为参照系来审视革命运动和社会历史变迁的。
由此,人们自然将日瓦戈医生这个高度自我中心的人物视为远离人民大众、远离时代前进步伐的旧式贵族知识分子,并进而把小说视为一个站在历史潮流之外的知识分子对历史进程的病态的感伤,从而怀疑小说的思想的正确性。
然而,这种以个性的、自主性的对当时的集体意识的批判性思考,这种从哲学上对社会历史变迁的透视,正是知识分子以其独立的理性精神审视世界的可贵方式,《日瓦戈医生》对俄国历史的思考的非政治性,恰恰是这部小说的价值所在。
一百年前政治上异常反动的老托尔斯泰依然作为文学经典大师永存于历史的长河中,这已是无可置疑的事实了,那么,帕斯捷尔纳克的这部以哲学与文化的反思超越了当下社会意识形态层面,揭示了人的存在的意义,揭示了人的存在的悲剧性色彩等广泛的形而上问题的小说《日瓦戈医生》呢,这不也是一部永恒的经典吗
帕斯捷尔纳克曾经说过,艺术家是与上帝交谈的。
这是对艺术家提出的颇高的要求,这就要求艺术家以探寻历史的真谛、人性的真谛,倾听生活最深处的声响的精神面对浮躁的现实人生,揭示出现实与历史的洪流巨变中人的存在的悲剧性,揭示出历史进程的荒诞性。
《日瓦戈医生》正是这样的精神产品,难怪威尔逊称赞它是人类文学史和道德史上的重要事件,是与20世纪最伟大的革命相辉映的诗化小说,而帕斯捷尔纳克,作为现代苏联文学谜一般的巨人,正是人们开启俄国文化宝库和知识分子心扉的专门钥匙。
20世纪发生在俄国的这场革命被历史的实践赋予了悲壮的色彩。
苏联人民所经历的从精神到肉体上的一切痛苦,都与这场革命的矛盾的两重性有内在的联系。
20世纪俄罗斯文学的经典,是应当能够深刻地表现这具有悲剧性色彩的两种精神特质的,文学经典之所以为经典,就在于能在对人的精神层面的把握中深刻地洞察时代的本质精神内涵。
在《日瓦戈医生》中,安季波夫(斯特列尼科夫)的形象正是俄国革命深刻的矛盾性的体现。
他不是一个纯粹的政治动物,他既是纯洁的体现,又是一个被时代和政治异化了的工具;他虽然铁石心肠,但仍有一星半点不朽的东西。
精神的这种两重性不正是预示着20世纪俄罗斯人所面临的坎坷经历吗
文学经典不是无根的浮萍,经典之花是深深地扎根在文学传统的精神土壤里的。
《日瓦戈医生》是20世纪的史诗,但我们显然能于其间感受到影响的焦虑的:帕斯捷尔纳克这位渴望描绘当代历史的诗人却无时不让我们体验到传统的力量。
也许,企图在日瓦戈医生身上找寻罗亭、李特维诺夫、伊凡诺夫、特里戈林亦或特里勃列夫的影子;在拉拉身上寻觅塔吉娅娜亦或娜斯塔西娅·菲里波芙娜的痕迹;在冬尼娅身上寻找娜达莎·罗斯托娃亦或吉提的身影;在安季波夫身上嗅出拉赫梅托夫、巴扎洛夫甚至历史真人涅恰耶夫的气味,均是徒劳的,但有一点不可否认,那就是从《日瓦戈医生》里我们清晰地体会到了那种只有俄罗斯的知识分子才具有的对世界、对生命的体悟方式。
日瓦戈也好,帕斯捷尔纳克也罢,都是以俄国知识分子典型的生活方式生活着,他们思考着只有俄国知识分子才会去琢磨的问题。
上帝-死亡之谜-俄罗斯母亲的命运,这曾萦绕在果戈理、老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俄罗斯文化巨匠们心头的永恒的疑虑,正是帕斯捷尔纳克以及他所心爱的主人公日瓦戈最关切的纯粹俄罗斯式的问题。
日瓦戈,以及他的创造者作家帕斯捷尔纳克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对生活真谛,对真理的独立的精神探寻,抗争对人的精神奴役,使他们成为了别尔嘉耶夫所说的俄国特有的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俄国知识分子)中的一员。
在苏联,保持这种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精神传统更需要有极大的勇气,正因为此,这种精神传统在苏联文学中才显得尤为珍贵,也只有在艰难的岁月中坚守这个精神资源的苏联作家,才会在历史的长河中写下自己的名字。
帕斯捷尔纳克是有这样的资格的。
不过,一切思想与精神探寻倘若不能以诗的意蕴呈现出来,那么就不可能诞生文学的经典。
我们永远不该忘却别林斯基在他那篇著名的《1847年俄国文学一瞥》里所阐明的朴素道理:不管一首诗充满着怎样美好的思想,不管它多么强烈地反映着现代问题,可是如果里面没有诗歌,那么,它就不能够包含美好的思想和任何问题,我们所能看到的,充其量不过是执行得很坏的美好的企图而已。
苏联文学中有多少光辉思想正因为没有了诗性的融注而黯然失色,而《日瓦戈医生》,这部因为涉及到十月革命而使我们不得不谨小慎微待之的小说,却因为它首先是一首诗,一首爱情诗,从而使它所包含的一切关于社会、宗教、历史的思考真正地具有了震撼力。
西班牙作家略萨称这部小说是抒情诗般的创作;利哈乔夫把它看作是对现实的抒情态度,都是精辟之见。
的确,《日瓦戈医生》最大的独特性就在于它以诗的韵味审视了俄国革命的历史。
这首拉拉之歌所表达的革命-历史-生命哲学-文化恋母情结的主题,是那些充斥着激昂的政治说教的伪文学作品所无法替代的。
作家对人生的探索,对历史的沉思,他的一切追求与苦闷,均是从日瓦戈与拉拉的爱情曲的闪光中折射出来的。
作家幻想出了一个只属于日瓦戈与拉拉这两个充满真正人性之光芒的人物的世界。
在这个世界里,他们懂得生命之谜、死亡之谜、天才之魅力和袒露之魅力;在这个世界里,他们可以与象重新剪裁地球那样卑微的世界争吵毫不相干;在这个世界里,心灵、艺术、美、大自然可以浑然一体,人与大地和宇宙紧紧相连,艺术为美而服务,人,充满理性与情感的人,沉浸在艺术创造的神秘的幸福中,沉浸在爱情的甜蜜中,沉浸在宁静的生活的温馨中,沉浸在夜的庄严的寂静中,永远真诚地生活、思考,不会为真理感到害羞,不必去出卖最珍贵的东西,夸奖令人厌恶的东西,附和无法理解的东西。
然而,这个美丽的童话般的世界,日瓦戈与拉拉的世界,在诗人笔下被无情地摧毁了,这个迷人的世界无法与现实的、充满功利色彩的世界相对抗,等待它的只能是悲剧性的毁灭。
人的正直与善良在特定历史事件面前变得软弱无力,注定要被毁灭,这种悲剧性的历史悖论仿佛是文学经典向我们提出的永恒的疑惑。
也许,感受这份无奈与遗憾才是最经典的美。
人们或许会因此而珍重苏联文学,珍重这创造了格利戈里·麦列霍夫的悲剧、日瓦戈的悲剧等等这些经典之美的苏联文学。
立足于时代又超越那个时代;超越现实的桎梏牢笼又回归传统的精神家园,当这一切发生在一位只会以抒情诗人的眼光走进生活的艺术家身上时,我们可以说,经典的产生为期不远了。
《日瓦戈医生》正是这样的文学经典,它的经典性,远不是每一部被写进苏联文学史教科书的作品所能具备的。
有些作品将永远被文学史所记忆,因为它们标志着文学发展历程的特定阶段(如《解冻》、《一个人的遭遇》等),或者本身就是特定历史时期的典型代表(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但它们并不能成为严格意义上的文学经典。
能够跨入经典的行列的唯有那些超越了当下的狭隘政治层面和民族主义情绪,表达了人类共通的、永恒的情感的作品。
在20世纪俄罗斯文学中,《日瓦戈医生》是能够与《静静的顿河》、《大师与玛格丽特》等屈指可数的作品一道跨入经典之门的。
求有关遗忘的名言或素材
幸福在于爱,在于自我遗忘。
——当代哲学家、学者、作家 周国平 行动被人们遗忘,结果却将永存。
——古罗马诗人 奥维德 遗忘名言所以选择用颠沛流离的生活来遗忘。
——女作家,原名励婕 安妮宝贝 而我,会把这一些放在逐渐的遗忘中。
——女作家,原名励婕 安妮宝贝 没有行动的绝望是对义务的遗忘和违犯。
——前苏联作家,诗人 帕斯捷尔纳克 高尚的思想即使被人遗忘,也不会消亡。
——古罗马哲学家 绪儒斯 遗忘的名言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悲伤也抵不过时间。
——台湾女诗人,散文家 席慕容 为伟大事业献身的人,永远不会被人们遗忘。
—— 不是谁离开了谁就无法生活,遗忘让我们坚强。
——女作家,原名励婕 安妮宝贝 若不是笔帮助了剑,恺撒大帝可能早已被世人遗忘。
—— 亨·沃思 爱情这东西,就算曾经刻骨铭心,也会被遗忘在下一个眨眼间。
——台湾言情小说作家 席绢 《珠玉在侧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经典名句(急求,10句以上)
①人最宝贵的东西命.生命来说只有一次.因此,人的一生应样度过:当一个人回首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这样,在他临死的时候,能够说,我把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人生最宝贵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奋斗。
我们必须抓紧时间生活,因为即使是一场暴病或意外都可能终止生命。
②领袖的逝世没有引起党的队伍涣散。
就像一棵大树一样,强有力的将根深深地扎入土壤中,即使削掉树梢,也绝不会因此而凋零。
③收起枪,别跟任何人说。
哪怕,生活无法忍受也要坚持下去,这样的生活才有可能变得有价值。
④数千人形成一个强大的变压器,形成一种永不枯竭的原动力。
⑤“不必召开群众大会了,这里没有哪个人需要宣传鼓舞,托卡列夫,你说话很准确,他们确实是无价之宝,钢铁就是这样炼成的
”朱赫来说的。
1974年的阅读与情感以死亡的想象沉思生命他徘徊于悼别与憧憬之间以独白的句式承诺无所悔恨的人生那是一个俄罗斯青年曾经响亮的名字那是一个朴素时代曾经不朽的世界名著被遗忘的格言抄在被遗弃的塑料日记本的扉页上昔日的偶象淹没于今天眼花缭乱的明星排行榜而1974年的春天保尔?柯察金几乎是你唯一的阅读那些温暖的逃学的下午断墙外低矮的树林里你沉醉于最初的崇拜也惶恐于最初的迷恋一遍遍你持久地、秘密地想念着冬妮娅想念着歌唱在山楂树下的美丽少女倾刻间缠绵的露水吞没于革命的激流心碎的冬妮娅凝视着保尔的一脸忧愁昨夜的爱情与明天的斗争对峙在这告别的黎明而在美丽与神圣之间英雄只能有一种背叛艰苦地你跋涉在繁体字的丛林中幻想革命与爱情的完美妥协期盼神圣与美丽握手言欢而结局终于来临在一个冬天的车站你目睹了他们最后的相逢最后的决别风雪中的保尔手握铁镐的布尔什维克以“公民”称呼自己最初的恋人无言的冬妮娅凄楚的冬妮娅在泪光里承受着无情的阶级蔑视保尔坚定地踏入风雪踏入冬季的烈焰这是苏维埃的革命之火一个英雄必经的考验而此刻你终于明白钢铁就是这样炼成的低矮的树林里你捧着泛黄的书页少年的眼神凝视着天空阳光在泪水中映出彩虹吟诵着保尔的名句意志的力量使你颤栗而冬妮娅,当你再次默读她的名字有一种感觉几乎令你窒息那时你正历经热烈而脆弱的年龄只能以敬畏代替模仿以眼泪代替血1974年彷惶而无从堕落的岁月一个布尔乔亚的少女成为你仅有的心事二十多年前的初夏,我恋上了冬妮娅那一年,“文化大革命”早已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革命没有完,正向纵深发展。
恋上冬妮娅之前,我认识冬妮娅已近十年。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我高小时读的第一本小说。
一九六五年的冬天,重庆的天气格外荒凉、沉闷,每年都躲不掉的冬雨,先是悄无声息的下着,不知不觉变成了令人忐忑不安的料峭寒雨。
强制性午睡。
我躲在被窝里看保尔的连环画。
母亲悄悄过来巡视,收缴了小人书,不过说了一句:家里有小说,还看连环画
从此我告别了连环画,读起小说来,而且是繁体字版的。
奥斯特洛夫斯基把革命描写得引人入胜,我读得入迷。
回想起来,所以吸引人,是因为他描写伴随着恋爱经历的革命磨炼之路:保尔有过三个女朋友,最后一个女友才成为他的妻子;那时,他已差不多瘫痪了。
质丽而佐以革命意识的达雅愿意献身给他--确切地说,献身给保尔代表的革命事业。
革命和爱欲都是刺激性的题材,象时下的警匪与美女遭遇的故事,把青少年弄得神情恍惚,亢奋莫名。
但革命与癌症的关系我当时并不清楚,究竟是革命为了爱欲,还是爱欲为了革命
革命是社会性行为,爱欲是个体性行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而爱欲是偶在个体脆弱的天然力量,是“一种温暖、闪烁并变成纯粹辉光的感觉”……象大多数革命小说一样,爱欲的伏线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故事中牵动这革命者的经历,但革命与爱欲的关系相当暧昧,两者并没有意外相逢的喜悦,反倒生发出零落难堪的悲喜。
在“反”革命小说中,革命与爱欲的关系在阴郁的社会动荡中往往要明确得多。
帕斯捷尔纳克写道,拉娜的丈夫在新婚之夜发觉拉娜不是处女,被“资产阶级占有过”,于是投奔“资产阶级”的革命;日瓦戈与拉娜的爱情被描写成一盏被革命震得剧烈摇晃的吊灯里的孱弱烛光,它有如夏日旷野上苍凉的暮色,与披红绽赤的朝霞般的革命不在同一个地平线。
爱欲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处于什么位置
它与那场革命的关系究竟怎样
从一开始我就下意识地关心冬妮娅在革命中的位置。
我老在想,为何作者要安排保尔与冬妮娅在冰天雪地里意外重逢
在重逢中,保尔用革命意识的“粗鲁”羞辱初恋情人的惊魂,说她变得“酸臭”,还佯装不知站在冬妮娅身边的男人是她丈夫。
这样来叙述自己的初恋,不知是在抱怨革命对初恋的阉割,还是在报复初恋中染上的资产阶级的蓝色水兵服和肥腿裤上的异己阶级情调。
出逃的前夜,保尔第一次与冬妮娅搂抱在一起好几个小时,他感到冬妮娅柔软的身体何等温顺,热吻象甜蜜的电流令他发颤地欢乐;他的手还“无意间触及爱人的胸脯”……要是革命没有发生,或革命在相爱的人儿与温柔之乡紧挨在一起的时候戛然而止,保尔就与资产阶级的女儿结了婚,那又会是一番故事。
他们发誓互不相忘。
那时保尔没有革命意识,称革命为“骚乱”。
热恋中的情语成了飓风中的残叶,这是由革命意识造成的吗
这部小说我还没有读完第一遍,大街上、学校里闹起了“文化大革命”。
我不懂这场革命的涵义,只听说是革“资产阶级”的命;所有资产阶级都是“酸臭”的,冬妮娅是资产阶级的人,所以冬妮娅是“酸臭”的。
可是,为什么资产阶级的冬妮娅但爱抚会激起保尔这个工人的孩子“急速的心跳”,保尔怎么敢说“我多么爱你”
我没空多想。
带着对冬妮娅“酸臭”的反感,怀揣着保尔的自传,加入“文化大革命”的红小兵队伍,散传单去了。
其实,一开始我就暗自喜欢冬妮娅,她性格爽朗,性情温厚,爱念小说,有天香之质;乌黑粗大的辫子,苗条娇小的身材,穿上一袭水兵式衣裙非常漂亮,是我心目中第一个具体的轻盈、透明的美人儿形象。
但保尔说过,她不是“自己人”,要警惕对她产生感情……我关心冬妮娅在革命中的位置,其实是因为,如果她不属于革命中的一员,我就不能(不敢)喜欢她。
“文化大革命”已进行到武斗阶段。
“反派”占据了西区和南区,正向中区推进;“保派”占据了大部份中区,只余下我家附近一栋六层交电大楼由“反派”控制,“保派”已围攻了一个星期。
南区的“反派”在长江南岸的沙滩上一字儿排开几十门高射机关枪,不分昼夜,炮击中区。
不能出街,在枪炮声中,我读完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就在那天夜里,自动步枪的阵阵扫射通宵在耳边回荡,手榴弹的爆炸声不时传进我阵阵紧缩的恐惧中;总攻交电大楼的战斗在我家五百米远的范围激烈进行。
清晨,大楼冒起浓烟。
“保派”通宵攻击未克,干脆放火,三面紧缩包围。
死守的“反派”们终于弃楼而逃。
我家门前的小巷已经封锁了,三四个与冬妮娅一般大的女高中生戒守在这里。
时值七月,天气闷热,绷紧的武装带使她们青春的胸脯更显丰实,让人联想起保尔“无意间”的碰触。
草绿色的钢盔下有一张白皙、娇嫩的脸,眼睛大而亮丽。
重庆姑娘很美……她们手中的五六式冲锋枪令我生羡,因为保尔喜欢玩勃朗宁。
她们的任务是堵截散逃的“反派”队员。
对方没有统一制服,怎么知道那个提驳壳枪,行色匆匆的青年人是“反派”还是自己人
唯一的辨识是同窗的记忆。
提驳壳枪的青年男子被揪回来,驳壳枪被卸掉,少女们手中的冲锋枪托在白皙柔嫩的手臂挥动中轮番砸在他的头上,脸上、胸脯上……他不是自己人,但是同窗。
我第一次见到了单纯的血。
惊颤之余,突然想起了冬妮娅;她为什么要救保尔
她理解革命吗
她为了革命才救保尔吗
保尔明明说过,冬妮娅不是自己人。
革命与爱欲有一个含糊莫辨的共同点:献身。
献身是偶在个体身体的位置转移。
“这一个”身体自我被自己投入所欲求的时空位置,重新安顿在纯属自己切身的时间中颠簸的自身。
革命与爱欲的献身所向的时空位置,当然不同;但革命与爱欲都要求嘲笑怯懦的献身,这往往让人分辨不清两者的差异。
没有无缘无故的献身,献身总是有理由,这种理由可称为“这一个”身体自我的性情气质。
革命与爱欲的献身差异在于性情气质。
保尔献身革命,冬妮娅献身爱情。
身体位置的投入方向不同,本来酝酿着一场悲剧性的紧张,但因保尔的出逃而轻易地了结。
保尔走进革命的队伍,留下一连串光辉的业绩;冬妮娅被革命意识轻薄一番后抛入连历史角落都不是的地方。
保尔不是一开始就打算献身革命,献身革命要经历许多磨炼。
奥氏喜欢用情欲的磨炼来证明保尔对献身革命的忠贞,但有一次,他用情欲的磨炼来证明保尔对献身情爱的忠贞。
在囚室中,保尔面对一位将被蹂躏的少女的献身。
同情和情欲都在为保尔接受“这一个”少女的献身提供理由,而且,情欲的力量显然更大,因为,保尔感到自己需要自制的力量,同情显然不需要这样的自制力。
事实上,被赫丽丝金娜的“热烈而且丰满”的芳唇激起的情欲,抹去了身陷囚室的保尔“眼前所有的苦痛”,少女的身体和“泪水浸湿的双颊”使保尔感到情不自禁,“实在难于逃避”。
是冬妮娅,是她“那对美丽的、可爱的眼睛”使保尔找到在自制的力量,不仅抑制住情欲,也抑制住同情。
这里根本就没有某种性道德原则的束缚,仅仅因为他心中有“这一个”冬妮娅。
保尔的“这一个”身体自我的爱欲只趋向于另一位“这一个”身体自我,她是不可置换的。
革命意识使保尔的情欲力量改变了方向。
与冬妮娅临别前的情语被革命意识变成瑟瑟发抖的、应当嘲笑的东西。
革命意识的觉醒意味着,“我”的身体自我的情欲必须从属于革命,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革命中比有那么充沛的身体自我的原生性强力。
“九?五命令”下达,所有武斗革命团体在领袖的指示下交出各种火器。
大街上热闹非凡,“保派”武斗队正举行盛大的交枪典礼。
典礼实际是炫耀各种武器;解放牌卡车拖着四管高射炮,载着全副武装的战斗队,在市区徐徐兜圈。
我被一卡车战斗队员吸引住了:二十个与冬妮娅一般大的少女端坐卡车上,个个怀抱一挺轻机枪,头戴草绿色钢盔,车上还趴着一位女高中生,握着架在车头上的重机枪,眉头紧锁--特别漂亮的剑眉,凝视前方。
少女的满体皆春与手中钢枪的威武煞人真的交相辉映。
傍晚,中学举行牺牲烈士的葬礼。
第一个仪式是展示烈士遗体,目的不是为了表现烈士的伟大,而是表明“反派”的反革命意识的残忍。
天气仍然闷热,尸体裸露部份很多,大部份尸体已经变成深灰色,有些部位流出灰黑的液体弥散着令人窒息的腐气;守护死者的战友捂着洒满香水的口罩,不时用手中干树枝驱散苍蝇。
一个少年男子的尸体。
他身上只有一条裤衩,,太阳穴上被插入一根拇指粗的钢钎,眼睛睁得很大,象在问着什么,眼球上翻,留下很多眼白。
草坪上躺卧着一具女高中生的尸体,上身盖着一截草席,裸露着的腰部表明她上身是赤裸的;下身有一条草绿色军服短裤。
看来她刚“牺牲”不久,尸体尚有人色。
她的头歪向一边,左边面颊浸在草丛中,惨白的双唇紧贴着湿热的中国土地本来,她的芳唇应当期待着接纳夹杂着羞怯的初恋之吻;没有钢盔,一头飘散开来的秀发与披满黄昏露珠草叶织在一起,带点革命小说中描写的“诗意”。
她的眉头紧锁,那是饮弹后停止呼吸前忍受象摔了一跤似的疼痛的表情……一颗(几颗
)子弹射穿她的颈项
射穿胸脯
射穿心脏
我感到失去了某种生命的维系,那把“这一个”身体自我与“另一个”身体自我连在一起的感觉。
我想到趴在车头上紧握重机枪的女高中生的眉头,又突然想到冬妮娅,要是她也献身革命,跟保尔一同上了那列火车……武斗团的赵团长向围观的人群发表情绪高昂的演说。
“为了……(当然不是为了这些死尸的年轻)誓死血战到底
”然后从腰间别着的三支手枪中拔出一支左轮枪,对着天空,他的战友们跟着举起枪。
葬礼在令人心惊肉跳的鸣天枪声中结束。
革命的献身与爱欲的献身不同,前者要求个体服从革命的总体性目的,使革命得以实现,爱欲的献身则只是萦绕、巩固个体身位。
:“这一个”爱上了“另一个”的献身,是偶在个体的爱欲的目的本身,它萦系在个体的有限偶在身上;革命不是献身革命的目的本身,它要服从于一个二次目的,用奥氏令人心血上涌的话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解放全人类而斗争。
”斗争是革命,“解放全人类”是这种革命的二次(终极)谜底。
为了这个目的,个体必须与自己的有限偶在诀别,通过献身革命而献身到全人类的无限恒在中去。
在无限恒在中有偶在个体的终极性生存理由,弃绝无限的全人类,有限偶在的个体身位据说就丧失了活着的理由。
无限恒在与有限偶在之间的关系,从来就是紧张的,克尔凯戈尔吟哦道:“弃绝无限是一则古老传说中所提到的那件衬衫。
那丝线是和着泪水织就、和着泪水漂白的,那衬衫是和着泪水缝成的。
”“反”革命的小说《日瓦戈医生》表达的正是这种“弃绝无限”,所以,它充满了为了无限的革命中惊恐得发抖的泪水。
在基督临世之前,世界上的种种宗教已经星罗棋布,迄今仍在不断衍生;无论哪一种宗教,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寂静的还是迷狂的,目的不外乎要把个体的有限偶在身体挪到无限中去,尽管这无限的蕴含千差万别。
有神明,有大全,有梵天,有天堂,有净土,有人民。
但革命的无限恒在使魂萦受灾的个体爱欲丧失了自在的理由;弃绝革命就意味着个体偶在的“我”不在了。
在诸多革命中,许许多多“这一个”年轻身体的腐臭不足以让人惊怵,陈示许许多多的“这一个”青春尸体,不过为了革命的教育目的:这是个体为认同“人民”必须支付的代价。
保尔与冬妮娅分手时说,“有许多优秀的少女”和他们“一道进行残酷的斗争”,“忍受着一切的困苦”。
他要冬妮娅加入残酷的斗争,象他的政治辅导员丽达一样,懂得何时拔出手枪。
武斗过后,在军事管制下,中学生们继续进行对个体偶在的灵与肉的革命,到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那时,我已经过了中学战斗年龄,广阔天地令我神往。
下乡插队的小火轮沿长江而下,驶向巴东。
在船上,我没有观赏风景,只是又读了一遍《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我发觉自己的阅读速度大有长进,识繁体字的能力也提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