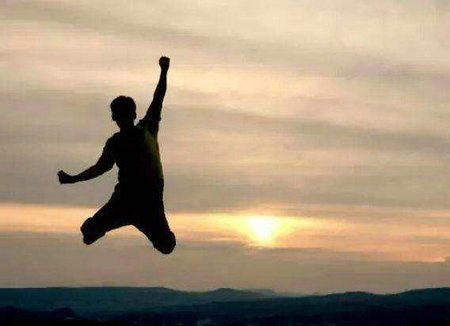朱良志《生命清供》读后感1
这是一本有关中国画的品味之作,作者走到绘画的背后,去揣摩那里深藏的画家心灵隐微,那些曾经感动过画家的幽深生命体验。在作者看来,中国画就是一瓶生命的清供。
作者通过对国画历史上的代表性人物及其画作的介绍,将国画作者的人生经历、境界和追求揭示出来,同时在介绍过程中将自己对人生、对生命的感悟流于笔端,读来颇具启发意义。全书文字优美,意境高远,字里行间表现出作者横溢的才气及深刻的人文情怀。
翻阅这本书:秋江待渡!生命清供!新枫初引!暮鸦宾鸿!好雪片片!山静日长!苇岸泊舟!落花时节!寒潭鹤影!潇湘八景!口如扁担!秋月正孤!乾坤草亭!明河见影!云烟飘渺....这书很美!真想:一口气把他看完,又舍不得一下子看完,细细地品读。心变得空灵起来,那一湾原来如浑浊的水,渐渐澄清,流动着透明。又如轻响从山间升起,我已经不属于这纷繁的世界,远离尘世的喧嚣……摆脱了所有纷芜的杂念,我的灵魂就像一个刚出生的婴儿,纤尘不染。
大涤子曾说“呕血十斗,不如啮雪一团。”一开始,很不理解这话,现在思索着:或者,这就是大师对己绘画探索的总结。如果说呕血十斗,是对我们绘画学习必须付出的辛劳的话,那么,啮血一团,就是平日的养心养性的悟。这本书就是说了这些画者,那些隐藏在作品背后的心灵隐微,那些曾经重重感动过画家的幽深生命体验。他,让我看到了一个个如雪般高明清远的心灵。
作者说他是怀着朝圣的心情写这本书的。而我对这本书更是一种虔诚的膜拜。中国人的宗教观念淡漠,艺术恐怕就是这样的圣殿。打开中国画的世界,到处都是心灵的宁静港湾。一片山水就是一片心灵的境界,一朵水仙也映照出画家的魂灵。夜深人静之时,在这样一个娃声一片月光中,我独坐窗前,静静地看你。抚摩先贤的.画作,聆听他们的心曲。我穿过岁月,和梁楷一道骑着马在深山的小径中沐浴好雪片片;盘坐一片芭蕉,和陈洪绶饮酒读骚,领略老莲的剑胆琴心;我超越时空,我走过了倪云林的寒山瘦水,跟着马远驾着小舟在寒江中独钓;我回到历史,同李翱去拜见药山惟俨,与米芾父子同看云山墨戏……
应该说,好久没有读过这样的好书了,这确实是一本让人容易静下来的书,一本让人静下来,又想开去的活书。我读了很多遍,可我还是说不清楚他到底告诉了我一些什么。犹如一名充满故事和情节的才貌双全的妙女子,你永远看不透她的心事。多想帮云林担水洗桐,多想给八大山人的孤鸟喂食,多想为文徵明摇扇烹茗?落花无言,沈周的《落花图》,唐寅的《落花诗》吟咏着落花,何尝不是在吟咏生命?无人能阻止花开花落,难在看花之心。有了从容之心,自然能让心灵的花永不凋谢。
我们平凡,但可以不庸俗。做人,可以有一点胸怀,追求一点境界。我们可以贫穷,但可以有一点品位、有一点情调。心中有月,处处月!
朱良志《生命清供》读后感2
年初腾出文心出版社的办公室,将我的图书纷纷打了包,一股脑运回家里。无处可放,就都堆在客厅的一隅。
每次回家,坐在沙发上,看着那些打成丁,外面裹了报纸的图书,像明眸善睐的阿拉伯少女头上脸上包了围巾,就忍不住想要揭开那围巾,选一本,抱过来仔细端详一番。
终于忍不住,我想了一个办法,把书们从客厅里移入卧室去。正好也可以打理一番,揭开一些围巾,窥探一下诸位阿拉伯风情的佳丽。
在一个精致的纸盒子里,我抱出了朱良志先生的几本书。安徽教育出版社的《曲院风荷:中国艺术论十讲》、《中国艺术的生命精神》,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美学十五讲》、《生命清供:国画背后的世界》(这是一本印错了的好书,残书)、《中国美学名著导读》。朱先生的书,本本清雅,摩挲封面,翻开目录,每一本都可读、耐读。这几本书,去年从网上买来,却由于一直以来奔波忙碌,从未细读。
选出薄一点的《生命清供》,塞进手提袋里。好打发回太原时漫长的旅途。
12月1日晚,倚在车轮与铁轨轰然交响的2502次车的卧铺车厢里,就着灯光,翻看《好雪片片》一章。朱良志先生以清新而明丽的文笔,细细阐述对于唐代大诗人王维《雪溪图》(传)、五代巨然《雪图》、元人黄公望《九峰雪霁图轴》、南宋人梁楷《雪图》等山水画名作的妙悟。朱先生用的是感性的笔墨,正显出中国艺术的精神。他也有理性的分析,让人豁然开朗。
文徵明曰:“古之高人逸士,往往喜弄笔作山水以自娱,然多写雪景,盖欲假此以寄其岁寒明洁之意耳。”对雪的喜爱,人人而皆然。而艺术巨子的胸襟,更加超然可喜,令人忘怀俗世,意兴遄飞。朱先生讲黄公望《山阴访戴图》,自然牵出了《世说新语》中王徽之雪夜访戴的妙典。我过去读这则风流雅事,往往觉得王徽之“乘兴而来,兴尽而返”,却终于未见好友戴安道,多少让人感到有些遗憾。而看了朱先生的点评,顿时有“一语点醒梦中人”之慨。他说:
这是何等潇洒倜傥的人生格调。他解除的是目的,高扬的是“兴”——生命的悸动,夜、酒、诗、友情,再加上雪,这就是他的兴发感动,他有不可遏止的生命冲动。
读到这里,真如凡世俗子,惶惑中忽闻梵钟,猛然醒豁。人生紧追目的,忽视当下,往往焦躁而多痛苦。而时时品味过程中的兴味,则幸福而愉悦,顿觉生命无限美好,触处花开……
人生,要走向哪里,往往非由人力所能决定,与其紧盯着天上远方那遥远的目标,何如惬意流连于沿途的风景,细细品味人间的种种真滋味?乘兴而动,因兴而息,沉浸在兴味中的人生,才其乐无穷。人生甚短,要用心做好那些与自己心性相合的事。兴冲冲地忙碌,要比索然无味的敷衍,于人生更有意义。
我忽然洞开于魏晋风度的真意,更深一层领会了骆玉明先生对魏晋风度的阐释。保持一种人生的优雅姿态,保持人生的兴味无穷,求其真性情,才不枉此生。
次日清晨醒来,从车窗望外面的山野。寒山瘦石,积雪皑皑,我心里涌起一种无以名状的感动,却不知道这感动从何处而来……
什么是李泽厚宣传的“人生哲理”?它不是以道德理性来处理人与人的关系的仁学,也不是研究心性义理的理学,它不是古代西方探讨人与自然关系的自然哲学,而是一种以生产劳动为基础来推衍政治、经济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社会学。李泽厚对这种理论作了错误的理解并把它运用到文学上,我在《论情境》中曾经作过分析:“他(指李泽厚——作者)按照劳动创造世界这个简单的结论,把人们在劳动改造自然过程中而形成的群体社会性称之为‘人的主体性’,并把人们在社会劳动中的知识积累、因互相交往的需要而产生的语言工具以及情感交流等等称之为‘主体的人性结构’。由于人的社会性是一种理性,所以他说:‘这种主体性的人性结构就是“理性的内化”(智力结构),“理性的凝聚”(意志结构),“理性的积淀”(审美结构)’(《李泽厚哲学美学文选》第168页)李泽厚虽然用了‘内化’、‘凝聚’、‘积淀’来区分知、意、情,但把人们的精神活动都归结为社会理性的本源,李泽厚以社会理性去要求文学实践,很容易地通向了‘文学从属于政治’、‘文学为政治服务’。李泽厚以社会理性去解释文学传统,也就顺理成章地以社会经济这个最活跃的因素去解释一切文艺现象和文艺思想的产生和发展。”⑥ 正是在这个思想基础上,他建构了“作为美的历程的概括巡礼”的“结构方程”:“只要相信人类是发展的,物质文明是发展的,意识形态和精神文化最终(而不是直接)决定于经济生活的前进,那么这其中总有一种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规律,在通过层层曲折渠道起作用。”
李泽厚以“意识形态和精神文化最终决定于经济生活的前进”这条规律来分析文艺问题,虽然也用了“不是直接”的、“层层曲折”的这些有限制性的词语,实际上却是凭着这条规律的权威,夹着对这条规律的误解,肆无忌惮地对文艺现象、文艺作品作出各种各样的错误诠释和任意评价。他的《美的历程》表面看来光昌流利、辩才无碍,内容上却充满了对文艺现象和作品的不合逻辑、不切实际的解读;充满了对文艺思想似是而非的论述和牵强附会的假参证。他把十分复杂的文艺现象简单化了;把非常个性化的文艺作品抽象化了;把曲折变化的文艺发展过程公式化了。我们并不否认“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歌谣文理与世推移”,文学艺术受社会生活影响的道理,但应该看到:经济并非唯一而是作为社会生活诸多因素之一对文学艺术发挥作用的;经济并非直接而是通过许多中介对文艺产生影响的;经济并非在一切条件下都作为决定性因素,而在更多的历史时期是作为次要的非决定因素关系到文艺发展的。归根到底,经济只是文艺发展的外部条件而不是内部根据,而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由它的内部本质因素所决定的。基于这个理由,我们研究文艺现象,分析文艺作品,描述文艺发展过程,更应注意文艺内部的传承关系,作家个人的主观作用,文艺创作的实际经验,以及各种文艺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等等。而不应把一切复杂文艺现象归根于经济就以为是找到了它的“内在逻辑”;更不应把文艺现象削足就履地去适应经济决定一切这样一个“结构方程”。
李泽厚对《春江花月夜》的解读,就是他的经济决定论在文艺作品分析中的具体应用。他首先指出产生《春江花月夜》的初唐时期的“经济发展”及其“在政治、财政、军事上都非常强盛”;“对外是开疆拓土军威四震,国内是相对的安定和统一”;“一方面,南北文化交流融合”,“另一方面,中外贸易交通发达”,归纳起来,“这就是产生文艺上所谓‘盛唐之音’的社会氛围和思想基础”。然后他在这个基础上想象出了那个时期文艺作品的美感特征:“一种丰满的、具有青春活力的热情和想象,渗透在盛唐文艺之中。即使是享乐、颓丧、忧郁、悲伤,也仍然闪烁着青春、自由和欢乐。这就是盛唐艺术,它的典型代表,就是唐诗。”李泽厚按照经济决定文艺的“结构方程”,给《春江花月夜》贴上标签,宣称他从这首诗里发现了一种奇异的美感,它是“夹着感伤、怅惘的激励和欢愉”,“带有某种人生的感伤,然而它仍然是那样快慰轻扬、光昌流利”。可是无论我们怎样沉浸浓郁、含英咀华,也不能从这首诗里品味到这种有些怪怪的美感。张若虚这首名诗从开始到结束,都是借春来春去、江涨江落、花开花谢、月盈月亏、夜复转夜的自然变化、环转交错、换景移情,来抒发恼人千古的离愁别绪。人生最苦是别离。这别离却发生在不同时代、不同阶层、不同个性的人们身上。这也就怪不得抒发离情的作品比比皆是:“彼采葛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诗经·王风·采葛》);“还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古诗·涉江采芙蓉》);“难为含愁独不见,更教明月照流黄”(沈佺期《独不见》);“故关衰草遍,离别正堪悲”(卢纶《送李端》);“梧桐树,三更雨,不道离情正苦”(温庭筠《更漏子》);“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范仲淹《苏幕遮》);“离愁万绪,闻岸草,切切蛩吟如纤”(柳永《倾杯》);“一池萍碎。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苏轼《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王实甫《西厢记》)……在古今文学作品里,离别引起的感情是愁、是恨、是苦、是悲、是相思、是惆怅、是眼泪、是摧人心肝、是断人愁肠,却从未读到像李泽厚所说的那种感伤带着激励、怅惘伴着欢愉,人生感伤与快慰轻扬混在一起的奇异美感。李泽厚说《春江花月夜》表现了这样的美感,完全是他按照唐初经济发达必然出现奋发上扬的审美意识这个“结构方程”演绎出来的,是他悍然不顾这首纯是离歌的诗的内容而把这种“奇异”的美感强加于它的。
君不见,以专注文艺外部关系来代替文艺内部规律的文学史;以哲学、社会学为内容来取代文艺美创造经验总结的美学史;以经济、政治为标准来衡量作家作品的文艺评论;以西方文艺思想来规范、诠释中国文艺的比较文学,汇成一股潮流出现在神州大地。这股崇尚西方的文艺思潮,由20世纪初期的中国留学生开其端绪,由30年代的经济决定论者集其大成,由西方现代派学者继其余响,至今犹是余波荡漾不息。在这种西方思潮影响下,独具特点而极其丰富的中国文学思想得不到科学的总结;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文艺传统得不到继承和发扬;在三千年文学史中占有主流地位的中国抒情文学竟然屈从于反映社会生活这个独一无二的标准而迷失了自己的方向;拥有《牡丹亭》、《红楼梦》这样抒情与叙事相结合传统的中国戏剧、小说,因为趋赶西方现代潮流而陷于邯郸学步失其故步。所有这一切又造成了中国文艺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患上了失语症,丧失了平等对话权。这是中国文艺研究者无法避免而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
处在世纪的转换点上,中国美学新的理论建构与深化前景究竟何在?显然,在这个问题上,人们的各种疑问总是同过去一个世纪里美学在中国的存在状况联系在一起的。
自从20世纪初中国美学步入自己的现代思想建构行程以来,各种美学问题的提出与探究,几乎总是先在地同中国人在社会剧变、国家困厄面前所产生的民族性生存焦虑相纠缠。现代民族国家的振兴期待,社会文化统一体系的重建愿望,民众自觉意识的大声呼唤,大众生活幸福的规划设计……所有这一切,都非常明确地流露在20世纪中国美学种种具体而微的理论思考中;现代中国美学家们竭力想要借助美学的精神能量,严格而理性地框范、引导甚至建构现代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新的生命改造活动与生活希望。所以,尽管20世纪中国美学发展中一直存在着某种功利主义与超功利主义的冲突和矛盾,但深入分析,我们却能看到,不管是持守激进人生改造意志的美学主张,还是保持了相对静观内省立场的各种美学理想,它们实质上都持守了一个最基本的文化立足点,即以“审美”作为人生理想的生命活动,以“审美化/艺术化”为社会进步和文化建设的最后归宿,因而美学上功利主义与超功利主义的分化最终不仅没有集结成大规模的理论对抗,相反却出现了两种美学立场长期并存,共同作为20世纪中国美学基本理论发展路线的局面。如果说,功利主义美学观着重把“美”和“艺术”具体落在了人生行动的崇高性实践方面,那么,超功利主义的美学理想则重点突出了“美”、“艺术”的社会和谐功能。这样,无论过去一百年里中国美学表现了怎样的理论分化,但从根子上说,主宰20世纪中国美学方向的,始终是一种“审美救世主义”的理想情怀。现代中国美学力图把对于社会人生问题的认识要求与实践改造,当作具有充足理由律的美学本体论,以此来实现现实生活与人生经验的精神疗治——美学家往往十分乐于充当这样的“社会精神医生”。
这里,我们便可以发现,如果把20世纪视为中国美学开始自身现代建构尝试的起步期,那么,这期间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就是:当理论内部的“救世情结”和学术追求上的“社会/人生改造冲动”从外部方面强烈制约了美学的内部建构努力,美学在20世纪中国便呈现了一种特定的“社会学症候”——面对强大而急迫的外部社会压力,理论建构本身的内在逻辑反而失去了它的现实合法性;对于“审美”、“艺术”的强调,成为特定历史、社会的集体意志表现,而作为个体存在的“人”和作为个体自由意识的选择与行动,则因此消失在美学对于“社会”这一集体利益的原则性肯定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20世纪中国美学的现代理论建构,实际从一开始就非常鲜明地指向了“社会本体”的确立方向,成为一种坚定地站在社会群体意志之上的美学追求:它把社会改造的目的、人群关系的改善以及人生幸福的不懈奋斗等社会性的价值满足当作为美学唯一合法的现代性根据。
也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20世纪中国美学的一个最大缺失:在社会实践意志、集体理性的高度扩张过程中,美学一方面表达了社会现代性的外部实践需要,另一方面却忽视了审美现代性问题的内在理论建构意义。因为毫无疑问,对于20世纪中国社会来说,社会现代性实践所要求的,是群体的社会自觉、统一而不是个体的生命自立、自由,是社会规范性而不是个体选择性,因而,追求社会现代性之实践满足的美学所集中体现的,便只能是那种超个人的社会意志、超感性的集体理性实践。而与此不同的是,审美现代性的核心却在于寻找社会本体、集体理性的超越前景,寻找并确立个体存在、感性活动的本体地位。因此,20世纪中国美学之现代建构所缺失的,根本上也就是对于个体存在及其生命价值的理论关注。
有鉴于这种历史的理论情状,中国美学倘欲在新的世纪里继续自己的现代理论建构追求,就必须在注意自身历史特点的同时,清醒地看到社会现代性追求在美学目标体系上的局限性,避免在对“社会本体”的确认中淹没掉“个人本体”的存在意义。从健全现代美学建构的整体要求出发,新世纪的中国美学研究应当在自身内部充分肯定审美现代性问题的理论重要性,重新认识超越一般社会规定性和集体意志之上的个体存在价值。换句话说,审美现代性问题之所以成为新世纪中国美学的重要探讨对象,既是一种学术史反省的结果,更是美学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
围绕审美现代性问题,中国美学研究需要思考的主要有:
第一,审美现代性问题的症结及其理论展开结构。这一方面,我们主要应着眼于个体存在的本体确定性及其结构规定,并在这一结构规定上展开审美现代性问题的理论阐释。在这里,我们首先将遇到的最大难题,就是如何从美学层面上理解个体、感性与社会、理性的现代冲突,如何把握“个人本体”与“社会本体”的理论关系?由于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美学始终把“社会”视为一个巨大现实而绝对化了,个体存在与社会利益之间的关系常常被设定为某种无法调和的存在,张扬个体及其感性满足被当作为对社会改造实践、集体理性规范的“反动”而遭到绝对排斥。在这种情况下,强调以个体及其存在价值作为现代美学建构的思考中心,便需要对其中所涉及的`诸多关系作出新的理解与确认,才能使美学之于审美现代性问题的考辨真正获得自己的理论合法性。
第二,“个人本体”的美学内涵及其现代意义。必须指出,所谓“个人本体”应在一种价值概念范围里被理解,而不是一个具有明确的意识形态属性的社会学或伦理学概念;“个人”首先不是被视为理性的生存,而是一种基于个体心理活动之上的感性存在。这样,强调“个人本体”,意味着中国美学将在突破一般理性主义藩篱的前提下,更加充分地关心个人、个人生存目的以及个人的心理建设,而不是以社会利益消解人的需要、以集体意志消解个人想象、以理性消解感性。事实上,美学原本就是一种形成并确立在个人主体活动基础上的思想体系,离开对“个人本体”的确证,美学的实际思想前提也就被取消了。所以,强调“个人本体”,根本上是要重新确认美学作为一种人文思想体系的学科建构本位,让美学真正站在“人”的立场上。当然,对于我们来说,审美现代性问题的关键主要还在于怎样理解这种“个人本体”的现代内涵?在这一点上,需要解决的理论困难主要是:首先,在现代文化语境中,“个人本体”的现实规定是什么?这种现实规定又是如何在美学层面上具体体现出来的?其次,如果说,对于“个人本体”的确定,意味着对于个人的选择自由、行动自由、感受自由的肯定,那么,这种“自由”的价值目标较之历史的存在形态又有什么具体差异?换句话说,在体现和维护个人生存的基本目标上,“现代个人”的特殊性在什么地方?这样的特殊性在美学系统中将如何获得自己的合法性?再次,由于现代社会本身的结构性转换所决定,传统美学对于统一、完整和完善的理性功能要求逐渐被充分感性的个人动机所消解,其影响到美学的现代建构,必然提出如何理解感性活动、感性需要的现代特性及其意义,以及在现代审美和艺术活动中如何有效把握感性与理性的矛盾关系等问题。对此,美学在自身的现代理论建构中必须予以深入的探讨。
第三,审美现代性与社会现代性之间的现实关联。在当代社会现实中,现代性建构作为一个持续性过程,不仅关系着社会实践的历史及其文化现实,而且关系着人对于自身存在价值的自主表达意愿和自由表达过程,关系着个人在一定历史维度上对于自我生命形象的确认方式。所以,社会现代性的建构不仅涉及个人在历史中的存在和价值形式,同时也必然涉及审美、艺术活动对个人存在及其价值形式的形象实现问题。美学在探讨审美和艺术领域的本体确定过程时,理应对此做出有效的回答。这里应该注意的,一是社会现代性建构的理论与实践的具体性质,二是审美现代性追求在社会现代性建构中的位置,三是审美现代性追求的现实合法性维度。
第四,审美现代性研究与美学的民族性理论建构的关系。这个问题本来并不应该成为一个主要的讨论话题,只是由于历史原因,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各种中国美学的“民族性”努力总是相当自觉地把审美和艺术活动与社会进步、审美“人生”的实现与集体意志的完满统一、个人自由与社会解放的关系等,当作一种具有必然性的东西加以高度推崇,并且强调美学理论的“民族性”特征与中国社会固有的实践伦理、集体理性要求之间的一致性。这样,肯定个人及其存在价值、张扬个体自由的审美现代性追求,便不可避免地会同这种美学“民族性”建构思维发生一定的冲突。对于新世纪中国美学来说,能不能真正确立审美现代性研究的合法地位,能不能真正满足美学现代建构的逻辑要求,便需要在审美现代性研究与美学的民族性建构关系问题上进行一定的理论“反正”,厘清其中的关系层次,解除理论顾虑,同时真正从民族思想中发现、发掘和利用“个体本体”的理论资源——在这方面,中国思想系统中其实有许多值得今天重视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