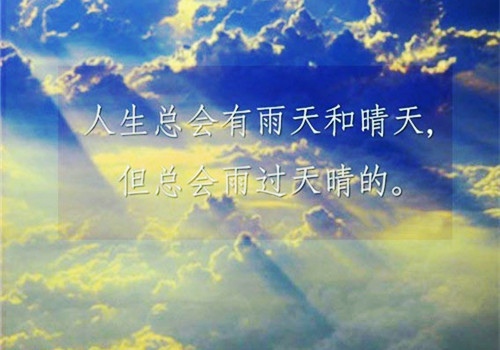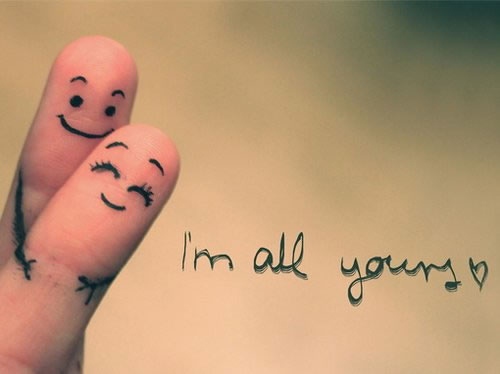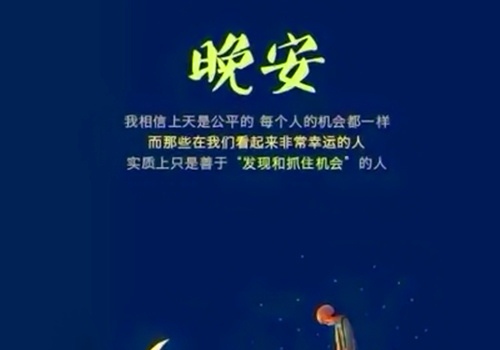白居易诗行路难全诗
太行之路能摧车,人坦途。
巫峡之水能覆舟, 若比人心是安流。
人恶苦不常,好生毛羽恶生疮。
与君结发未五载,岂期牛女为参商。
古称色衰相弃背, 当时美人犹怨悔。
何况如今鸾镜中,妾颜未改君心改。
为君熏衣裳,君闻兰麝不馨香。
为君盛容饰, 君看金翠无颜色。
行路难,难重陈。
人生莫作妇人身, 百年苦乐由他人。
行路难,难于山,险于水。
不独人间夫与妻,近代君臣亦如此。
君不见左纳言, 右纳史,朝承恩,暮赐死。
行路难,不在水,不在山, 只在人情反覆间。
白居易的诗
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
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
古人用诗句如何形容白居易
旧唐书臣观元之制策,白之奏议,极文章之壶奥,尽治乱之根荄。
非徒谣颂之片言,盘盂之小说。
就文观行,居易为优。
放心于自得之场,置器于必安之地。
优游卒岁,不亦贤乎
赞曰:文章新体,建安、永明。
沈、谢既往,元、白挺生。
但留金石,长有茎英。
不习孙吴,焉知用兵
新唐书观居易始以直道奋,在天子前争安危,冀以立功。
虽中被斥,晚益不衰。
当宗闵时,权势震赫,终不附离为进取计,完节自高。
而稹中道徼险得宰相,名望漼然。
呜呼
居易其贤哉
唐才子传公诗以六义为主,不赏艰难。
每成篇,必令其家老妪读之,问解则录。
后人评白诗“如山东父老课农桑,言言皆实”者也。
鸡林国行贾售于其国相,率篇百金,伪者即能辨之。
与元稹极善胶漆,音韵亦同。
天下曰“元白”。
元卒,与刘宾客齐名,曰“刘白”云。
公好神仙,自制飞云履,焚香振足,如拨烟雾,冉冉生云。
初来九江,居庐阜峰下,作草堂,烧丹。
今尚存。
有《白氏长庆集》七十五集,及所撰古今事实,为《六帖》,及述作诗格法,欲自除其病,名《白氏金针集》三卷,并行于世。
历代评价唐代唐宣宗有吊白居易诗:“缀玉联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
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
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
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
”此诗可作为白居易一生的概括。
五代及宋新、旧唐书对于白居易的评价亦有不同。
旧唐书对于白居易的文学成就给予高度的肯定:“昔建安才子,始定霸于曹、刘;永明辞宗,先让功于沈、谢。
元和主盟,微之、乐天而已。
臣观元之制策,白之奏议,极文章之壶奥,尽治乱之根荄。
非徒谣颂之片言,盘盂之小说。
就文观行,居易为优,放心于自得之场,置器于必安之地,优游卒岁,不亦贤乎。
”新唐书描述白居易“于文章精切,然最工诗。
”又说:“居易在元和、长庆时,与元稹俱有名,最长于诗,它文未能称是也。
”然而新唐书对白居易的人品则给予极高的肯定:“观居易始以直道奋,在天子前争安危,冀以立功,虽中被斥,晚益不衰。
当宗闵时,权势震赫,终不附离为进取计,完节自高。
而稹中道徼险得宰相,名望漼然。
鸣呼,居易其贤哉
”这种评价的变迁可能与宋代古文运动的兴起有密切的关系。
苏轼对白居易的评价也有不一致处。
苏轼曾提出“元轻白俗”的说法,对元白的诗风颇有微词。
然而后来却常以白居易自比,例如“定似香山老居士,世缘终浅道根深。
”又如“予去杭十六年,而复来留二年而去。
平生自觉出处老少粗似乐天,虽才名相远,而安分寡求亦庶几焉。
”苏轼对白居易的诗作,也有“白公晚年诗极高妙。
”的评语。
辽金元三代元好问:“并州未是风流域,五百年中一乐天。
”在《论诗三十首》“一语天然万古新”句下,元好问自注:“陶渊明,晋之白乐天。
”明清袁宗道以“白苏斋”为斋名,并有《咏怀效白》的诗作清代主张性灵说的袁枚亦给予白居易极高的评价。
清乾隆皇帝敕编的《唐宋诗醇》对白居易的诗文与为人均给予极高的评价,认为白居易“实具经世之才”,并认为官员应以白居易的诗“救烦无若静,补拙莫如勤”作为座右铭。
近现代胡适赞扬以白居易与元稹为领袖的文学革新运动,认为可以达到以诗歌造成舆论,而有助于改善政治。
因为陈独秀与胡适提倡新文学运动,在提倡白话、不避俗字俗语的风气下,白居易的诗歌因而很受推崇。
包括陈寅恪、刘大杰、钱基博等,都给予白居易极高的评价。
然而钱钟书对白居易的评价则不高。
他国评价白居易的文集在日本受到高度评价。
平安时代,菅原道真写汉诗,当时渤海国的人见道真的诗,认为与白居易的诗很像,这评语令道真很高兴,还特别记载下来,引以为荣。
白居易的诗10首
赋得古原草送别 (唐)白居易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
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