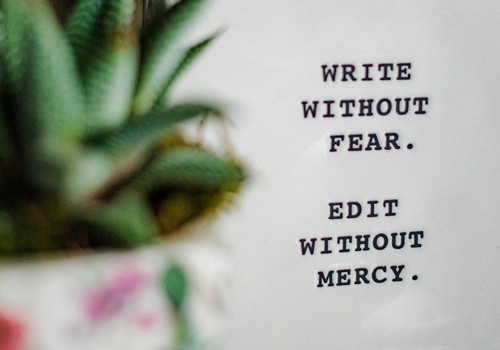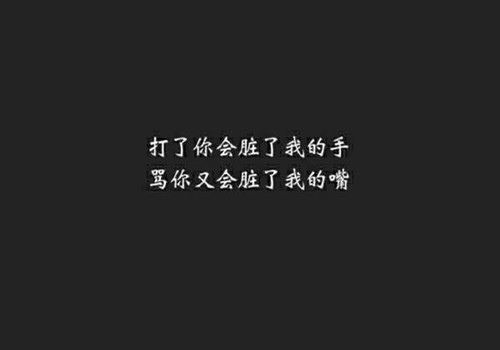1912 ~ 1949 的历史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求助
伦敦被难记 孙中山《伦敦被难记》及其早期「革命」思想等问题 在哈佛燕京图书馆找到孙中山先生的Kidnapped in Lon don(中译名《伦敦被难记》),1897年由伦敦布里斯托尔(Bris tol)书局印行的原刊本。
纸质还硬扎,沿边略有水渍的痕迹。
依稀百年, 算不得古物,还是带来一阵小小的欢喜,虽然百年之下这一阅读的巧遇并没有 产生什么浪漫的革命联想。
以前也一回二回的听到过《伦敦被难记》这本书,也约摸知道裏面讲的是 孙中山早年革命冒险的事迹,但这次想读到原来的英文本,倒并不在於这一段 故事,而是在阅读和写作时碰到了几个注脚,而引起困扰,亦激起了好奇。
首先是我自己的一个注脚,是在一篇讨论中国现代「革命」话语形成过程 的文章裏,后来该文发表在《二十一世纪》上(〈中国现代革命话语之源〉, 1997,4)。
文章主要谈本世纪初「革命」一词如何经过日语的翻译而被 赋予世界革命的普遍意义,从而在现代中国复活,甚至跑进我们的日常生活, 产生了所谓「革命之迷」。
在探讨梁启超如何接受日本翻译的「革命」时,孙 中山跑进了我的视域。
从一些材料来看,他和王韬、梁启超一样,是促使现代 中国革命意识形态形成的最主要的角色之一。
但考虑到孙中山早年的西学背景 ,他或许有直接接触英语的「Revolution」(革命)的可能,因此 产生一系列的问题:中山是通过怎样的具体途径理解和接受英语「革命」的意 义的
这又怎样影响了他的「革命」思想和宣传的
和梁启超所传播的「革命 」思想有何不同
这样从语言与翻译的角度来看这些问题,对於中国现代「革 命」思想史研究,会开启新的思路。
这也是因为见到陈锡祺先生编的《孙中山在港澳与海外活动史迹》(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1986)内中有一封1896年香港政府递呈英国殖民地 大臣张伯伦的公函,报告有关「中国革命分子」在香港的活动情况,并说明港 督已经向孙中山和朱和两人发出驱逐令云云。
这「中国革命分子」数字是编者 的说明,从《史迹》辑入的该函复印件来看,第一页大部分被第二页遮蔽,因 此当时香港政府的英文函件是否称孙中山为「革命分子」还是别的什么,令人 徒增悬想。
这问题一时不能解决,於是就在我的文章里加了一个注。
问题的复杂性在 於,在有关孙中山思想的起源方面,史家的论述汗牛充栋,一般声称在乙未( 1894)之际孙氏即萌发了「革命」思想,但史家所据乃属孙氏的自述,缺 乏史料的实证。
由於中国现代史的撰写与革命意识形态难分难解,这对於探究 「革命」一词的现代旅行带来特别的困难。
如严家伦主编的《国父年谱》,在 1890年谱中写道,孙中山在香港与陈少白等人「朝夕相处,昌言革命」。
(增订版,台湾,1969)这个「革命」即是一种典型的后设性的诠释。
1 894年孙氏在檀香山创立他第一个反满组织「兴中会」,并发表《兴中会章 程》,其中还没有使用「革命」一词,但在民国成立后,撰史者习称之为《兴 中会革命章程》。
后来国民党史家冯自由注意到这个误称问题,专门作文辨证 (《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台湾,1963。
第一编,第九册,页28 6-7)。
在二十年代初,孙中山自撰《革命运动概要》,说有关中国革命的著作大 多是道聼涂说之辞,因此「革命之起源,更无从追述」(同前书,页202) 。
但他自己也没讲清,到底在什么时候他开始使用「革命」作为宣传口号,并 以此命名其党为「革命党」的。
的确,孙氏最初以口传的方式宣传反满主张, 依靠的是秘密会党,也没有留下可靠的记录,这就给「革命之起源」罩上了一 层神秘的迷雾。
因此,我对「革命」话语的溯源的研究,就碰到了历史与「神 话」、诠释与史料之间的裂隙。
关於孙中山与英语「revolution」的关系,我想找《伦敦被难 记》,想从这个1897年出版的孙氏自述裏,是否会发现有关的资料。
这不 仅涉及孙氏的早期革命思想的形成及其西方来源,也有可能探知他接触西方「 革命」思想的具体传媒方式与客观条件。
与此相关的一件事是,孙中山在18 95年广州起义失败,次年遭香港政府驱逐出境,那么我想到,当时的外文报 纸是否报导或者怎样报导和评论的
当然,作这样的词源探索,是处理思想史的一种途径。
或许有人认为,中 国革命是怎么一回事,可以说是妇孺皆知,这样研究的结果意思不大。
其实不 然,试想中国人叫了半个多世纪的「革命」,首先是个语言问题,也是一个历 史现象。
过去历史学家忽视语言和文化、历史再现与日常生活的关系,因此常 常遮蔽了历史的真相。
尤其是「革命」的意识形态在本世纪初形成的过程,引 起我的兴趣。
因为中国「革命」的意识形态是个现代产物,是在东西文化的激 烈冲荡交合的过程中产生的。
这样的研究,在于考实「革命」和「revolution」、日语「か くめい」之间最初交遇的历史形态及其具体境遇。
这与过去的考证传统有一定 的关系,但基於某种对语言与历史、政治权益、文化机制及心理的复杂关系的 认识,在考释过程中尽量揭示「革命」作为一种理论话语的历史形态,包括文 本自身的再现及其与其他文本之间、与社会之间的互文性。
从这个角度看,这 样的「革命」研究就与所谓「正史」有关革命起源的作法有根本不同。
前者是 开放性的,结论产生於追踪、探讨之后,而后者是封闭性的,结论先行,为某 种意识形态所左右。
这些有关孙氏与revolution的质疑,既涉及「革命」话语的现 代形成的一个重要方面,那么这个注脚似乎是一种被压抑的「革命」的呐喊。
对我来说,像一部没有写完的侦探小说,如果找到《伦敦被难记》这个「案卷 」,似乎会构成一个必要的情节,虽然不知结局如何。
而这写作的机遇却与读 过的几本书裏的注脚产生奇妙的联系,他们或提供某个线索,或别生枝节,设 下新的障碍。
阅读的随想能带来喜悦,也包括一些不相干的事。
美国学者保尔柯文(PaulA.Cohen)的《传统与现代之间》(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Ca 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 987)是一部研究王韬的专著,用功颇深。
他在分析王韬的《法国志略》中 有关法国革命的敍述时,说「Revolution」在一八八十年代的中文 裏,还没有确切对应的词,从该书中对法国1789年历史的描述来看,被形 容为「乱」。
柯文在这裏略显出粗心。
他认真对照了《法国志略》和日人冈千 仞《法兰西志》之间的密切联系,但忽略了王著的另一重要来源——冈本监辅 的《万国史记》。
其实在《法国志略》裏,已经数次出现「革命」或「法国革 命」的字眼,只是用的比较晦涩,在敍述波旁王朝复辟时才提到,而在正面描 写巴黎市民的起义时,则称之为「作乱」或「乱民」。
在这些地方,王韬几乎 照抄了《万国史记》。
这个最早从日人历史著作中引进「法国革命」的概念, 对中国现代革命思想有相当的影响,我在别处已经略略谈过(《读书》,19 98,6)。
不过柯文在该段论述之后,加了一个注脚,却显出他的读书之细。
对我来 说,这完全是意外的收获。
他在注中说,「革命」一词原为中国所有,意谓改 朝换代,直到一八九十年代中期,才含有现代的革命意义。
他还指出,对「革 命」的现代使用,日本人要比中国人早一些,并举了两本名著:史扶林(Ha rold Shifffrin)的《孙中山与中国革命之源》和雷文森(J oseph R.Levenson)的《儒家中国及其现代命运》。
数十年来,论述中国革命的西文著作,也可谓浩如烟海。
但所谓「革命」 ,是比喻性的,具一种敍述框架的功能,大多敍述的是自十九世纪后半叶以来 中国政治、社会等方面的变化,很少有人从语言角度注意到我们每天挂在嘴上 的「革命」,到底对於中国革命有什么样的意义。
柯文对「革命」使用时间的 论断虽然不确切,但他在批注裏引证出处,说明自己看法的由来,体现了一种 严谨的学术作风。
当他把史扶林和雷文森的两条相关的材料放在一起,再稍加 引伸,说日人较早使用了现代意义上的「革命」,这就彰显了一个有研究潜力 的问题,他的这一注脚便包含著灼见,哪怕被后来的研究证明是错的。
注明出处,是写学术论文的基本格式。
在美国,对批注的格式要求是很机 制化的,有的教授明确规定他的研究生写论文,一定要根据——比方说——《 芝加哥写作手册》。
一般学术刊物对论文格式各有严格的要求。
我说「机制化 」,即是对注解格式的要求属於整个学院及学术研究机制化的一个有机的环节 。
以出书发文章为例,这是和匿名审稿、书评等制度是连在一起的。
出书时, 出版社寄书给有关方面的专家,请写书评。
有的写,有的不写;写的话,不是 为稿费。
当然有的写得好,有的差。
这样的机制性为的是保证学术质量,从资 本主义性质来看,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保证知识的累积性和个人创造的专利性。
虽然在实际功效上不一定如此,但有「格」可循,终究要好些。
批注不仅仅为的是注明出处。
柯文的这个注脚,是因为有关「革命」使用 问题的想法不便在正文裏展开,於是这批注就像一个小牛奶瓶,将溢出的文思 装起来。
有些学者或善发议论,或喜欢卖弄博学而横生枝节,又不好意思在正 文裏这么做,这样批注就有点像「跳蚤市场」了。
当然也有不少学者懒于或拙 於作注,或有注而不注出处的。
扯得远了,回到使我困惑的「革命」批注。
另一个例子,是在台湾学者朱 浤源《同盟会的革命理论》(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历史研究所,1985) 一书裏读到的。
此书副题为:「《民报》个案研究」。
1905年之际,以孙 中山为首的民族革命主义一派在他们的机关刊物《民报》上发表了大量讨论、 宣传「革命」理论的文章。
朱浤源这本书对於五花八门、纷纭复杂的「革命」 理论条分缕析,作了深入的研究,很有参考价值。
在开场白裏有一段话:「今 天的中国,尚在分裂的状态中。
台湾海峡两岸的执政者或人民,都肯定中国尚 未脱离革命的阶段。
」这类官腔,海峡两岸都差不多,有时在不以「革命」为 主题的著作中也不难见到。
这段话后面加一注:「中共持续发动各式大小革命 ,认为破坏仍不彻底。
唯有经大破坏之后,大建设才较容易。
中华民国的政府 ,秉持孙中山主义,亦肯定『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我读了之后 ,不由得哑然失笑。
这本书在1985年出版,想想曾几何时,风云突变,现 在一般读者,无论海峡两岸,在读这些话的时候,大约不会觉得那么顺耳。
从 这个意义上说,作者这一「宏大话语」幸而未中
然而倒过来想想,如果作者真要大发革命的宏词,尽可在正文裏发挥,实 在也不必忸怩作注的,其中也不必有那种注经式的「微言大义」。
所以作者加 这个注,在作用上是把「宏大话语」缩小,至少显出一种节制。
再看这个注脚 ,意在论证正文裏的革命必要性的论断,而强调的是,继续革命都更像是党和 政府方面的意图,与正文裏的「人民」没有什么干系。
由此对这条批注产生了几分同情。
再想想什么是「革命」
自己这篇文不 文、注不注的,是不必成为革命正史的一条注脚的。
自以为在解构「革命」, 而在「向革命告别」的时代,却斤斤於几个有关「革命」的注脚,岂不像解开 革命的裹脚布
最后一个批注,比较长,因为切入我的论题,也就应该成为正文的。
那是 在陈锡祺先生主编的《孙中山年谱长编》裏。
见1895年11月10日谱: 据冯自由记:舟过神户之际,先生等「登岸购得日本报纸,中有新闻一则,题 曰〈支那革命党首领孙逸仙抵日。
总理语少白曰:『革命二字出於《易经》汤 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一语,日人称吾党为革命党,意义甚佳,吾党以后即 称革命党可也。
』」(《革命逸史》初集1页)又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 亦说:「到了神户就买份日报来看看。
我们那时,虽然不认识日文,看了几个 中国字,也略知梗概。
所以一看,就看见『中国革命党孙逸仙』等字样,赫然 耀在眼前。
我们从前的心理,以为要做皇帝才叫『革命』,我们的行动只算造 反而已。
自从见了这样报纸后,就有『革命党』三字的影像印在脑中了。
」此 事不见於先生本人记述,据安井三吉、陈德仁考查,当时日本报纸亦未见此种 报导。
(北京:中华书局,1991,102页) 限於年谱的体例,往往通过对占有材料的编排、选择和考订而见出史家的 见识。
陈少白的这条材料,在罗家伦编的《国父年谱》裏,被理所当然的编入 1895年谱中,作为正文。
陈锡祺此谱不系于正文而置於批注,表示编者对 这条史料的审慎,也足见在年谱的现代翻版中注脚的妙用。
所谓「此事不见於 先生本人记述」,是编者的按语,也表达了对谱主的尊重。
只是略感不足的是 ,既指出安井三吉、陈德仁对这条史料的「考查」,可见此有关革命原始的史 实已引起学者重视,至少应当将有关他们考查的资料出处注明的。
在探索「革命」语源时,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革命的历史是如此充满激 情和戏剧性,因此有关革命的记忆常常有一种将理想的自我传奇化倾向。
陈少 白这段回忆,尽管时、地、人三者都凿凿有据,恐怕在革命记忆和革命事实之 间有了裂痕。
或者是一种后设性的对自己革命历史的表述;或者是记忆的错位 ,细节上有差错,不一定纯属子虚乌有。
对於孙中山与「革命」的关系,这段 话非常重要,它反映了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接受「革命」话语过程的集体经验。
「革命」话语不是一个单纯的字眼问题,它本身有一个漫长的历史,所谓 「汤武革命」作为儒家政治文化的某种范式,也负载著民族的文化认知方式。
从上世纪未直至今日,「革命」和世界革命接轨以来,其间对抗和亲和关系始 终是紧张的。
据陈少白的说法,「汤武革命」这样富有封建色彩的革命话语已 经在国际环境中重新获得生命,带有某种普遍的正义性,而陈氏那种乐观的口 气,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需要具备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条件。
从理论上说,通过日本报纸的报导而自称「革命党」,就有相当的权威性 。
因为日本报纸代表了某种「公意」,当时的日本在中国人心目中,已成为「 西化」成功的典范。
事实上,自德川时代起,日本学者逐渐完成了对儒家「革 命」话语的改造。
如雷文森所说,日本人把「革命」用作一个比喻,已与儒家 所说的「革命」意义基本上脱离了关系。
尤其在崇尚「文明开化」的明治时期 ,那种在世界历史背景中理解的「革命」,相当於一般意义的「变革」,因此 日人也习称「明治维新革命」。
这和中国人习惯上理解「革命」为改朝换代的 政治暴力不同。
这样说来,当时日本报纸是否会把孙中山的未遂暴动称为「革 命」值得怀疑。
事实上据陈锡祺《长编》,当时的《神户又新日报》(189 5,11,10,可参陈德仁、安井三吉《孙文と神户》,神户,1985, 页34)对孙氏广东暴动的报导,称之为「暴徒巨魁」,根本没有「革命」的 意思。
因此从实践上说,陈少白所说的从「造反」到「革命」的正义感的产生 ,更需要的是集体的参与并产生一定的政治气候。
这两方面的条件,在189 5年孙氏及其同志在日本的情况来看,是不可能具备的。
《长编》所谓「此事不见於先生本人记述」,应当指的是孙中山在192 3年自撰的《革命运动概要》及其它资料,的确,只字未提这件事。
孙中山指 出民国以来,出现无数有关中国革命的著作,「多道聼涂说之辞,鲜能知革命 之事实;而于革命之起源,更无从追述。
」甲午之后孙氏在香港活动,他说, 学者们追述革命起源,「多有本於予之《伦敦被难记》第一章之革命事由。
该 章所述,本甚简略,且于二十余年之前,革命之成否,尚成问题。
而当时虽在 英京,然亦事多忌讳……」的确,我们细看此书,孙中山声称自己主张「和平 改革」(apeaceful reformation)。
确实因为「事多 忌讳」,而不能直言其反满的革命宗旨。
如果我们斤斤於孙中山最初与「革命 」一词的瓜葛,那这一权威版本也难以满足我们的「历史癖」。
如果说因为「事多忌讳」而使用「reformation」,似乎孙氏 心目中已有「revolution」的念头。
有意思的是,《伦敦被难记》 书末附录当时香港《德臣新报》(China Mail)的一篇评论,标题 为The Supposed Chinese Revolutionis t(假定的中国革命者)。
这个英文的revolutionist,我们都 知道意为「革命者」,但在当时不是译为「革命」,而是译为「造反」。
冯自 由在辨证最初的《兴中会章程》时,不仅说原章程裏没有使用「革命」一词。
他还指出,次年孙中山在香港的兴中会章程中沿用了「香港旧译名辞」,而「 英文革命(Revolution)一字,旧译为『造反』,即同此例。
」 《德臣新报》中revolutionist的意义,涉及「revol ution」一词在英语历史中的衍变。
在十七世纪,英语rebel(叛乱 )的意义和revolution之间界限开始模糊,但据雷蒙威廉斯《开键 词》一书,至十九世纪末,revolution的意义与evolutio n(进化)相对,含有暴力颠覆政权或根本改变政治体制之意。
(Raymo nd Williams,Keywords.New York:Oxfo rd University Press,1983,p.273)细看那 篇报导,作者显然在为孙中山辩护,称颂他的人格正直,理想高尚,但文中提 及孙氏的广东暴动为「abortive revolution」(流产的 革命)或「rebellion」(叛乱),可见这「革命」与「叛乱」或「 造反」的意思差不多,由是亦可推断,尽管孙中山已熟悉revolutio n一语,但在他的语汇裏,还是「造反」的意思。
看来他对「革命」的真正接 受,这个翻译过程问题,仍造成认识上的障碍。
读到《伦敦被难记》,对英文世界颇为失望,於是更把注意力放到他在日 本的「革命」之旅。
另一个有关中山早时「革命」文献,是宫崎滔天的《三十 三年之梦》,却也使我疑窦丛生。
书中写到孙中山伦敦被难后,从英国至日本 。
宫崎与孙会见,展开一场访谈:我首先发问道:「我早已听闻你是以中国革 命为志的。
但还不知详情。
我希望能够详细领教你那所谓革命的宗旨,以及方 法手段。
」他徐徐开口说道:「我认为人民自治是政治的极则。
因此,我的政 治主张是共和主义。
但以这一点来说,我认为就有责任从事革命。
……(《三 十三年之梦》,佚名初译,林启彦改译,花城出版社,1981,页122) 据滔天之子宫崎龙介的回忆,当初两人作的是「笔谈」,宫崎不懂汉语, 因此「这样的笔谈问答,是和不完整的英语混在一起谈的,所以难以理解的地 方很多。
」(同前书,页275)而上引的对谈,犹如公共传媒的记者采访, 而所谓「革命的宗旨,以及方法和手段」云云,好象一场新闻发布会。
《三十 三年之梦》出版於1902年,作者追述五年前讲过的话,却无异於历史重构 ,显见他为孙氏鼓吹革命的意图。
从现存少数「笔谈」来看,那种会谈的秘密 性质,那种用语和内容,可以感受到另一种历史的气氛,从中也看不到「革命 」的字眼。
问题的关键仍是孙氏使用「革命」的历史条件。
如章炳麟、康有为 等人已经在戊戌期间谈到「革命」,都持否定态度。
因此通过孙中山由否定「 革命」转向肯定,意味著传统革命话语的内在逻辑出现某种决定性的转变,以 及社会一般恐惧心理的克服。
换言之,当1902年孙中山的反满革命主张能 够产生社会效应时,中国知识界和社会意识——伴随著传统革命话语——似乎 经历了一次「换脑」手术,也即和当时大量「新名词」风靡朝野上下的情况有 关。
这就不得不提到梁启超。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通过日人的翻译,真正接触到西方R evolution的意义,同时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往还,谈论「革命」 。
在这样的中/西、保守/激进、传统/现代的文化冲荡与交汇的熔炉裏,中 国现代「革命」话语应运而生。
1899年改良派在日本的喉舌《清议报》上刊载了欧榘甲〈中国历代革 命说略〉一文。
在改良派营垒裏,欧氏属於激进份子,与孙中山过往密迩。
文 中盛颂孔子和汤武为「革命」始祖,符合孙氏在《革命运动概要》所说的:「 革命之名词,创於孔子,中国历史,汤武之后,革命之事实,已数见不鲜矣
」从历史文本的角度看,这篇文章可视作孙中山「革命源起」之一证,尽管是 间接的。
关於孙中山最初对「革命」一词的接受和使用,我的初步结论和台湾学者 周弘然的说法有相合之处。
他说:「革命排满两个概念结在一起,公开号召, 收大效者,当在光绪二十五年(一八九九)保皇会成立之后。
」(〈国父〈上 李鸿章书〉之时代背景〉,见《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之文献》,页278-9 )虽然这一灼见缺乏证据。
当然我这篇短文只是提出问题,许多细节尚需展开 和深入。
同年年底,仍在《清议报》上,刊出梁启超《汗漫录》,首唱「诗界革命 」和「文界革命」,宣传西方的Revolution之意,这个含有和平改 良意愿的革命,颇有与孙中山的反满革命分途扬镳的意思,但事实上却使反满 革命的意识形态如虎添翼,「革命」一词从此深植于现代中国。
关於梁启超与 「革命」话语的关系,我在〈现代中国革命话语之源〉一文中稍作过讨论,不 妨读作本文的一个注脚。
虎门销烟谈谈自己的感受
中国人民不屈不饶的斗争精神是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不间断的重要原因之一。
压迫和反抗是并存的,鸦片战争是西方资本的贪婪触动了晚清的统治基础,在时代局限的条件下,虎门销烟是值得肯定的,林则徐是民族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