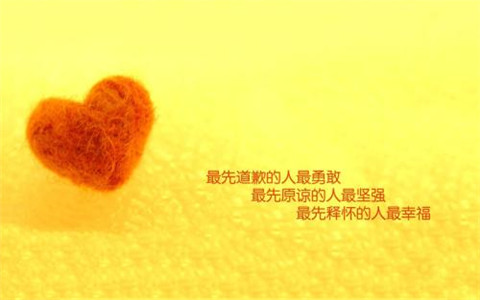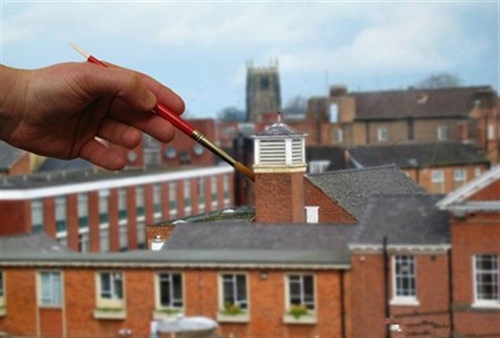昆虫记荒石园阅读感悟50字
昆虫记之《荒石园》读后感:荒石园读完了,看作者法布尔当做宝地的荒石园,这里长着植物,如:矢车菊,犬齿草等。
对于膜翅目昆虫们来说是天堂,它们每天忙忙碌碌,建设自己的家园。
因为少了人的足迹,这些动物们踏踏实实跑进园子,占领着各处空间。
黄莺翠鸟和金丝雀也在树上搭起小窝。
5月,池塘成了雨蛙的乐池,它们在池塘欢快的歌唱。
连作者的房间也被占领,这些老朋友新朋友都聚集在这里,有各种“猎手”“建筑工”“技工”“矿工”的蜂类 ,有鸟类。
看到这里,我真想来到这座园子,每天观察这些有趣的昆虫,每天和小鸟在林子里欢快歌唱。
多么有趣的园子,多么可爱的虫子们,我要爱护它们
我的荒石园读后感
四周一片废墟,中间一堵断墙危立,石灰和沙使它巍然不动;这屹立着的断墙正是我对科学真理的热爱。
哦,我的灵巧的膜翅目昆虫啊,这种热爱是不是足以让我名正言顺地对你们的故事在添上几页话呢
我会不会力不从心呢
为什么我自己也把你们抛弃了这么长时间呢
一些朋友为此责备我。
啊,告诉他们,告诉那些既是你们的也是我的朋友们,告诉他们,并不是由于我的遗憾,我的懒散,我的抛弃;我想念你们;我深信节腹泥蜂的窝还会告诉我们动人的秘密,飞蝗泥蜂的捕猎还会给我们带来惊奇的故事。
但是我缺少时间,我在跟不幸的命运做斗争中,孤立无援,被人遗弃。
在高谈阔论之前,必须能够活下去。
请您告诉他们把,它们会原谅我的。
有人指责我使用的语言不庄重,干脆说吧,没有干巴巴的学究气。
他们害怕读起来不令人疲倦的作品,认为它就是没有说出真理,照他们的说法,只有晦涩难懂才是思想深刻。
你们这些带螫针、盔甲上长鞘翅的,不管有多少都来吧,为我辩护,替我说话吧。
你们说说我跟你们是多么亲密无间,我多么耐心地观察你们,我多么耐心地观察你们,多么认真地记录你们的行为。
你们的证词会异口同声地说:是的,我的作品没有充满言之无物的公式,一知半解的瞎扯,而是准确地描述观察到的事实,一点儿不多,一点儿也不少;谁愿意询问你们就去问好了,他们也会得到同样的答复的。
亲爱的昆虫们,如果因为对你们的描述不够令人生厌,所以说服不了这些正直的人,那么就由我来对他们说:“你们是把昆虫开膛破肚,而我是在它们活蹦乱跳时进行研究;你们把昆虫变得既可怖又可怜,而我则使人们喜欢它们;你们在酷刑室和碎尸场里工作,而我是在蔚蓝的天空下,在鸣蝉的歌声中观察;你们用试剂测试蜂房和原生质,而我却研究本能的最高表现;你们探究死亡,而我却探究生命。
那么,我为什么不进一步说明我的想法:野猪搅浑了清泉;博物学于青年人是极好的学科,可由于越分越细,彼此隔绝,如今已令人可厌可嫌。
如果说我是为了企图将来能弄清本能这个热门问题的学者和哲学家们而写,其实我更是为年轻人而写,我希望他们热爱被你们弄得令人憎恶的博物学。
这就是为什么我在极力保持翔实的同时,不采用你们那种科学性的文字,因为这种文字似乎是从休伦人(17世纪北美洲的印第安人——编者注)的语言中借来的。
” …… 法布尔小传 法布尔(Jean-Henri Fabre,1823~1915年),1823年生于法国南部圣雷翁村一户农家,童年在乡间与花草虫鸟一起度过。
由于贫穷,他连中学也无法正常读完,但他坚持自学,一生中先后取得了业士学位、数学学士学位、自然科学学士学位和自然科学博士学位。
1847年,来到阿雅克修中学,在那里遇到了影响了他人生选择的两位学者,他从此打定主意,教学之余潜心研究昆虫。
1857年,他发表了处女作《节腹泥蜂习性观察记》,这篇论文修正了当时的昆虫学祖师列翁·杜福尔的错误观点,由此赢得了法兰西研究院的赞誉,被授予实验生理学奖。
达尔文也给了他很高的赞誉,在《物种起源》中称法布尔为“无与伦比的观察家”。
1879年,《昆虫记》第一卷问世。
1880年,他终于有了一间实验室,一块荒芜不毛但却是矢车菊和膜翅目昆虫钟爱的土地,他风趣地称之为“荒石园”。
在余生的35年中,法布尔就蛰居在荒石园,一边进行观察和实验,一边整理前半生研究昆虫的观察笔记、实验记录、科学札记等资料,完成了《昆虫记》的后九卷。
1915年,92岁的法布尔在他钟爱的昆虫陪伴下,静静地长眠于荒石园
昆虫记荒石园主要内容
荒石园读完了,看作者法布尔当做宝地的荒石园,这里长着植物,如:矢车菊,犬齿草等。
对于膜翅目昆虫们来说是天堂,它们每天忙忙碌碌,建设自己的家园。
因为少了人的足迹,这些动物们踏踏实实跑进园子,占领着各处空间。
黄莺翠鸟和金丝雀也在树上搭起小窝。
5月,池塘成了雨蛙的乐池,它们在池塘欢快的歌唱。
连作者的房间也被占领,这些老朋友新朋友都聚集在这里,有各种“猎手”“建筑工”“技工”“矿工”的蜂类 ,有鸟类。
看到这里,我真想来到这座园子,每天观察这些有趣的昆虫,每天和小鸟在林子里欢快歌唱。
多么有趣的园子,多么可爱的虫子们,我要爱护它们
昆虫记中《荒石园》的读后感
而不是《昆虫记》的读后感。
600字。
我的荒石园这是我长来的一个梦想:一地。
一片面积不大、整日被阳晒、长满荒草的空地本就是一块被人们抛弃的荒地,因为上面除了蓝色矢车菊和其他蓟属菊科植物,几乎不能生长农田作物。
然而这里正是昆虫的乐园。
我把它买了下来,四周围上围墙,这样,就不会有人随意进出干扰我的观察活动。
我可以尽情地安排我的观察实验,倾心投入与土蜂和砂泥蜂的交谈。
是的。
这正是我的梦想。
一个我从未奢望能够实现、而今却变作现实的一个梦想。
对一个时时要为生活琐事甚至一日三餐劳心费神的人来说,要想在野外建立一个观察试验室是何其不易
近四十年来我一直怀抱着这个心愿,虽然穷困潦倒,困难重重,但我总算拥有了这么一片令我朝思暮想的私人领地。
尽管条件不甚理想,但这仍然是我不懈奋斗的成果。
但愿我能拥有更多的自由时间与我的小精灵们相处。
看起来是有些迟了,我真担心,我可爱的昆虫精灵们
我很怕手里终于拥有了一个甜美的桃子时,自己却已经没有牙齿来咬动它。
是有一些迟了。
因为那原本开阔敞亮无遮拦的视野,现今已经变得十分局促。
很多东西都已失去,种种际遇使我心力交瘁,我甚至怀疑自己的坚持还有没有必要继续下去。
然而却没有什么东西值得遗憾,就连那已经逝去的二十年的光阴。
虽然身陷废墟当中,但我心中有一堵石墙仍然屹立,那就是我胸中燃烧着的对科学真理的无比的信念。
啊,我亲爱的膜翅科昆虫,我到底有没有资格为你们的故事增添几页恰如其分的描述呢
我能不能做到呢
而我也是的,我为什么把你们遗忘了那么久呢
我的朋友们因此而责怪我。
啊,快去告诉他们吧。
我并不是有意的冷落你们,也不是因为我的懒惰。
我无时无刻不想念着你们,关心着你们,我相信节腹泥蜂的洞穴还有很多引人入胜的秘密有待我们去揭开,也觉得穴蜂的猎食行为还有大量令人惊异的细节等待我们去发现。
然而我必须承认我缺少的恰恰是时间。
在与命运的拼搏中,我已用上了几乎全部的心力。
毕竟在追求真理之前,要先把肚子填饱。
请告诉他们吧,无论在你们这里还是他们那里,我都应该能够得到原谅。
一直以来,还有人指责我的作品语气不当,缺乏严肃性。
说白了,就是没有他们那种自以为是的学究词汇。
他们总觉得如果一篇文章不被弄得故作深沉、刻板无味,就无法表现真理。
如果我按照他们的方式和你们讲话,估计你们马上就会对我敬而远之。
你们这些长着翅膀、带着螯刺、身穿护甲的各科昆虫们,你们都来吧,都来这里为我辩护。
请你们跟他们说说我在观察你们的时候是多么的耐心细致,与你们相处时是多么的和乐融融,记录你们行为的时候是多么的一丝不苟。
你们一定会众口一致地证明我的作品的严谨性和忠于事实,我的表述既没有增加什么,也从不曾妄自减少。
谁愿意去问你们就去问好了,他们都将得到同样的答案。
最后,如果你们觉得自己身单力微,不足以令那些满口经纶的先生们信服,那么就由我就站出来,告诉他们一些他们不能不承认的事项:“你们把昆虫们杀死做各种实验,而我研究的是活的生命体;你们把它们变作苍白可怖的标本,而我却要让人们感到它们的鲜活可爱;你们在解剖室和碎尸间研究,我却在蓝天下边听蝉鸣边观察;你们把细胞和原生质分离做化学实验,我却在它们生命的巅峰研究生物的本能;你们探索死亡,而我探索生命。
我还要说清楚的一点就是:一颗老鼠屎弄坏一锅汤。
博物学原本是年轻人乐于从事的天然学问,然而却被细胞研究的进步分割得面目全非,充满可憎之物。
我究竟是为了哪些人写作
当然,我是为了那些有志于从事该方面研究的人士写作,但更重要的,我是为年轻人而写。
我要把被你们弄得面目全非、令人生厌的博物学重新变得让他们易于接受和喜欢。
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在尽量保持作品的翔实和严谨性的基础上,避免你们的那种令人生厌的科学性文体。
”然而,我现在并不想纠缠这些事。
我要说的是我的计划中被期待已久的这块地。
这一片我终于在一个偏僻的小村庄里找到的空地,我想要把它建成一座昆虫学的观察实验基地。
这片土地被当地人叫做:“阿尔玛斯”,意思是“只长百里香植物的多荒石的贫瘠土地”。
我的这座荒石园几乎没办法耕作,不过如果花费工夫耕耘,还是可以长出东西的,但这样实在不值得。
到了春天,如果碰巧下点雨,这里也会长出一些青草,吸引牧羊人赶来他们的羊群。
我的荒石园里有一些掺着石子的红土,据说曾经被人粗略地耕种过,长过一些葡萄树。
这令我感到几分懊恼,因为这里原来的植物已经被人挖掉,现在已经没有了百里香和其他矮树丛。
而那些植物对我或许更为有用:它们可以为我养育很多昆虫。
所以我不得已又把它们重新种植起来。
现在,这里重新长满了各种杂草。
数量最多的是犬齿草,这是令所有庄稼人深恶痛绝的一种草,极难根绝;数量第二多的是各种矢车菊,尤其是长满了橙黄色花朵的那种,棵棵都披满尖刺和星形戟。
比它们长得都高的是伊利里亚大翅蓟,它那耸然直立的枝干,有时高达六尺,而且末梢还长着大大的粉红球样的花朵和小刺,使得想要采集它们的人不知应从哪里下手。
在它们当中,还有一些穗形的矢车菊,长了好长一排钩子。
假使你不穿上高筒皮靴,就来到有这么多刺的草丛里,你就要因为你的粗心而受到惩罚了。
只要是土壤里还留有足够的水分,这些植物便会毫不吝惜地展示它们蓬勃的生命活力。
但是当干旱的夏季到来,这里就会变成一片荒芜的景象,到处是枯枝败叶,一把火就可以把它们烧个精光。
这就是我四十年来拼命奋斗得来的乐园。
打从它出现在我的计划书中的那一天起,我就把它当作我与昆虫们为伍的伊甸园。
从现实情况来看,我的这个目标将会很完满地得到实现。
我的这个稀奇而又冷清的王国用“伊甸园”这个词来称呼或许并不确切,因为没有人会愿意在这里撒上一把萝卜籽。
然而这里却是无数蜜蜂和黄蜂的乐园。
这里蓬勃生长的蓟和矢车菊把周围的膜翅目昆虫都招来了,我从来没有在其他地方看见过这么多的昆虫。
这一行当的各种成员都以这块地为中心汇聚起来。
这儿有充当猎手的猎蜂,有充当工程师的筑巢蜂,有充当泥水匠的涂泥蜂,还有充当纺织工人的编织蜂,甚至连充当家具制造者的切叶蜂和负责开凿隧道的矿工蜂都来了……总之,各种职能的蜂种全都汇集了。
哦,快看这个是什么
原来是只黄斑蜂。
它正剥下开有黄花的矢车菊的网状叶梗,把它们推集成一个大绒球,准备带回去用它储藏蜜和卵。
那儿还有一群切叶蜂,它们的腹部带着黑的、白的或者红的花粉刷。
它们打算到邻近的小树丛中,把叶子切割成圆形的小片用来包裹它们的蜜和卵。
另外,这一群穿着黑色丝绒衣的家伙是谁
啊,原来它们是砂泥蜂。
它们负责混合水泥与铺制沙石工作,在我的荒石园里很容易在石头上发现它们工作用的工具。
现在可以看到的是几只壁蜂。
一只正把巢藏在空蜗牛壳的旋梯里,另一只正要把它的幼虫安置在干燥的覆盆子的木髓里,第三只则在利用干芦苇的茎秆做它的窝,至于第四只,则直接住进了砂泥蜂留下的空巢里,连租金都用不着付。
大头蜂和长须蜂也来了。
还有毛足蜂,它们的后足长有一双巨大的毛刷,用来采集花粉。
种类繁多的土蜂嗡嗡地飞着,间或还可以发现几只肚子纤细的隧蜂。
然而我决定对这一切小冉过多赘述。
要是我继续说下去,我可能要搬出整个采蜜类昆虫的族谱。
我曾经向一位住在波尔多的昆虫学家请教我捕捉到的各种昆虫的名字,这位大名鼎鼎的人士就是佩雷教授。
他问过我是不是有什么秘诀,以至于能抓到那么多稀有的昆虫。
我的所有昆虫都是从我长着大蓟和矢车菊的乐园里找到的,然而我并不是热忱的摘虫专家。
我更喜欢观察活动着的昆虫们,而不是被大头针钉在盒子里的昆虫标本。
环绕着我的荒石园的围墙建好了,曾经有一段时间,园墙下到处都是泥水匠留下的成堆的石子和细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