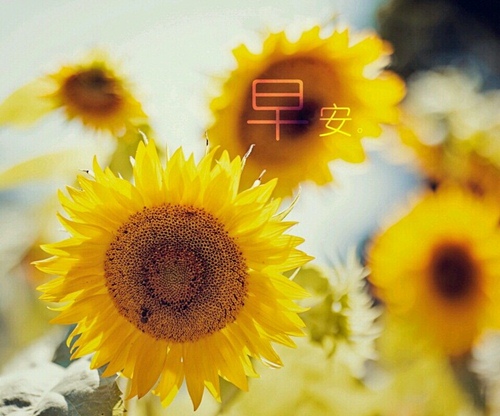1942年发生了很多事,一如斯大林格勒战役,一如甘地绝食,一如宋美龄访美又或是丘吉尔感冒,然而在这片我们深爱的土地上,鲜血染红了土壤,泪水划过了心田。一幕幕的人间惨剧,一场场的悲欢离合,悄然上演在河南。大旱、蝗灾、饥荒、战争、流民、死亡,每一天都有人在绝望中死去,也有人在希望中残喘。那个年代,那抹沉重,陇上心田,久久不散。
一部改编自刘震云先生《温故一九四二》的电影用它的视角诉说着曾经的故事。银屏上掠过一张张饱经沧桑的面孔,熟悉的是炎黄子孙的坚韧,陌生的是茫然空洞甚至绝望的眼神。坐在电影院中的我,呆呆地望着前方,随着故事的展开,心一点点地下沉。泪水含在眼底,迟迟未落,却不是坚强,而是,深知没有资格。没有经历过那一场场劫难的我,虽然做不到剧中人为了生存付出的牺牲与奉献,但是至少我可以不再软弱。
在广袤的平原之上,战火纷飞,哀鸿遍野。在几乎遍及全省的灾区内,每一个村庄,每一个县城,每一座车站,每一条公路都在经历着相似的故事与苦难。剧中的老东家范殿元是一个典型的封建地主,狡猾、市侩。就是这么一个人,也无法对抗这史无前例的灾难,他被迫逃荒,亲眼见证着儿子、儿媳、老伴等亲人的种种死状。随着逃荒日子的渐长,饥饿的阴影笼罩了大地,死亡变成了一种解脱。他甚至在老伴离去后,只是叹息“早死早托生,来生千万别再托生到这个地方。”真正的悲哀莫过于连他自己都失去了悲哀的权利。他的'遭遇是三百万灾民的缩影,他的痛苦是万千痛苦中平凡的一角。那个年代,那抹沉重,已不是言语能够诉说得起的。
剧中人演着属于他们的故事,我难以忘掉他们所有。
我忘不掉那个俏丽的女孩。作为老东家的女儿,她读过书,有知识。一张年轻活力的脸上闪烁着对生活的期盼。我忘不掉在刚开始逃荒的时候,老东家拽她上车,她怀抱着最爱的小黑猫,任性地喊:“要去和同学们一起保卫校园”。她倔强天真,很讨人喜欢。我忘不掉她在嫂子生子后,撕着课本,将小黑煮成一锅猫汤。她麻木地望着天,眼中是哀鸣与疼痛。我忘不掉她在大年三十将自己卖到妓院,换取5斗小米,只为了自己和父亲能够活下去。洛阳城里是过年的欢喜,烟花束束,美丽而妖娆。城外是她年轻生命的沦落,纯贞逝去,只为了生存。
我忘不掉那个年少的妇人。作为长工家的媳妇,她坚韧而善良。她有着中国传统女人的美德,她相夫教子,服侍婆婆。在逃荒的途中,为了丈夫和孩子,努力地找着食物,宁可自己挨饿,也要家人能够活下去。我忘不掉她在老东家面前用着嘲讽的语气说出大家都一样话时的狡黠与对命运的感叹。我忘不掉她在丈夫死后,独自抚养孩子,无论遇到什么都不离不弃的伟大母爱。我忘不掉她年三十改嫁只为了在卖掉自己之后,孩子可以有个去处时浓重的牺牲意味。她随着养牛人的马车渐行渐远,路远方,栓柱带着两个孩子还在原地。若目光可以穿透距离,我想他们的心,他们的爱也是相依相随的。
我忘不掉那两个男人,同为长工的男人。一个是拖家带口的瞎鹿,一个是爱慕着地主家女儿的栓柱。他们有着人性的狭隘与自私,但同时又有着责任与担当。在逃荒途中,他们扛起了重担,带着女人,老人,孩子,开始着新的征程。我忘不掉瞎鹿为了给家人驴肉,死在沸腾的开水之中的惨烈。我忘不掉栓柱为了养女的玩具不落入日本人之手,而被屠刀穿心而过时染透了雪的血,红白分明。
我忘不掉剧中的那些人,那些努力活着,为了活着而闪烁出人性光辉的人。在那个年代,那个沉重的年代,他们用爱,用坚强为我们撑起了一片天空。围绕着老东家与两个长工家庭展开的故事,落幕在一片桃花绽放背景之下。桃花开了,春天到了,我忍不住地想,会不会给豫中平原带来新的生机与活力。哭声、泪水沾染了每一个人的心,明明是见面不相识的路人,却通过一部相同的影片,心中涌起同一片感动。我不知道该怎么描述心中那缕不是滋味的情思,谨以此文镌刻下我对爱、对人性的尊重,以及对那个年代,那抹沉重的沉思。
那是一个为了生存而不顾一切的年代。 那是一个一条人命值两块饼干的年代。 那是一个人尸只能为狼狗所食的年代。 一九四二。一个可怕而又可悲的年代。——题记 一九四二年,河南省发生大旱灾。灾民们纷纷离家逃荒。因为日本的入侵,救济的缺失,这一场灾难,夺走了河南三百万人的生命。 “与此同时,世界上还发生着这些大事:斯大林格勒战役、甘地绝食、宋美龄访美和丘吉尔感冒。”这是电影中的独白,现在读来觉得颇为讽刺。
在那个时代,与那些“国际时事”相比,死三百万人算什么?更何况,这三百万人不是打仗的士兵,只是普通的平民百姓而已。腐败的政府官员都尽可能远离灾区,将兵力撤出河南,蒋介石忙于战争的.前线,决定甩开河南这个“包袱”,而日本侵略者,只因灾民中混有军队士兵,便驾驶轰炸机进行大规模的轰炸。黑烟滚滚,沙石四溅。在这个战火四起的年代,灾民们无处可逃。他们只能在心里怀着一点渺茫的希望,在那不知通往生还是死的无尽道路上不断前行。每天都会有无数人倒在逃荒的道路上,然而又有谁去关心呢?当活着已经成了一种奢望,当食物已经变成衡量生命价值的唯一计量单位,在日军轰炸机的阴影下,所有人都自身难保。人尸为狼狗所食的惨烈可怖的情景,见证了那个时代人命的卑微和人性的泯灭。
然而,我们庆幸,在那个时代,总还有那么几个闪光的片段能深深地感动我们。花枝,一个普通平凡的逃荒者,一个母亲,她坚强、现实,把孩子看得比任何人任何事都重要。在逃荒的路途中,她凭借自己护犊的本能,一路为自己和孩子的生存而不惜一切代价地坚持。白修德,一个美国的记者,作为“局外人”,他大可不必卷入这场灾难之中,然而他有作为人的本性的善良和作为记者的责任感。他随着灾民们历经了种种苦难,突破重重阻碍,将河南大旱的现实和真像告诉全世界,让河南的灾情得到了重视,获得了救济。
在大灾大难之中,终究还是有那些温暖我们的存在。 《一九四二》是一部讲述那个年代灾难的电影,它既体现了当时人们深深的苦难,又体现了灾难之中那些感动我们的一次次闪光。它讲述的那些故事,在今天,带给了我们最强大的震撼和最深刻的思考。
我关注的不是这部影片,而是背后那段沉重的历史。——题记
“饿死还是当亡国奴”是个伪命题
一九四二年,国民政府抛弃了1000万灾民,让他们自生自灭,把他们视作乱摊子抛给了日本人。在国民政府的眼中,几百万灾民的生计在抗战大业面前几乎不值一提,就像二十年之后几千万人的生存在国家建设的“大仁政”里也不值一提一样。抽象的国家宏大的需要压倒了具体国民的生死存亡。
“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经由程朱理学所树立的传统道德观在国家层面就成了“宁死不做亡国奴”的道德律令。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的那段话堪为代表:“老百姓死了,土地还是中国人的;可是如果当兵的饿死了,日本人就会接管这个国家”。于是,我们看到,旱灾蝗灾并起之下,军粮照征不误;灾民的生死小业让位于抗战的生死大业。
美国记者白修德看不懂。没有经历过极权社会的美国人,政府权力受到限制的美国人,享受一流政治文明的美国人,当然看不懂。他们不懂“是饿死还是做亡国奴”的二分逻辑,也不懂为何一个政府能对几千万人流离失所置之不理。在他们看来,饿死和亡国奴并不是绝然对立的,任何战争最终为的都是一个个具体的国民的生存和尊严。民都没了,国又何在?
国民政府很快就吃到苦果。日军进攻河南,发放军粮,收拢民心,国军一败涂地。其间,甚至发生豫西山地民众截击国军缴械这些让后人不敢正视的历史。有多少民众“投靠”了日军我们不得而知,有多少是土匪和游击队趁乱抢劫滋事我们也不得而知。但让一个个吃完了观音土离死亡只有一线之隔的民众,担负起“不当亡国奴”的民族大任,不觉得担子太重了一些吗?
是谁把灾民推给了敌人,是谁让灾民只能做出这样的选择?政府抛弃了灾民,日军残忍,败军如匪,火上加油,反过来抢劫手无缚鸡之力的灾民,反抗日军的不正义被视为理所当然,这种来自自己人的不正义,难道就只能默默忍受吗?中国人不能被外人奴役,难道就活该被自己人奴役吗?“汉奸论”可以休矣。
“民族劣根性”论也可以休矣
冯小刚避免陷入国族的宏大叙事里,也没有一厢情愿地塑造一个有气节的底层中国人。唯一死在日本刺刀之下的,为的是不可磨灭的亲情和记忆,而不是所谓的民族或国家。他深知在这种极端情境中的选择是没有选择,所以不可能苛求饿的奄奄一息的灾民按照社会的.想象“气节”一番。这是冯小刚的进步之处。
这部影片现实得残酷,残酷得却不彻底。那段沉重的苦难让人备感压抑,而灾难中真实的人性则让人更加绝望。“饿殍遍野”、“赤地千里”是文人政客的含糊说辞。人命贱如草,生无尊严死无尊严。野菜、树皮、观音土,凡是能撑满肚皮的都成了口中物;荒野中堆满尸体,任野狗撕咬,路过的人在饥饿的威胁之下早已麻木不仁;人命成为交易,卖妻易子,只为几升小米;让这种灰暗的色调蒙上一层黑色的残酷的,是人吃人,至此,人已经失去了人之为人的意识。先是卑微的苟活,再是沦为野兽般的苟活,活着,成了唯一的本能。
所有道德溃败的社会无不如此,这与所谓的民族劣根性毫无关系,跟所谓的地域更是八竿子打不着。从这部影片中看到民族劣根性的人不仅失之对具体情境的理解和同情,更是深受意识形态教育流毒之害。有的社会发生大饥荒,却没有出现食人的极端场景,不是因为他们的人格更为高尚,而是因为有政府、宗教组织和社会组织的接济使他们不至于沦为目露凶光、只知果腹的野兽。
而在一个不民主的社会,不仅政府没有动力去解决饥荒,各种社会组织和宗教组织也没有多大生存空间。印度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早已解剖出大饥荒背后的机理,饥荒的背后是权利剥夺,“从未有一个重大饥荒在民主国家发生,不管它是多么贫困……如果政府致力于防止饥荒的话,饥荒是极其容易防止的”,这在二十年后那场更大的灾难里表现得更为明显。
从这个角度来看,冯小刚又过于保守。他毕竟希望给绝望的人性留下一份温情的寄托。他知道,人性退居到野蛮只是在特定情形下的极端状况,要防止这种极端状况的不断呈现,我们需要的不是人性的改良,而是政府和社会的变革。
还有多少苦难需要打捞?
一九四二,在抗战八年的宏大叙事中不值一提。正如刘震云说的,那一年,还发生了斯大林格勒战役、甘地绝食、宋美龄访美和丘吉尔的感冒,整个历史上却没有河南的位置。正因为如此,这部影片的上映,某种程度上打捞了那段苦难的历史。
片尾旁白问母亲一九四二年的经历,母亲说,那些闹心的事,我都忘了,你要写它,图个啥呢?
是的,图个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