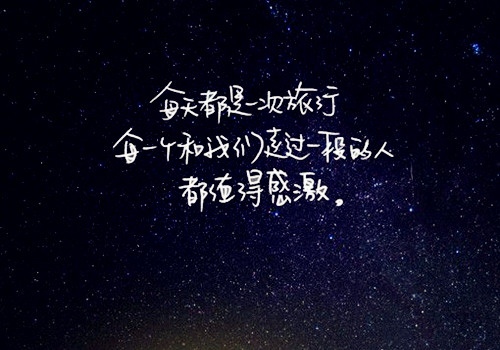求几首苏曼殊的写得好的诗词,只要几首经典的,外带一点赏析
《七绝·本事诗 》春雨楼头尺八箫,何时归看浙江潮
芒鞋破钵无人识,踏过樱花第几桥
三百年来的诗人,最爱是曼殊。
曼殊的作品,最爱是此篇。
此篇于曼殊而言,正如《锦瑟》之于义山——都是压卷之作,都是身世之感,都是言有尽而意无穷。
此诗易解,四句不过是两层意思:前二句写思乡之情,后二句写身世之感。
而故国之思与飘零之感,又浑然交织,全无半点隔断。
起首一句,七个字是三种意象:春雨;楼头;尺八箫。
三种意象,简简单单的陈列,譬如三面墙,围起一个空间,留给人无限的想象。
这三种意象乃是最好的诗料——春雨朦胧,不知是谁家的楼头,吹起了一片箫声。
春雨易让人惆怅,箫声入耳,撩拨起的便是无边的乡愁了。
果不其然,接下来的一句,诗人便说起乡愁。
当时,诗人流落在异国他乡的日本。
尺八是日本的箫,樱花是日本的国花,这两样都是对处境的点明。
日本的箫,在式样上与中国的不尽相同,但一样是作诗的好材料。
箫与笛,在中国诗歌里有着神奇的魔力,它们是乡愁的催生剂。
李白《春夜洛城闻笛》诗云:“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
”李益《夜上受降城闻笛》云:“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
”曼殊写此篇的时候,潜意识里或许受他们的影响。
由箫声而及乡愁,是旧诗常见的模式,但本篇并不因此减色。
玫瑰和玫瑰总是相类,我们并不因此减少一分爱。
关于“春雨”、“尺八箫”和“浙江潮”,尚有几句可以交代。
《燕子龛随笔》(二九则)云:“日本尺八,状类中土洞箫,闻传自金人。
其曲有名《春雨》,阴深凄惘。
余《春雨》绝句云:……”。
相传,日本僧人乞食,常吹尺八箫。
曼殊流宕异国,心境近于乞食之僧。
乞食箫中,最凄惘者,莫过于《春雨》一曲,故曼殊于此曲最是萦怀。
“春雨”固然是曲名,但在篇中,毋宁解作实景。
若于篇中,拘泥“春雨”只是曲名,则神色顿减。
读此诗,当知《春雨》是何种曲子,又不可拘泥其只是曲子。
《断鸿零雁记》(第二十章)云:“……更二日,抵上海。
余即入城,购僧衣一着易之,萧然向武林去,以余素慕圣湖之美,今应顺道酬吾夙愿也。
既至西子湖边,盈眸寂乐,迥绝尘寰。
余复泛瓜皮舟,之茅家埠。
既至,余舍舟,肩挑被席数事,投灵隐寺,即宋之问‘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处也。
”“浙江潮”,即自宋之问诗中来。
《断鸿零雁记》是曼殊带有自传性质的作品,写于日本归来之后。
武林是自古灵秀地,更兼有宋之问佳句添采,曼殊何日能忘之
故自异国归来,第一站便奔此地。
《断鸿零雁记》是记已归之事,《春雨》诗则写未归之思。
总而言之,“浙江潮”于曼殊而言,是梦绕魂牵的埋骨地。
“归看浙江潮”,正是狐死必首丘之意。
而“浙江潮”者,乃名震天下的钱塘潮,是激情和力量的象征。
故“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是壮语,“归看浙江潮”亦是壮语。
全诗之悲,不掩此句之壮;此句之壮,更增全诗之悲。
三四句,则由故国之思转入身世之感。
芒鞋破钵是点明自家的僧人身份。
僧人自然只能是一双草鞋、一个破钵,走千村、求万户地讨生活。
“踏过樱花第几桥
”究竟走过了多少桥梁道路,记不清了。
当然,诗人未必如此凄惨,以至于要化缘乞讨。
这两句只是极力渲染身世的凄楚而已。
“芒鞋破钵”与漫天樱花之间又是何其的不相称
一片绚烂美丽的背景里,走来的便是这样一个地老天荒无人识的行脚僧。
背景的绚烂,将主人公的潦倒反衬得异样的显目。
“踏过樱花第几桥
”又似从小山词中来。
小山《鹧鸪天》词云:“梦魂惯得无拘检,又踏杨花过谢桥。
”“杨花”换成了“樱花”,不变的是梦境和诗情。
几百年前的词人小晏,是个多愁多病多情种;几百年后的诗人苏曼殊,亦复如是。
小晏《临江仙》词又云:“相寻梦里路,飞雨落花中。
”诗人总是敏感于飞雨落花交织成的梦境,该篇首句的“春雨”、末句的“落花”不正透漏出这一信息么
漫天花雨中,走来一个芒鞋破钵的诗僧,正是梦幻一般的意境呀
樱花是极美丽绚烂的一种花,但花期却太短暂,不消半个月的时间,便在风雨中凋零了。
我们震惊于她的绚烂,痛心于她的凋零。
她是美的极至,却不能永驻,一如我们美好的青春、美好的人生。
生命一如飞雨落花的梦境,美丽,然而短暂。
短得触目惊心。
以至于让我们怀疑她的存在,以为她只是梦境,不曾真实。
为我们留下这美丽篇章的诗人,也只在人间度过三十五个春秋,便在贫病之中永远的走了。
曼殊是诗人中的诗人,他用诗篇来抒写生命,亦用生命来诠释诗篇。
诗人的诗篇与生命,相互应证。
记得曾问朋友:樱花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
朋友回答:繁花如梦缀浮生。
真是感动极了。
忽然想起北岛的两句诗:“路啊路,飘满红罂粟。
” 苏曼殊」这个名字,当今年轻一辈当有「天外来客」之感。
不过粤曲爱好者或会对「情僧苏曼殊」为题之戏曲留有记忆,资深影迷也会对五十年代由吴楚帆、紫罗莲演的粤语片「断源零雁记」有多少印象,查此片便是改编来自苏曼的自传式同名小说。
近日兴记了对苏曼殊其人其事其文的热潮,尤其是在中国大陆。
用google.com的搜索引擎以「苏曼殊」search一下,马上便找到几百个网页可供参考,整本的「断鸿零雁记」也可以逐章下载阅读。
苏曼殊出生在清末,算起来是「上上个」世纪的人了,生平简述如下: 苏曼殊,小名三廊,香山(广东中山)人,光绪十年(1884)年生於日本横滨。
父亲是广东茶商,母亲是日本人。
五岁时苏曼殊随父亲回广东。
苏曼殊十二岁时便在广州长寿寺出家,青年时代即学识渊博,灵慧敏捷。
此后,苏曼殊到东京早稻田大学学习,并利用假期到泰国、斯里兰卡等国游历,学成后回国,在日本期间,参加国中国留学生的爱国组织,倾向民主革命。
苏曼殊没有受过长期的正规教育,但能诗文、善绘画、通英、法、日、梵多种文字,和陈独秀、柳亚子等文学泰斗交往甚密。
苏曼殊英年早逝,於1918年病逝於上海,年仅34岁。
上星期一,布市孙灵之女士的府上,几个学术界同好组成了小小的雅集,由恰巧莅临布市讲学的美国俄勒冈大学叶红玉教授带领,讨论苏曼殊这个传奇人物。
参加者有昆大的叶富强和黎志刚两位教授,本报作者陈栋华、孙女士和笔者。
苏曼殊是僧人;佛教要求人摒弃情欲,认为情欲带来人的苦楚,苏曼殊则是世间少有的多情之人,「情僧」的称号,道出了基本矛盾。
他佛理深湛,但一生渴望被爱而不得、嗜吃未能持素而被逐出师门,他追求灵魂的清静却多与俗家人士为友,甚至支持革命运动。
他并非圣贤,受的是凡人的矛盾和痛苦,这才是他可爱的地方。
苏曼殊著作不多,除了几本薄书之外,未有巨著留传,但对当时的年轻人起了很大的影响。
叶红玉教授分析他最近受到大陆读者重视的原因,主要是他追求个性解脱的经历使今日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人感到共鸣。
跟著我分发「断鸿零雁记」的一段给大家研究一下。
这是苏曼殊自传性质甚强的爱情小说,内容描述他与日本少女静子的恋爱悲剧。
当年被老一辈视为大胆至极的作品,但使千万的青年学子著迷,如饥似渴的狂读。
请看以下一段(第十六章节录) ……静子垂头弗余答。
少选,复步近余胸前,双波略注余面。
余在月色溟蒙之下,凝神静观其脸,横云斜月,殊胜端丽。
此际万籁都寂,余心不自镇;既而昂首瞩天,则又乌云弥布,只馀残星数点,空摇明灭。
余不觉自语曰:“吁
此非人间世耶
今夕吾何为置身如是景域中也
” 余言甫竟,似有一缕吴绵,轻温而贴余掌。
视之,则静子一手牵余,一手扶彼枯石而坐。
余即立其膝畔,而不可自脱也。
久之,静子发清响之音,如怨如诉曰:“我且问三郎,先是姨母,曾否有言关白三郎乎
” 余此际神经已无所主,几於膝摇而牙齿相击,垂头不敢睇视,心中默念,情网已张,插翼难飞,此其时矣…… 余言甫发,忽觉静子筋脉跃动,骤松其柔荑之掌。
余如其心固中吾言而愕然耳。
余正思言以他事,忽尔悲风自海面吹来,乃至山岭,出林薄而去。
余方凝伫间,静子四顾惶然,即襟间出一温香罗帕,填余掌中,立而言曰:“三郎,珍重。
此中有绣负梨花笺,吾婴年随阿母挑绣而成,谨以奉赠,聊报今晨杰作。
君其纳之。
此闲花草,宁足云贡
三郎其亦知吾心耳
” 余户闻是语,无以为计。
自念拒之於心良弗忍;受之则睹物思人,宁可力行正照,直证无生耶
余反复思维,不知所可。
静子故欲有言,余陡闻阴风怒号,声振十方,巨浪触石,惨然如破军之声。
静子自将笺帕袭之,谨纳余胸间…… 我用文学的观点发表了几项意见: 首先这段文字的描写方法在当时实在是很大的突破,比诸同期流行的爱情小说如玉梨魂(徐枕亚著)、社会小说如九命奇冤(吴趼人著的梁天来故事)、政治小说如官场现形记(李伯元著),在技巧上不知超越了多少。
这段文字即有心理描写(情),又有环境描写(景),一时写情,一时写景,瞬息间情景交融;景随情移、情由景生。
作者更用第一人的叙事观点,使读者代入了故事的主人翁去感受当时的情景。
此外,他的描写时则用远观法,时则用近观法,当中又名有远近程度之分别。
我们读这一段,有如在看电影中的远景、中景、近景、大特写镜头互相推拉、加上旁述及对白的烘托,令人拍案叫绝
了解背景的话也许可以好理解一点
流年是什么意思
春雨尺八箫,何时浙江潮
芒鞋破钵识,踏过樱花第几桥
三百年诗人,最爱是曼殊。
曼殊的作品,最爱是此篇。
此篇于曼殊而言,正如《锦瑟》之于义山——都是压卷之作,都是身世之感,都是言有尽而意无穷。
此诗易解,四句不过是两层意思:前二句写思乡之情,后二句写身世之感。
而故国之思与飘零之感,又浑然交织,全无半点隔断。
起首一句,七个字是三种意象:春雨;楼头;尺八箫。
三种意象,简简单单的陈列,譬如三面墙,围起一个空间,留给人无限的想象。
这三种意象乃是最好的诗料——春雨朦胧,不知是谁家的楼头,吹起了一片箫声。
春雨易让人惆怅,箫声入耳,撩拨起的便是无边的乡愁了。
果不其然,接下来的一句,诗人便说起乡愁。
当时,诗人流落在异国他乡的日本。
尺八是日本的箫,樱花是日本的国花,这两样都是对处境的点明。
日本的箫,在式样上与中国的不尽相同,但一样是作诗的好材料。
箫与笛,在中国诗歌里有着神奇的魔力,它们是乡愁的催生剂。
李白《春夜洛城闻笛》诗云:“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
”李益《夜上受降城闻笛》云:“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
”曼殊写此篇的时候,潜意识里或许受他们的影响。
由箫声而及乡愁,是旧诗常见的模式,但本篇并不因此减色。
玫瑰和玫瑰总是相类,我们并不因此减少一分爱。
关于“春雨”、“尺八箫”和“浙江潮”,尚有几句可以交代。
《燕子龛随笔》(二九则)云:“日本尺八,状类中土洞箫,闻传自金人。
其曲有名《春雨》,阴深凄惘。
余《春雨》绝句云:……”。
相传,日本僧人乞食,常吹尺八箫。
曼殊流宕异国,心境近于乞食之僧。
乞食箫中,最凄惘者,莫过于《春雨》一曲,故曼殊于此曲最是萦怀。
“春雨”固然是曲名,但在篇中,毋宁解作实景。
若于篇中,拘泥“春雨”只是曲名,则神色顿减。
读此诗,当知《春雨》是何种曲子,又不可拘泥其只是曲子。
《断鸿零雁记》(第二十章)云:“……更二日,抵上海。
余即入城,购僧衣一着易之,萧然向武林去,以余素慕圣湖之美,今应顺道酬吾夙愿也。
既至西子湖边,盈眸寂乐,迥绝尘寰。
余复泛瓜皮舟,之茅家埠。
既至,余舍舟,肩挑被席数事,投灵隐寺,即宋之问‘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处也。
”“浙江潮”,即自宋之问诗中来。
《断鸿零雁记》是曼殊带有自传性质的作品,写于日本归来之后。
武林是自古灵秀地,更兼有宋之问佳句添采,曼殊何日能忘之
故自异国归来,第一站便奔此地。
《断鸿零雁记》是记已归之事,《春雨》诗则写未归之思。
总而言之,“浙江潮”于曼殊而言,是梦绕魂牵的埋骨地。
“归看浙江潮”,正是狐死必首丘之意。
而“浙江潮”者,乃名震天下的钱塘潮,是激情和力量的象征。
故“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是壮语,“归看浙江潮”亦是壮语。
全诗之悲,不掩此句之壮;此句之壮,更增全诗之悲。
三四句,则由故国之思转入身世之感。
芒鞋破钵是点明自家的僧人身份。
僧人自然只能是一双草鞋、一个破钵,走千村、求万户地讨生活。
“踏过樱花第几桥
”究竟走过了多少桥梁道路,记不清了。
当然,诗人未必如此凄惨,以至于要化缘乞讨。
这两句只是极力渲染身世的凄楚而已。
“芒鞋破钵”与漫天樱花之间又是何其的不相称
一片绚烂美丽的背景里,走来的便是这样一个地老天荒无人识的行脚僧。
背景的绚烂,将主人公的潦倒反衬得异样的显目。
“踏过樱花第几桥
”又似从小山词中来。
小山《鹧鸪天》词云:“梦魂惯得无拘检,又踏杨花过谢桥。
”“杨花”换成了“樱花”,不变的是梦境和诗情。
几百年前的词人小晏,是个多愁多病多情种;几百年后的诗人苏曼殊,亦复如是。
小晏《临江仙》词又云:“相寻梦里路,飞雨落花中。
”诗人总是敏感于飞雨落花交织成的梦境,该篇首句的“春雨”、末句的“落花”不正透漏出这一信息么
漫天花雨中,走来一个芒鞋破钵的诗僧,正是梦幻一般的意境呀
樱花是极美丽绚烂的一种花,但花期却太短暂,不消半个月的时间,便在风雨中凋零了。
我们震惊于她的绚烂,痛心于她的凋零。
她是美的极至,却不能永驻,一如我们美好的青春、美好的人生。
生命一如飞雨落花的梦境,美丽,然而短暂。
短得触目惊心。
以至于让我们怀疑她的存在,以为她只是梦境,不曾真实。
为我们留下这美丽篇章的诗人,也只在人间度过三十五个春秋,便在贫病之中永远的走了。
曼殊是诗人中的诗人,他用诗篇来抒写生命,亦用生命来诠释诗篇。
诗人的诗篇与生命,相互应证。
记得曾问朋友:樱花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
朋友回答:繁花如梦缀浮生。
真是感动极了。
忽然想起北岛的两句诗:“路啊路,飘满红罂粟。
”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特征表现在哪几个方面
在外发性和后发性:中国思潮从西方引进, 二间存在着时间差; 中国文学多种世界文学思潮的影响, 具有复合性。
在接受过程中, 中国文学出现了对外来文学思潮的误读, 主要是对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误读。
由于中国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冲突, 导致文学思潮演变的倒序和反复, 如五四启蒙主义被新古典主义取代以及新时期启蒙主义的复兴; 也导致中国反现代性文学思潮的薄弱、滞后, 而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始终没有成为主潮。
我本将心照明月 奈何明月照沟渠什么意思
1、释义 出自《琵琶记》,“我本向明月,明月照沟渠”意思是,心好意地对待你,你却无动于衷,毫不领情。
自己的真心付出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
2、原著简介 《琵琶记》,元末南戏,高明撰。
写汉代书生蔡伯喈与赵五娘悲欢离合的故事。
共四十二出。
被誉为传奇之祖的《琵琶记》,是我国古代戏曲中一部经典名著。
3、作者简介 《琵琶记》的作者高明字则诚,号菜根道人,今浙江瑞安人。
他的生年约在1305年前后。
他的卒年有元末说和明初说两种说法。
持元末说者,认为卒于1359年。
持明初说者,认为卒于朱元璋开国以后。
高明四十岁左右中了进士,在杭州等地作过小官。
后来隐居在宁波城东的栎社镇,《琵琶记》就是在这一时期写成的。
他的剧作除《琵琶记》外,还有《闵子骞单衣记》,已佚。
请问哪位阁下知道“革命和尚”出处
被人称作“革命和尚”。
首先,是个干革命的人。
在清朝末期,维新与革命两派争得厉害,是站在革命派一边的。
因为干革命,苏曼殊结识了不少朋友,他的朋友中,有不少是名头很大的人物,如,如,如,如等。
苏曼殊是个和尚,他不是在家居士,他是真正削发剃度出家了的。
苏曼殊出家的所在,是广东惠州慧能寺。
苏曼殊出家之后,披着袈裟,认真干革命,拼命谈恋爱,写诗作画,依然故我。
此外,他还写了不少小说,最有名者,是《断鸿零雁记》。
苏曼殊的小说,写的是痛彻骨髓的感情,柔肠寸断的爱情。
苏曼殊是个用情至真者,一生和他有过接触有过感情纠葛的女子名单一直罗列下去,可以列很长,如静子,金凤,百助,花雪南,雪鸿,,桐花馆,好好,惠姬,素云,小如意,,国香,湘痕,阿可等等。
和尚苏曼殊和朋友们一起去吃花酒,和女子们诗酒唱和,来来往往,但都是点到为止,“发乎情,止乎礼仪”。
苏曼殊为人之特点,在于真。
在日本的时候,苏曼殊入革命党人办的学校,每天上课之前,教员要训导一番中华将亡,志士努力的话,学员起立肃静,默而听之,苏曼殊奔出教室,号啕大哭。
此是苏曼殊用情之真处。
在给的诗中,他说:“契阔死生君莫问,行云流水一孤僧。
无端狂笑无端哭,纵有欢肠已似冰。
”(《过若松町有感示仲兄》)此是苏曼殊用情之真处。
1914年,他写诗道:“流萤明灭夜悠悠,不耐秋。
相逢莫问人间事,故国伤心只泪流。
”(《东居杂诗十九首》)此是苏曼殊用情之真处。
苏曼殊小说中也多的是痴情男子和痴情女子。
此一种痴情,是“真”。
世上懂得“真”的人不多,纵有知道者,亦少,亦不多,在这不多的人之中,苏曼殊可算是一个。
正如为苏曼殊小说《绛纱记》写的序言中所说:“人生有真,世人苦不知。
彼自谓知之,仍不知耳;苟其知之,未有一日能生其生者也。
”苏曼殊可谓如此。
苏曼殊身世坎坷,生母之去,养母之弃,生父之死,被逐于家庭,飘浮于世间,而又最重一情字。
在其革命志气里,有一粒感情的种子——禅宗慧可大师说“本来缘有地,因地种华生,本来无有地,华亦不曾生”,僧璨大师说“华种虽因地,从地种华生,若无人下种,华地尽无生”——苏曼殊身体里的感情种子,弄得他痛苦,弄得他不安宁。
苏曼殊为了解脱这一痛苦,以自戕的方式生活,大吃大喝,大酒大肉,折磨自己,以求一死,以求速死。
后来,苏曼殊死了。
苏曼殊死的时候,只有35岁,还是年纪轻轻的呢。
时间过得很快,十九世纪过去了,二十世纪过去了,作为历史人物的苏曼殊死了,作为历史人物研究个案的苏曼殊还没有死。
与苏曼殊同时而生但不理解苏曼殊的人很多,不理解苏曼殊的情和苏曼殊的真的人很多,现在,他们基本上也都死了。
关于他们,后来人所知不多,可以知道的是,他们都死了。
呜乎哀哉,唯此而已。
萧萧的意思
【词语】 萧萧【全拼】: 【xiāoxiāo】【释义】: <书>象声词,形容马叫声或风声:马鸣~|风~兮易水寒。
哪里方言月亮叫夜明
我来回答你
只有出处,没有传说
月亮有在中国古代文人笔下有很多不同的叫法,至少有数百种之多,每一种称呼都反映了作者当时写作是的心境,没有其他更深的含义。
月亮比较有名的别称有150种之多。
下面我罗列其中的三分之一,你就明白了“玄度”没有那么“玄”,几百年后的谢庄千古名篇《月赋》还称之为“玄兔”呢
月亮的别称150例(按字母顺序排列)(二) 51、寒璧:喻月亮。
陆游《大醉梅花下走笔赋此》:“酒阑江月上,珠树挂寒璧。
” 陆游《秋夜独过小桥观月》:“乍圆素月升寒璧,欲散微云蹙细鳞。
” 52、寒蟾:指月亮。
传说月中有蟾,故称。
唐 刘禹锡《和汴州令狐相公到镇改月偶书所怀二十二韵》:“管弦喧夜景,灯烛掩寒蟾。
” 宋 张铣《玉树后庭花》词之二:“青骢一骑来飞鸟,靓妆难好,至今落日寒蟾,照台城秋草。
” 53、寒魄:指月亮。
亦指月光。
唐 刘得仁《对月寄雍陶》:“圆明寒魄上,天地一光中。
” 唐 方干《中秋月》:“泉澄寒魄莹,露滴冷光浮。
” 明 李流芳《过皋亭龙居湾宿永庆禅院同一濂澄心恒可诸上人步月》:“气和空宇澄,寒魄如春露。
” 54、寒兔:传说月中有玉兔,故称。
李贺《李凭箜篌引》:“吴质不眠倚桂树,露脚斜飞湿寒兔。
” 王琦汇解:“寒兔谓秋月。
” 55、寒玉:指月。
李贺《江南弄》:“吴歈越吟未终曲,江上团团帖寒玉。
” 宋 吕渭老《念奴娇·赠希文宠姬》:“暮云收尽,霁霞明高拥一轮寒玉。
” 56、寒月:清冷的月亮。
李白《望月有怀》:“寒月摇清波,流光入窗户。
” 元 吴澄《送国子伴读倪行简赴京》:“不怕狂风妨去鷁,偏愁寒月照栖鸦。
” 57、金蟾:月亮的别称。
神话传说月中有蟾蜍,故称。
汉 张衡《灵宪》:“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姮娥窃之以奔月……遂托身于月,是为蟾蠩。
” 唐 令狐楚《八月十七日夜书怀》:“金蟾着未出,玉树悲稍破。
” 明 高启《赋赵王孙家琵琶诗》:“梦断金蟾隔烟小,青冢理声秋不晓。
” 58、金娥:指神话传说月中女神嫦娥,亦借指月亮。
唐 许敬宗《奉和喜雪应制》:“腾华承玉宇,凝照混金娥。
” 李白《明堂赋》:“玉女攀星于网户,金娥纳月于璇题。
” 59、金镜:喻月亮。
元稹《泛江翫月》:“远树悬金镜,深潭倒玉幢。
” 陆游《隔浦莲近拍》:“烟霏散,水面飞金镜,露华冷。
” 刘克庄《水调歌头·癸卯中秋作》:“竞看姮娥金镜,争信仙人玉斧,费了一番修。
” 60、金盆:喻圆月。
杨万里《携酒夜觅罗季周》:“淡月轻云相映着,浅黄帕子裹金盆。
” 61、金魄:满月。
唐 沉佺期 《和元舍人万顷临池玩月》:“玉流含吹动,金魄度云来。
” 李白《古风》之二:“圆光亏中天,金魄遂沦没。
” 王琦 注:“金魄者,是言满月之影,光明灿熳,有似乎金,故曰金魄也。
” 白居易《首夏同诸校正游开元观因宿玩月》:“须臾金魄生,若与吾徒期。
” 62、金兔:月的别称。
南朝 梁 刘孝绰《林下映月》:“攒柯半玉蟾,裛叶彰金兔。
” 隋 江总《答王筠早朝守建阳门开》:“金兔犹悬魄,铜龙欲启扉。
” 唐 卢仝《月蚀》:“朱弦初罢弹,金兔正奇绝。
” 63、冷月:月亮。
月光给人以清冷之感,故称。
苏轼《次韵刘景文路分上元》:“华灯閟艰岁,冷月挂空府。
”《红楼梦》第七六回:“寒塘渡鹤影,冷月葬诗魂。
” 64、满魄:圆月。
唐 赵蕃《月中桂树赋》:“杳杳低枝,拂孤轮而挺秀;依依密树,侵满魄而含芳。
” 元 柳贯《晚渡扬子江未至甘露寺城下潮退阁舟风雨竟夕》:“乘流俟满魄,明夕异今昨。
” 65、明蟾:古代神话称月中有蟾蜍,后因以“明蟾”为月亮的代称。
唐 舒元舆《坊州按狱苏氏庄记室二贤自鄜州走马相访》诗:“阳乌忽西倾,明蟾挂高枝。
” 明 刘基《次韵和十六夜月再次韵》:“永夜凉风吹碧落,深秋白露洗明蟾。
” 66、千里烛:指明月。
宋 陶谷《清异录·天文》:“道士王致一曰:‘我平生不曾使一文油钱,在家则为扇子灯,出路则为千里烛。
’” 67、清蟾:称澄澈的月亮。
因传说月中有蟾蜍,故以蟾代称月。
亦用以比喻圆镜。
宋 张先《于飞乐令》:“宝奁开,菱鉴静,一掬清蟾。
” 宋 贺铸《采桑子·罗敷歌》:“犀尘流连。
喜见清蟾似旧圆。
” 范成大《代人七月十四日生朝》:“已饶瑞荚明朝满,先借清蟾一夜圆。
” 68、清规:指月亮。
唐 齐己《中秋月》:“空碧无云露湿衣,群星光外涌清规。
” 69、卿月:月亮的美称。
亦借指百官。
语出《书·洪范》:“王省惟岁,卿士惟月,师尹惟日。
” 孔传:“卿士各有所掌,如月之有别。
” 孔颖达疏:“卿士分居列位,惟如月也。
” 岑参《西河太守杜公挽歌》:“惟余卿月在,留向 杜陵 悬。
”杜甫《暮春江陵送马大卿赴阙下》诗:“卿月升金掌,王春度玉墀。
” 浦起龙心解:“卿月升,恩命起召也。
” 清 赵翼《述庵司寇新刻大集兼怀亡友璞函》:“即今奏凯十五年,卿月崇班已屡迁。
” 70、却月:半圆的月亮。
《南史·侯景传》:“城内作迂城,形如却月以捍之。
” 71、麝月:指月。
南朝 陈 徐陵《<玉台新咏>序》:“金星将婺女争华,麝月与嫦娥竞爽。
” 明 唐寅《咏春江花月夜》:“麝月重轮三五夜,玉人联浆出灵娥。
” 72、素娥:亦用作月的代称。
《文选·谢庄<月赋>》:“引玄兔于帝台,集素娥于后庭。
” 李周翰 注:“常娥窃药奔月,因以为名。
月色白,故云素娥 。
” 李商隐《霜月》:“青女 素娥 俱耐冷,月中霜里鬭婵娟。
” 明 徐渭《月下梨花》诗之一:“莫遣风吹廻作态, 素娥应妬舞《霓裳》。
” 郁达夫《旧历八月十六夜观月》:“窗外素娥窗内客,分明各自梦巫阳 。
” 73、素魄:月的别称,亦指月光。
南朝 梁简文帝《京洛篇》:“夜轮悬素魄,朝光荡碧空。
” 孟郊《立德新居》诗之五:“素魄衔夕岸,绿水生晓浔。
” 周邦彦《倒犯·新月》:“驻马望素魄,印遥碧,金枢小。
”《水浒传》第二回:“彩霞照万里如银,素魄映千山似水。
” 清 姚鼐《乙卯二月望夜与胡豫生观月有咏》:“素魄行无极,光霁旷来临。
” 74、太阴:谓月亮。
日月对举,日称太阳,故月称太阴:坐使青天暮,小星愁太阴。
唐 杨炯《盂兰盆赋》:“太阴望兮圆魄皎,阊阖开兮凉风袅。
” 清 龚自珍 《叙嘉定七生》:“抱秋树之晨华,指太阴以宵盟。
” 郭沫若 《女神·地球,我的母亲
》诗:“那昼间的太阳,夜间的太阴,只不过是那明镜中的你自己的虚影。
”神话中指月神。
《西游记》第九五回:“ 太阴道:‘与你对敌的这个妖邪,是我广寒宫捣玄霜仙药之玉兔。
’”指月宫。
清 洪升《长生殿·闻乐》:“吾乃嫦娥是也,本属太阴之主,浪传后羿之妻。
” 75、太阴精:指月亮。
古人以为月乃太阴之精。
唐 张祜《中秋夜杭州玩月》:“万古太阴精,中秋海上生。
” 76、天镜:指明月。
唐 宋之问《游禹穴回出若邪》:“石帆摇海上,天镜落湖中。
”明 王世贞《月夜步西园积雪有述》诗:“冰壶初世外,天镜忽林端。
” 77、天眼:指月亮。
唐 卢仝《月蚀诗》:“皇天要识物,日月乃化生。
走天汲汲劳四体,与天作眼行光明……再得见天眼,感荷天地力。
” 明 刘基《次韵石末公七月十五夜月蚀诗》:“不知妖恠从何来,惝恍初惊天眼昳。
” 78、兔钩:弯月。
唐 崔橹《过南城县麻姑山》:“斜倚兔钩孤影伴,校低仙掌一头来。
” 79、兔轮:月亮的别称。
传说月中有玉兔捣药,故称。
唐 元稹《梦上天》:“西瞻若水兔轮低,东望蟠桃海波黑。
” 80、兔魄:月亮的别称。
《参同契》卷上:“蟾蜍与兔魄,日月无双明。
” 元 范梈《赠郭判官》:“慈乌夜夜向人啼,几度纱窗兔魄低。
” 明 刘基《怨王孙》:“兔魄又满,天长鴈短。
”《剪灯馀话·江庙泥神记》:“俄而兔魄将低,鸡声渐动。
” 81、兔华:明月。
清 陈维崧《水调歌头·汾西侯仲辂示我九日纪梦词二阕依韵奉和》之二:“天上兔华满,只照别家圆。
” 82、兔月:月亮的别名。
北周 庾信《七夕赋》:“兔月先上,羊灯次安。
” 唐 杨师道《阙题》:“羊车讵畏青门闭,兔月今宵照后庭。
” 82、团栾:指圆月。
林逋《又咏小梅》:“摘索又开三两朵,团栾空绕百千回。
荒邻独映山初尽,晚景相禁雪欲来。
”借指月,清 纳兰性德 《菩萨蛮·回文五》:“月也异当时,团栾照鬓丝。
” 83、望舒:话中为月驾车的神。
《楚辞·离骚》:“前望舒使先驱兮,后飞廉使奔属。
” 王逸 注:“望舒月御也。
” 借指月亮。
汉 张衡《归田赋》:“于时曜灵俄景,继以望舒,极盘游之至乐,虽日夕而忘劬。
”《后汉书·蔡邕传》:“元首宽则望舒朓,侯王肃则月侧匿。
” 李贤 注:“望舒,月也。
” 晋 张协《杂诗》之八:“下车如昨日,望舒四五圆。
” 唐 耿湋《喜侯十七校书见访》:“谁为(谓)须张烛,凉空有望舒。
” 84、微月:犹眉月,新月。
指农历月初的月亮。
晋 傅玄《杂诗》:“清风何飘颻,微月出西方。
” 杜甫《水会渡》:“微月没已久,崖倾路何难
”王闿运《七夕立秋作》:“虚庭一叶下,微月千里阴。
” 苏曼殊《断鸿零雁记》:“是夕,微月已生西海,水波不兴。
” 85、夕轮:指圆月。
骆宾王《久戍边城有怀京邑》:“葭繁秋引急,桂满夕轮孤。
” 86、夕兔:古代神话谓月中有兔,故用为月亮的代称。
骆宾王《艳情代郭氏答卢照邻》:“抱膝当窗看夕兔,侧耳空房听晓鸡。
” 87、夕月:傍晚的月亮。
李白《怨歌行》:“荐枕娇夕月,卷衣恋春风。
” 苏轼《坤成节功德疏文》之七:“右伏以星火西流,方岁功之平秩,夕月既望,昭阴德之致隆。
” 88、小蟾:指月亮。
宋 吴文英《霜叶飞·重九》词:“小蟾斜影转东篱,夜冷残蛩语。
” 89、宵晖:指月亮。
元稹《春》:“昼漏频加箭,宵晖欲半弓。
” 90、宵魄:指月亮。
韩愈《会合联句》:“夏阴偶高庇,宵魄接虚拥。
” 廖莹中 注:“宵魄,谓月。
” 91、玄度:月亮。
汉 刘向《列仙传·关令尹赞》:“ 尹喜 抱关,含德为务,挹漱日华,仰玩玄度。
” 92、玄兔:指月亮。
《文选·谢庄<月赋>》:“引玄兔于帝台,集素娥于后庭。
” 李周翰 注:“玄兔,月也。
月中有兔象,故以名焉。
” 唐 白行简《新月误惊鱼赋》:“桂影西南,尽迷玄兔;与波上下,难晦紫鳞。
” 宁调元《八月十五夜漫书一律》:“玉宇琼楼最高处,一天霾雾拨难开。
祇怜玄兔千年冷,不见灵槎八月来。
” 93、玄阴:指月亮。
柳宗元《天对》:“玄阴多缺,爰感厥免。
”元稹《赋得九月尽》:“玄阴迎落日,凉魄尽残钩。
” 94、玄烛:指月亮。
曹丕《答繁钦书》:“白日西逝,清风赴闱,罗帷徒袪,玄烛方微。
” 95、瑶轮:指月亮。
明 夏完淳《大哀赋》:“不意瑶轮无长炯之期,玉历有中屯之会。
” 96、瑶兔:指月亮。
唐 王勃《上明员外启》:“侧闻金乌耸辔,俯圆燧而抽光;瑶兔浮轮,候方诸而吐液。
” 唐 黄滔《丈六金身碑》:“一夕雨歇天清,风微月明,瑶兔无烟,铜龙有声。
” 97、瑶月:月亮的美称。
唐 令狐楚《还珠亭赋》:“掩星彩,迷瑶月。
” 金 王庭筠 《清平乐·应制》:“琼枝瑶月,帘卷黄金阙。
” 98、夜光:月亮。
《楚辞·天问》:“夜光何德,死则又育
” 王逸 注:“夜光,月也。
” 三国 魏 曹植《芙蓉赋》:“其始荣也,皦若夜光寻扶桑 ;其扬晖也,晃若九阳出暘谷 。
” 晋 王嘉《拾遗记·炎帝神农》:“筑圆邱以视朝日,饰瑶阶以揖夜光。
” 99、夜明:月亮。
明 张居正《郊礼新旧考》:“初建圜丘于大祀殿之南,每冬至祀天,以大明、夜明、星辰、风雷从祀。
” 100、夜魄:指月亮。
前蜀 韦庄《三堂东湖作》:“蟾投夜魄当湖落,岳倒秋莲入浪生。
”
鸳鸯蝴蝶派的文学趣味
鸳鸯蝴蝶派是发端20世纪初叶的上海“十里”的一个文学流派们最初热衷的题材情小说,写才子和佳人“相悦相恋,分拆不开,柳荫花下,象一对蝴蝶,一双鸳鸯”(《上海文艺之一瞥》),并因此得名而成为鸳鸯蝴蝶派。
这一派的早期代表作为徐枕亚的《玉梨魂》,是用四六骈俪加上香艳诗词而成的哀情小说。
重要而特殊的一个文学流 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过程中,涌现过许多文学流派,鸳鸯蝴蝶派是其中重要而且特殊的一个派别。
说其重要,是因为在“五四”前后的文学革命的时代大潮流中,他们是属于重继承和多保守的一个文学流派,屡遭新文学界的批判。
在新文学营垒与该派的论争和交锋中,使新文学在文坛中扩大了自己 啼笑姻缘的影响,日益茁壮成长。
谈及新文学运动就不可避免地牵涉到该派别。
说其特殊,是因为由于受到新文学各派的的指责,使其中的有些作者长期以来不原承认自己是隶属于该流派的成员,突出的例子是其代表作家之一的包天笑否认自己是鸳鸯蝴蝶派。
他曾说:“近今有许多评论中国文学史实的书上,都视我为鸳鸯蝴蝶派……我所不了解者,不知哪几部我所写的小说是属鸳鸯蝴蝶派。
”该派有的作者只承认自己是《礼拜六》派,而否认自己是鸳鸯蝴蝶派,他们通常所持的一个理由是,鸳鸯蝴蝶派是仅限于徐枕亚,李定夷等少数几位作者,只有民初那些写四六骈俪体言情小说的才是名实相符合的鸳鸯蝴蝶派。
鸳鸯蝴蝶派的代表作品 鸳鸯蝴蝶派小说曾是新文化运动前文学界最走俏的通俗读物之一。
代表作之一徐枕亚的《玉梨魂》,曾创下了再版三十二次,销量数十万的纪录。
著名作家张恨水的《啼笑因缘》也曾先后十数次再版。
其中最杰出的的是”五虎将“与“四大说部“:前者为徐枕亚、包天笑、周瘦鹃、李涵秋、张恨水,后者为《玉梨魂》《广陵潮》《江湖奇侠传》《啼笑姻缘》。
批判 但五四新文化运动、鲁迅先生领导下的左翼文联(左联)等新文化阵营,“在批判复古论调的同时,新文学阵营不断地同鸳鸯蝴蝶派展开斗争”。
他们认为鸳鸯蝴蝶派“文学”滋生于半殖民地的“十里洋场”,风行于辛亥革命失败后的几年间,是在人民开始觉醒的道路上的麻醉药和迷惑汤。
虽然有少数作品在某种程度上暴露了社会黑暗、家庭专制和军阀横暴等等,但其总的倾向却不外乎“卅六鸳鸯同命鸟,一双蝴蝶可怜虫”,正如鲁迅说的是“新的才子+佳人”,“相悦相恋,分拆不开,柳荫花下,象一对蝴蝶,一双鸳鸯一样”。
标榜趣味主义,大都内容庸俗,思想空虚,“言爱情不出才子佳人偷香窃玉的旧套,言政治言社会,不外慨叹人心日非世道沦夷的老调”。
有一定进步意义 然而,在阅读鸳鸯蝴蝶派作家的一些作品后,我们却可以感觉到,这一类作家的所谓靡靡之作,并非全都只是单纯的“以描写‘才子佳人’为主,主要表现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落后思想意识,表现了病态社会中小市民阶层的艺术趣味。
”他们中不少,比如张恨水的《啼笑因缘》,比如包天笑的《沧州道中》等,或多或少的抨击了当时社会的黑暗面,讽刺了当时社会的种种弊端,借才子佳人或凄婉或悲凉的恋爱故事,歌颂或赞扬了抗日青年,反映了对当时社会男女不平等、贫富不均匀、等种种丑恶,在当时来说,与其同时代的一些极端宣扬封建复辟、迷信邪说的文学作品相比,是具有一定进步意义的。
对于某些批判鸳鸯蝴蝶派的结论 对于某些批判鸳鸯蝴蝶派的结论,归纳起来,大致有下列三点:一、在思想倾向上,认为该派代表了封建阶级(或日垂死的地主阶级)和买办势力在文学上的要求,是遗老遗少的文学流派,或称是“一般逆流“;二、认定这是十里洋场的产物,是殖民地租界的畸形胎儿,三、这一流派属帮闲、消遣文学,是游戏的消遣的金钱主义文学观念的派生物。
以上的这些论点是有明显偏颇的,与大量作品对照,“定论”与客观存在的实际相去甚远。
而现实中,有些批判往往是对某种现成的论点的转辗传抄。
传抄得多了,某些现成的论点就成为“众口一词”的定论。
于是这一定论又为人们所“习相沿用”,如此循环往复,笃信弥坚。
但是越对该流派了解深入,就会不可避免的对所持的过去的“批判定论”产生应有的、必要的疑窦。
对于鸳鸯蝴蝶派的正确解释 其实,对于鸳鸯蝴蝶派的正确解释,应当是:清末民初大都会兴建过程中出现的一个承袭中国古代小说传统的通俗文学流派。
这一流派一直得不到新文学界各派别的承认,是有其很复杂的历史背景的:时代潮流的激荡,文学观念的演进,读者心态的变异等多方面的原因,再加上其本身的先天的缺陷,都决定了它必然要经历一段受压抑的历程。
该派与“新派”文学之间的论争,说到本质上,也就是“通俗”文学与“严肃”文学,“平民”文学和“革命”文学之间的矛盾的产物。
埋石弃石记鸳鸯蝴蝶派的代表作家之一包天笑曾谈及他的创作宗旨是:“提倡新政制,保守旧道德”。
这十个字是极凝炼概括地代表了这一流派大多数作者群的思想实况。
这与“五四”前后兴起的新文学运动中的极力提倡科学,反封建的宗旨是相违背的。
在形式上,鸳鸯蝴蝶派则以长篇章回体小说为其特色,而短篇最可读的首推传奇故事,也即他们仍然承袭的古代白话小说的传统。
而新文学在初创阶段就主动摒弃章口体,而重点致力于短篇小说的创新上。
这样、在“五四”揭开新民主主义革命序幕时,在新文学阵营眼里,他们还“拖着一条无形的旧民主主义的辫子”,而他们在作品中的某些传统意识,必然与新文学营垒形成一对矛盾。
由于内容和形式上的分道扬镳,“五四”前后新文学界对该派的主动出击是无可避免的,既是历史的必然,也是创新的必需。
在历史发展的进程面前,我们完全可以理解这场批判的必要性和必然性。
在五四时期对鸳鸯蝴蝶派的另一严重批评是抨击它的游戏消遣的金钱主义的文学观念。
这是有关文学功能方面的原则分歧。
文学功能应该是多方面的,它应该有战斗功能、教育功能、认识功能、审美功能、娱乐功能等等。
小说与“大”说 每当迎来历史变革的潮汐或革命大波袭来的前夜,文艺的战斗功能和教育功能总是会被强调到极端重要的地步。
在近代文学中梁启超就是鼓吹这方面的功能的代表人物。
他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
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
何以故
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
” 梁启超将小说提高到“大道中的大道”的高度,小说就成了“大”说,成为救国救民的灵药。
但在中国文学传统中,小说一直被视为“小道中的小说”。
新文学作家朱自清是看到了这一点的:“在中国文学的传统里,小说和词曲(包括戏曲)更是小道中的小说,就因为是消遣的,不严肃。
不严肃也就是不正经;小说通常称为“闲书”,不是正经书……鸳鸯蝴蝶派的小说意在供人们茶余酒后消遣,倒是中国小说的正宗。
中国小说一向以“志怪”、“传奇”为主,“怪”和“奇”都不是正经的东西。
明朝人编的小说总集所谓“三言二拍”……“拍案惊奇》重在“奇“很显然。
“三言”……虽然重在“劝俗”,但是还是先得使人们“惊奇”,才能收到“劝俗”的效果……《今古奇观》,还是归到“奇”上。
这个“奇”正是供人们茶余酒后消遣的。
” 鸳鸯蝴蝶派的成员是这一传统功能观的自觉世袭者。
姚鹤雏在《小说学概论》中引经据典他说:“依刘向《七略》及《汉书·艺文志》,小说出于‘街谈巷语,道听途说’,则其所载,当然多属‘闲谈奇事’;又观《七略》及《隋书·经籍志》所录,则‘凡各著艺术立说稍平常而范围略小巧者,皆可归于小说’。
‘其所包举、无非小道’。
” 冲突 这种文学的功能观与当时提倡血和泪的文学且具有历史使命感的革命作家就构成了冲突。
由沈雁冰和周作人发起的文学研究会对“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文学观及在这种文学观引导下产生的文学现象提出了批评。
如果将这种批评进行“语境还原”的话,那种被视作游戏或消遣的文学,无疑指的是清末民初以来的所谓“黑幕文学”、“狭邪小说”,指的就是“鸳鸯蝴蝶派”等依赖报刊杂志和读者市场的大众通俗文学。
沈雁冰和周作人,此前此后发表了很多批评“礼拜六派”、“鸳鸯蝴蝶派”等游戏消遣文学的言辞文章。
而且不仅是文学研究会诸人,在“五四”历史文化语境中,新文化阵营中的几乎所有人都把鸳蝴派文学当作封建旧文学的余孽、当作建立新文学的障碍和对立物而痛加批判与否定。
新文学作家认为鸳鸯蝴蝶派文学不仅是创建新文学的绊脚石,而且它们的消闲游戏观念和倾向更大有害于国民性的改造和重建、有害于人生社会的改良和更新、有害于中国从“边缘”重返“中心”的努力、有害于现代民族国家的实现,一句话,有害于中国现代化历史目标和“强国梦”的实现。
因此,出于这种以民族国家为终极关怀的启蒙文学观的立场和追求,文学研究会以及新文学阵营对鸳鸯蝴蝶派等游戏消闲类的都市通俗文学发出了激烈的批判之声,而且,“五四”以后新文学对都市通俗文学的轻蔑和批判依然没有终结,对武侠影片《火烧红莲寺》为代表的武侠小说、侦探言情小说以及所谓的“小市民文艺”,包括鲁迅和茅盾在内的新文学作家也都予以了痛击。
新文学阵营对上述的都市通俗文学的批判,从其启蒙文学观和为新文学的创立与发展开辟道路、开拓空间的角度来看,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与必要性。
他们之对鸳蝴派等都市通俗文学的批判清理,是因为他们认为此类文学根本上不利于甚至是妨碍着中国成为现代民族国家,妨碍着中国走向进步,所以,必欲批判之铲除之,他们是为了这一根本的现代性使命而进行了对“旧世界”的批判和清理。
在这些追求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先驱者看来,那些以游戏消遣娱乐消费为 江湖奇侠传目的的文学,尽管比新文学诞生得早或与新文学同时存在,但它们却不具有丝毫的现代性,而是历史和时代的垃圾。
革命作家的使命在于用他们的小说启发和培养一代民族精英。
因此,游戏与消遣功能在现代文学的历史阶段中常被视为玩物丧志的反面效应而一再加以否定。
“平民”文学 但“娱乐”既然是文学本身的功能之一,人们就只能在某一特定时期对它加以否定而去约束它,以便突出其他的功能,却无法彻底剥夺这种功能的本身。
即使在特别需要发挥文学的战斗功能的岁月里,都市中的别一层次的读者,仍然停留在将小说看成“小道中的小道”的梯阶上,那就是一般意义上的大众,或称“俗众”也可以。
首先在“俗众”看来,小说发挥游戏与消遣效应是他们调节生活的一种需要。
随着新兴大都市的成型和工业机器齿轮的转速越来越快,都市通俗小说的需求量也激升。
生活节奏频率的空前增速,人们觉得脑力和筋肉的弦绷得太紧,工余或夜晚需要松弛一下被机械绞得太紧的神经。
这就需要娱休,而读小说就是娱乐和调节的方法之一。
其次,当四周生活像万花筒般变异的环境里,特别是像上海这样新兴的大都市,光怪陆离,五光十色,瞳勉担越,无奇不有。
一般的“俗众”也希望通过都市通俗文学去了解四周的环境,以增强适应性,不致茫茫然地跌人生活陷饼。
第三,这些“俗众”一般都缺乏新兴意识,但是他们也在通俗文学中接受某种教育,即在茶余酒后阅读通俗文学,在拍案惊奇中受到潜移默化的教诲与惩戒。
因此,在近现代文学革命中,这一流派不是面向民族精英,而是主要面向一般意义上的大众,因而可以称他是一种市民文艺,“平民”文学。
但是它也并非与知识分子读者无缘,在知识分子阶层中,比较明显分成两种类型:一种是喜爱新文艺的读者,他们常为文学功能观的矛盾而排斥通俗文学:另一种平日对新旧两派的小说部涉猎例览,又往往为通俗文学的趣味性和可读性所吸引,为其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紧张惊险的悬念所牢牢控制,在富有兢力的优秀通俗文学作品面前,他们也手不释卷,废寝忘食。
但问题是他们并不在公开场合中赞扬或介绍通俗文学,为其制造良性评价的舆论。
似乎被通俗文学所吸引是有失身份的一种表现,因为部分知识分子一直视通俗文学是低级趣味的同义词。
这就构成了一种表里不一的矛盾:“暗里读得津津有味,明里却不愿津津乐道”,“感情上被它打动过,理智上认定它低人一等”。
这种微妙的心态是一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心理分裂症。
不论是一般“俗众”或是部分知识分子,被通俗文学所吸引的磁力皆来自趣味性,而趣味性正是达到游戏、消遣目的的必备要素,也是娱乐功能的灵魂。
趣味性还是通俗文学进行“劝俗”和“教化”的媒介和桥梁。
但是趣味性一度被新文学家看成是“玩物丧志”、”醉生梦死”的麻醉剂,以致朱自清也发生这样的感啃:“但是正经作品若是一味讲究正经,只顾人民性,不管艺术性,死板板的长面孔教人亲近不得,读者恐怕更会躲向那些刊物里去。
”鲁迅也曾说:“说到‘趣味’那是现在确已算一种罪名了,但无论人类底也罢,阶级底也罢,我还希望总有一日弛禁,讲文艺不必定要‘没趣味’。
”同时鲁迅还说:“在实际上,悲愤者和劳作者,是时时需要休息和高兴的。
”这正说明了趣味性和娱乐功能是无罪的。
而通俗文学是着眼于可读性、情节性。
讲究情节曲折,峰口路转,跌宕多姿,高潮迭起。
在中国的现代通俗小 广陵潮说读者中出现过“《啼笑姻缘》、《金粉世家》迷”就是从有趣味而逐渐进入陶醉的境界,以致达到了消遣娱乐的效果。
这与我们七十,八十年代的“武侠”小说迷,“金庸”迷;“古龙”迷;以及“言情”小说“琼瑶”迷等很是相似。
这也说明通俗文学是有其存在的旺盛力的
横向对比 据说,在美国,过去许多学者对通俗文化也持否定态度,认为它们仅是庸俗文学和文学垃圾而已。
但是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学”兴起。
学者对通俗文化开始从轻视转为重视,从主观转为客观,从片面转为全面。
他们认识到,通俗文艺能历史地反映某一时间长链中读者心态和价值观的变化。
“这些畅销书是一种有用的工具,我们能够透过它们,看到任何特定时间人们普遍关心的事情和某段时间内人们的思想变化。
”日本的尾崎秀树在他的《大众文学的历史》一书中写道:“说起大众文学,一般是指能够大量生产、大量传播、大量消费的商业性文学。
就内容而言,是为大众娱乐的文学,但不只是单纯的有趣,也起着通过具体化的方式给大众提供其所不知道的事物的作用……由于日报百万数的突破,新闻系统周刊的创刊……本来与小说无缘的阶层变成了接受者,这就期待适应不仅本来热衷文学、还有未经文学训练的读者要求的小说。
……大众文学是与大众一起产生,而又是大众意识的反映。
”这位研究日本通俗文学颇有建树的学者的一席话,对我们很有参考价值。
生不逢时 鸳鸯蝴蝶派的兴起可谓生不逢时,五四时期,在中国小说从传统型改道转轨为现代型的过程中,开始总要与民族旧形式呈决裂的态势,以期符合世界潮流的新形式。
这就会有一番大革命、大剧变,对内容中的传统意识和形式中的传统框架,总要有一番大革新和大突破。
这就必然会与仍然坚持承袭中国传统的文学流派产生大碰撞。
新兴意识和革新形式总要在大搏战中争得自己的文坛领土,否则它难于有立锥之地。
对传统的精神产品,总要有人来向它进行大胆的挑战,对世袭文坛的权威总要有人去撼动它的根基,然后才会有创新的极大的自由。
文学研究会在宣言中宣告:“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
我们相信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治文学的人也当以这事为他终身的事业,正同劳农一样。
”这段话的指向当然是以鸳鸯蝴蝶派为否定目标的。
所以鸳鸯蝴蝶派首当其冲,其实是作了革命文学的反面教材。
走向末路 中国的成立后一段时间的革命浪潮彻底断绝了鸳鸯蝴蝶派的政治经济基础,同时给以这一派作家猛烈的打击,从此鸳鸯蝴蝶派正式走向末路。
客观上也作过一定的贡献 客观上说这个继承中国古典小说传统革新发展意识不强的都市通俗文学流派,在现代文学的发展历史上,虽有其局限性,却也作过一定的贡献。
其中的很多文学作品是非常不错的,与新文学的某些同类题材相比,也是毫不逊色的。
“黑幕狭邪”鸳鸯蝴蝶派文学,在根本上是中国社会现代化和文学现代化追求的产物,它们本身就是现代性事物。
其实,鸳鸯蝴蝶派当初问世之时,甚至标榜的是“新小说”,直接承继晚清“新小说”而来,接受了西方小说的影响,为中国小说的发展,作出过重要的贡献:中国第一本正面描写和尚恋爱的小说,是被周作人称为鸳鸯蝴蝶派的祖师苏曼殊写的《断鸿零雁记》。
中国第一本歌颂寡妇恋爱的小说,是鸳 断鸿零雁记鸯蝴蝶派的代表作《玉梨魂》。
中国第一本长篇日记体小说,是《玉梨魂》作者徐枕亚写的《雪鸿泪史》。
中国第一篇书信体小说,是鸳鸯蝴蝶派主将包天笑的《冥鸿》。
无论在内容还是在形式上,鸳鸯蝴蝶派都有所创新。
在民初的文坛上,无论从大量运用文言创作还是从内容与形式的创新来看,鸳鸯蝴蝶派都代表了当时中国文学的水平。
它同时创作纯文学与通俗文学。
五四新文学的崛起,一种更新的纯文学问世,逼着鸳鸯蝴蝶派完全走向通俗文学。
抗拒这一转化的徐枕亚、李定夷、吴双热等人先后离开了作家队伍,顺应这一转化的包天笑、周瘦鹃等则占据了通俗文坛。
从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双栖,转化为完全的通俗文学,决定了通俗文学接受纯文学的影响,表现为纯文学对通俗文学的渗透。
例如中国的通俗小说,本来是偏重于故事情节的,这时大量运用心理描写、情景描写,也注重展示人物的内心世界。
从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可以看到通俗小说从传统的“章回体”变为现代小说,其间充满了纯文学对通俗文学的渗透。
发展到琼瑶、金庸的小说,只是在题材上沿袭了传统的“言情”、“武侠”,小说的思想情感,形式内容与传统通俗小说相比,已经完全现代化了。
当代小说,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界限越来越不明朗:一些被视为是纯文学的作品,按西方标准应当算通俗小说;一些从来被视为通俗小说的,如金庸的作品,被一些大学讲坛认为是纯文学。
也许,这本身就可以证明纯文学与通俗文学之间的差距已经缩小到何等地步。
虽然按照五四新文学的标准,这些创新还不够,作家不敢打倒封建礼教,不敢让恋爱的和尚、寡妇与恋人结婚,而且颇有媚俗的倾向,但是,文学史的评价,毕竟是根据它比前人多提供了什么。
因此,新文学有理由批判鸳鸯蝴蝶派,如今的文学史家却不能否认鸳鸯蝴蝶派作出的贡献。
对鸳鸯蝴蝶派,过去有若干不公允或误解性的评价以致定论,是偏颇的,是以“革命文学”的名义对其全面的否定,是一种不科学的学术氛围下的产物。
我们今天对待这一流派,应当正确认识其历史与地位,肯定其历史意义。
客观的去看待他,客观的去看待中国近代的文学史。
复苏 今天的思想解放下,很多人又重新看到了鸳鸯蝴蝶派的价值,早已凋亡的鸳鸯蝴蝶派又在20世纪末得到复苏。
很多新时代的作品涌现了出来。
对鸳鸯蝴蝶派的评价也公正化。
(这种文学团体或文学艺术在特定时期衰亡,又在一段时期后得到复苏的现象很常见,通常称为“借尸还魂”)[1]